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李彥慧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董子琪
“畢業”二字總是意味著學生生涯的結束,意味著新的起點與開始,在過去的兩個月里,高校畢業生們收拾行囊,離開校園,前往他們人生的“下一站”。然而也有一群年輕人選擇暫緩離開校園,用延遲畢業的方式為自己劃出“安全區”。
盡管從制度上來說,延遲畢業的高校學生仍是在規定的年限內繼續學習,但我們在社交平臺上常常看到諸如“延畢會是一生的污點嗎?”、“延期畢業很丟臉嗎?”類似的擔憂,以及不少講述自己因為學分沒修滿、論文沒有通過、某些考試沒有合格等原因,想要畢業卻因學校硬性要求而“被動延畢”的例子。
《本科生延期畢業現象的透視與解析》一文分析了延畢本科生的畫像:佛系心態、喪樣狀態、病弱體質,這些學生從“老油條”、“逃課生”、“學困生”最后沉淪為延畢生。即使最后成功畢業,延畢的污名也始終伴隨著他們。有人在社交平臺分享延畢經驗時提到,找工作時一旦被HR知道,個人能力往往會遭到質疑。

但前段時間,“一批985畢業生選擇主動延畢”的詞條爬上熱搜,“延畢是更適合中國寶寶體質的gap year(間隔年)”這類表達也在社交平臺走紅。一群人有心畢業卻因為達不到標準而“被動延畢”,另一群人則不惜以少修學分、故意掛科追求“主動延畢”,后者甚至成了“聰明人的選擇”。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預計有1158萬高校畢業生,同比增加82萬。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延畢意味著能保留應屆生身份,而應屆生意味著更多的選擇,不僅能參與相對門檻更低的校招,也能報名參加一些只面向應屆生開放的考編、考公的崗位考試。

所謂“延畢是更適合中國寶寶體質的gap year”,但gap year的出發點是打破框架式的生活,可主動延畢的高校學生們卻似乎在框架內持續內卷: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那便延遲一年畢業,期間多做幾份實習優化履歷等待下一年;沒有考到理想的崗位,那便延遲一年畢業,備考復習爭取下一年上岸。為了學校之外、畢業之后的目標,他們決心延長呆在學校內的時間。
前耶魯大學教授德雷謝維奇在《優秀的綿羊》一書里寫道:“當今的名校大學生,對成就和成功有著一種被壓迫式的追求:他們都覺得自己必須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從而再接著去追逐下一個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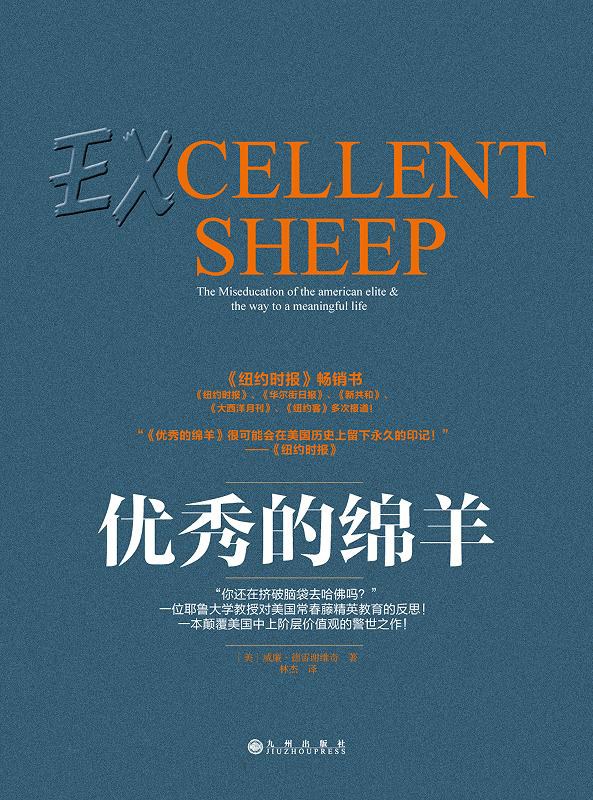
[美] 威廉·德雷謝維奇 著 林杰 譯
九州出版社 2016年
人類學家項飚和袁長庚在《我的這份工,與人類學家聊聊青年與工作》的直播對談里提到了“人生的游戲化”,指的是人生像游戲一樣會遵循一種簡單的“付出即有回報”的規律。考試正是人生游戲化的注腳,也是做了二十幾年學生的大學生最熟悉的思維方式,即我為此付出,就應有所收獲。而當以往的付出沒有獲得滿意回報(工作)、付出即有回報的鏈條被斬斷之時,好像除了再付出一點、多付出一點之外,這些年輕人束手無策。
在這樣的情形下,走出校門猶如跌落懸崖,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而選擇延畢就能待在學校,這成為唯一可以確定的事情。項飚提到,他在與青年的訪談中發現,付出即有回報的鏈條斷裂帶來了青年進入社會的焦慮,一份付出無法獲得一份回報又讓青年人的失落滋生。相信付出-回報的規律,世界就是確定的、可知的、可控的。當規律失效時,部分年輕人在不安與焦慮中更加追求確定性與穩定性,踏上單一的路徑,選擇考試這個熟悉且代表付出即回報的方式繼續前行。
畢業季的學生時常看到“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的寄語。但或許選擇主動延畢的高校生更愿意期待人生是《塞爾達曠野之息》。在海拉魯大地上自由奔跑的林克,無論是點亮神廟、尋找英杰還是拍照、看風景,游戲里的所作所為都會變成可視的數據。但也只有游戲世界才會忠實地遵循付出-回報的單線規律。

確定性真的是確定的嗎?在考公考編以追求穩定確定之時,激烈競爭的不確定性陡增:2023年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招錄筆試計劃招錄3.71萬人,共有152.5萬人報名參加。主動延畢的學生們試圖以時間換取空間,在自己與社會之間劃出安全地帶。但安全區真的安全嗎?或許正如一些社交平臺上的延畢日記所寫的那樣:“留給我的時間也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