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暑假到來,“研學營”在今年屢次登上新聞熱搜。
據新京報報道,市場上出現大量旅游團、研學團,有組織者口頭承諾可以“逛清華校園”“與清華學霸交流”,但實際上只是在學校門口拍照,甚至把清華科技園謊稱為“清華新校區”,帶領孩子們在其中游玩。民生節目“1818黃金眼”也以《“偷渡”進清華,還失敗了……》為題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報道,市民給孩子購買了幾千元的游學項目,核心賣點就是去清華北大游學走訪,一部分人預約成功,一部分人以“清華里面的人”的“弟弟妹妹家屬名義進去”了,還有一部分孩子被保安攔下,在校園外等到晚上11點多。
今年6月30日,清華大學發布了“暑期校園參觀管理公告”,公告稱進入校園需實名預約,且“每人在暑期校園參觀開放期內僅能成功預約1次”。研學營工作人員在采訪中提到,預約名額不僅隨機,而且極少(校方保衛處給出的數據是每天名額為4000人),但“全國可能去了有幾萬個孩子”。

雖然清華和北大的公告中都表示,校園參觀不收取任何費用,希望大家拒絕以任何名義提供參觀服務的有償預約行為,但仍有人在名額緊俏中看到了巨大商機。根據北京大學校友網消息,7月21日,一支名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課”的校外研學團隊,由部分北大校友通過預約同行人員的方式,拆分預約139名學員入校,每人收費10800元,合計收費約150萬元。后來,北大關閉了這些人校友預約系統的使用權限。
不少媒體在關注“研學營”存在欺騙嫌疑的時候,另一個問題也浮現了出來:為什么進入大學校園那么難?曾幾何時,去北大旁聽并不是一件特別難的事情,2007年的《新民周刊》曾記錄當年旁聽的盛況,有人甚至在北大旁聽了11年——文章稱,“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走入校門,坐進課堂,即九九歸一,皆為學子”,一位旁聽生接受采訪時說,“北大幾乎任何一間課堂都對所有人開放。每個系的課程表基本上都可以查詢到,而講臺上的老師看見陌生面孔,也不會追問你的身份。”然而如今,不僅旁聽生幾乎銷聲匿跡,非本校學生、非校友群體進入學校都成為了難題。

早就有不少聲音在呼吁“高校拆掉圍墻”,這種觀點認為,大學資源理應向社會開放和共享。2016年,中國傳媒大學研究生院院長任孟山撰文提到,他在美國著名高校參觀時,“對別人的開放校園深有體會。甚至總是下意識記起,有次我帶孩子路過北京一所著名學府準備進去略加參觀時,被門衛堅決拒之門外的情景,當時給我的理由是學校正在上課。作為一名高校教師,我能理解,但作為家長,我確實不能接受。”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劉永謀也在一次采訪中提及,“中國主要的大學資源都是國家財政公共投入的,應該適當反饋社會,比如校園綠地、運動場所等可以與社會共享”。

從開放到隔絕的大學校園
董子琪:在過去很長時間里,高校大門都是隨便進的。我小時候住在省財經大學附近,也報過學校老師的美術班還有大學生開的暑期班,這也算“研學”了吧?哈哈!當然是門檻比較低的,只是借用了人家的空間而已。那時候對大學印象很好、很自由,就在于校門大開,大學生也很和善。我上大學時,大部分高校也是對公眾開放的,在鼓樓校區經常能看到市民推著小孩來游玩,帶著飯盒進食堂打飯買包子什么的。當然我也借這樣開放的機會進過清華和北大,在人家食堂吃過飯,至今都能回想起那個熱鬧的場面。
之前也聽人講過專門住在五角場、進復旦旁聽中文系課程的美談。但不知道什么時候起氣氛就嚴峻了,再進校要刷卡刷證件,要人工登記,閑雜人等不讓入校,哪怕是校友都不行,更別說上課了,一律不準進,警衛森嚴,讓人不敢靠近也不敢問。因為這樣,過年時跟著留校的同學溜進了幾乎空無一人的學校,激動不已,在校門嚴格管理的時代,這大概算是享受到了某種內部福利吧。
不過這個情況最近又有所緩和,上海的高校又陸續可以進入,但還是有一天內的預約名額限制,可能會因為預約不上,到了門口也只能敗興而歸。我還觀察到一點,高校大門緊閉這個情況不僅對外也對內,現在大學生進出校門都需要刷臉刷卡,過個馬路都得認證,似乎是管理制度借助科技手段更加嚴格了。
可以參考一下某主流媒體人對這個事件的點評(不以人廢言),他將大學緊閉的校門視為疫情時代的陰影與象征,也認為校門攔住的不僅是普通市民,更是大學生向往自由與開放的心。雖然我不太認同校門緊閉是疫情造成的,我看到的大學校門嚴格管理都早于2020年,但覺得這件事他說得也算公允,尤其在于高墻、大門緊鎖給人帶來的普遍心靈感覺方面。
林子人:我覺得大學的管理措施和文化氛圍真的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讀大學的時候,“大學是一種公共資源”應當算是社會共識,我沒怎么注意過是不是有校外人士來旁聽大學課程,但大學里舉辦的公共講座的確是歡迎公眾參加的。因為校園里綠化很不錯(甚至還有一片濕地),我們學校也是附近居民散步溜娃的去處,學生有時會戲稱學校是“XX鎮人民公園”。校外人士只要辦張校園卡,就可以在我們學校的食堂吃飯。
防疫政策放開后,就有人開始呼吁重新開放大學校門,有一種反對聲音是這會增加學校的管理成本,增加風險,影響到學生的學習生活。我覺得挺可笑的。按年齡算,大學生在入學之時基本都已經算是成年人了,大學是他們進入社會前的最后一站,他們既有接觸社會的心智,也需要為之做好充分準備,讓大學校園成為城市公共空間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最自然的讓大學生接觸社會的方法。

徐魯青:中國高校確實應該屬于城市公共資源的一部分,高校師生在法理上只是具有優先使用權,但現在很多情況是“私有”狀態讓使用排序靠后的城市居民被隔離,失去了使用它的可能。
我覺得,不僅高校可以給周邊市民帶來好處,學生和老師也需要和周邊的社區發生關系。如果大學生要么是在象牙塔里好好學習,要么是去CBD辦公室實習,這樣的教育是很匱乏和單向度的。上街頭游蕩,去社區玩耍,與當地居民、小店小販產生關系,對學生與老師來說都會有很多收獲。一直不太喜歡“學生”和“社會人”的二元劃分,回想起來,大學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朋友都是在校外認識的“社會人”。
建筑師簡·雅各布斯曾提出,學校周邊一個社區的消失,對學校的影響大部分是負面的。她說,必須理解在街頭蹲著喝可樂和在專門的游戲室喝可樂是不一樣的,是城市街道讓我們形成對世界的基本理解,在街頭我們會發現自己除了是學生,也是市民與公民,我們會參與進城市的運行模式里,這些影響或許要比教室里的知識教育更加深刻與久遠。
尹清露:我小時候家住在山東大學老校區旁邊,父母都是校友,所以經常帶我進去玩,我也對校園里蔥蔥郁郁的梧桐樹和校門旁邊的大教堂很有好感,依稀記得最早上過的小學英語輔導班也是在山大的外語學院里面,現在想來,這些體驗形成了我對大學最初的印象:隨和而友善。那時經常聽說“保安旁聽課程考上北大”的事例,現在這類北大旁聽生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類價格水漲船高的“研學團”,或者需要有親友關系才能進入校門。
我看到,現如今想要去北大聽課,必須符合一定要求才能成為名義上的“旁聽生”,申請者必須是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的在職工作人員,具有大學程度的文化水平。這也令人疑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課堂秩序,但也從源頭上切斷了許多人接觸知識的渠道。
與校園的物理區隔相匹配的心理區隔
潘文捷:維護學校秩序和滿足市民需求可以兼得嗎?理想的情況是什么樣的?
尹清露:這可能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從公眾的角度來說,我們會覺得進出大學校園是納稅人的權利,大學與社區之間的互動也是社會良好氛圍的體現。不過校方多數是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盡量避免增加工作負擔。我問過一名在南方科技大學做法務的朋友,他表示疫情后學校開放了游客預約制,即使是在這樣的制度下,還是發生了很多人身傷害或者糾紛,無形中增加了校方的工作量。
林子人:是怎樣的人身傷害呢?
潘文捷:有的報道談到過清華開放時女寢被人闖入、北大參觀者隨地大小便等。不過仔細想一想,這并不是本校生和外來人的區別,因為外來訪客也會保持禮貌友好,校內學生和老師也會行為不端。比如2017年8月30日清華研究生院發布的違紀處分中,就出現了“冒用學校名義在社會上參加活動”、“婚外與他人交往”、“在宿舍內留宿異性過夜并毆打該異性”、“在女衛生間進行偷窺”等違紀行為。近年來很多重要社會事件也是在校園內發生的。舉這些例子并非在比壞,而是說人群中總是有好人有壞人,不能將普通游客妖魔化。

我也有一種感覺,高校教育正在把校園之外的人塑造成一種他者的形象。在我讀研的學校里,幾乎每一堂課的老師都會說一些類似于你們是某校的學生、你們和其他人不同、你們是社會精英之類的話,不斷加重學生們的傲慢。所以,當我看到校友,尤其是還在校讀書的學生,首先的刻板印象不是他們成績很好,而是這人八成很自戀。社交網絡上還流行著“如果你認識的人是某大學的,一定會三句話之內讓你知道”之類的段子。當學校不斷加強與社會的物理區隔,也一定有一套適配的心理區隔,以至于很多學生和校友不但拒絕思考校園開放的問題,反而為自己有直通校園的“特權”感到高人一等。
徐魯青:其實也有研究表明,開放校園的安全性反而更高。《打開臨校空間|期待高校與城市相融合的未來》一文就提到了這個問題,相比于不定時的安保巡邏,行人的社會監督能更加實時響應各種突發事件,也更具威脅力。校園面積往往很大,人口密度也遠低于城市人口密度,即便是把大量用于教育的資金投入安保力量巡邏,也會有很多監視盲點。
父母與孩子的高質量互動比什么研學營都強
董子琪:高校不僅有綠地草坪,文化資源也可以輻射周邊,家附近街道開展面向老年人的普法講座,邀請的就是財經大學的老師,書店講座也經常由周邊大學的教師主講,這樣的活動不比要交錢的研學營差。難道說野草一般自由生長、為愛發電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人們更信賴包裝好的課程?
林子人:我從一些報道中了解到,很多參加研學營的孩子年齡非常小。我非常懷疑,就算他們真的能順利進入清華北大校園,對校園氛圍如何、全國頂尖的學生如何積極進取,又能有多少理解能力呢?我小時候雖然沒參加過研學營,但也不可免俗被家長帶去瞻仰過清華大學,實話說,并沒有什么打雞血的作用……認為孩子去好大學體驗一遭就能激發他們的學習動力,恐怕更多是家長的一廂情愿。
我也會覺得,把孩子送進研學營是不是家長用金錢來推卸陪伴責任的舉動,父母與孩子的高質量互動,其實比什么研學營都強。前段時間有一本新書《同窗》出版,作者是一對母女,她們一起讀了《沉思錄》《西游記》《挪威的森林》《伊利亞特》等十幾部文學作品,聊各自的感受,對話自由又平等,令人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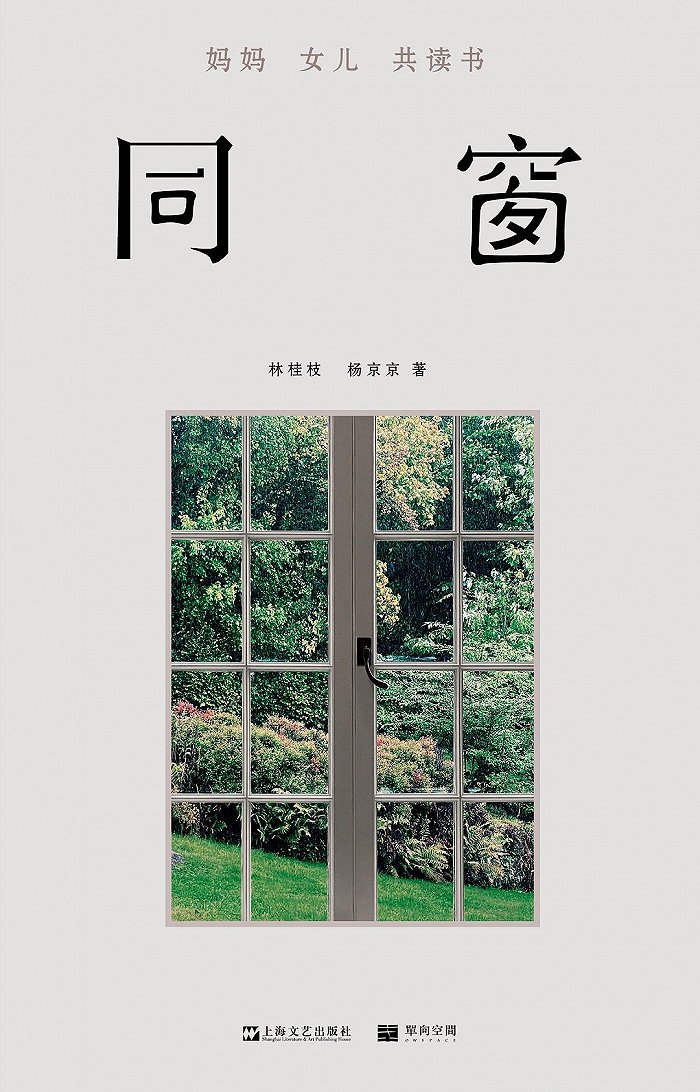
林桂枝 楊京京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3年
父母與孩子之間碰撞出的智識火花,將激勵孩子自主學習、思辨。這才是能讓他們受益終身的“研學”。當然,現在不少家長恐怕也是無奈,本來工作就那么忙了,沒多少精力安排孩子的悠長假期,自然是讓所謂的專業人士負責照看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