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音樂先聲 丁茜雯
編輯|范志輝
伴隨著2023年上半年的結束,井噴的音樂節也因樂迷間的口碑有了三六九等。
7月10日,大量樂迷聲討西安玩世TIME音樂節虛假售票事件繼續發酵。原因則是大量樂迷在多個購票平臺付款時,發現勾選7月16日VIP票便會顯示為7月15日,部分“上當”買到非勾選日期門票的樂迷群體不得不投訴與維權,而這場票務鬧劇也引起西安市監局關注介入。

作為新生音樂節,西安玩世TIME音樂節出師未捷便“社死”受眾圈層,被批為“史上最會欺詐的音樂節之一”。
無獨有偶,剛過去的嵩山音樂節也被樂迷細數包含跳票、抄襲、臨時擴建場地、違約未提供藝人差旅接待等“六宗罪”行為;來自成都的DIGI GHETTO更是因主辦方未按合約履行付款、協調試音且多次失聯無法進行演出工作,無奈宣布退出嵩山音樂節。

凡此種種,也引起不少購票粉絲不滿抗議,直指嵩山音樂節為“最拉胯的音樂節”,更將其置于音樂節鄙視鏈的末端。

不知從何時起,過度飽和的音樂節們的“咖位”,已然漸漸在受眾心中有了好壞劃分,一條無形的鄙視鏈也橫亙這些新老音樂節品牌之間。
音樂節也有鄙視鏈
誠如2019年梁龍曾在《圓桌派》中談及發生在音樂節領域樂迷的互相“瞧不上”現象時所言,群體的不同造就了這種文化現象的升級,而最早中國的音樂節現場也過于緊張,“目前可能從音樂標桿上還是有一點太緊張,你是流行,我是搖滾,他是嘻哈,你是民謠,然后大家在網上也看過那種互相糟踐你糟踐我的段子。”相較于音樂圈不同流派的鄙視鏈還有一定爭議性,音樂節的鄙視鏈則十分簡明——陣容搖滾與否是第一要義。
伴隨越來越多新音樂節的崛起,不乏出現滾哈拼盤、流量愛豆與樂隊拼盤、聲優演員與搖滾樂隊同臺等具有一定爭議性的陣容。而這種牽涉多重粉絲屬性的大型拼湊行為,也使得音樂節不再是搖滾樂迷專屬、獨立音樂的領地,逐漸演化成一場場定位不明的拼盤演唱會。
比如在6月底結束的嵩山音樂節,便因充斥著泰國流量藝人、說唱歌手陣容,且又在售票文案中疑似抄襲西湖音樂節文案自稱“搖滾”,而被西湖音樂節官方吐槽“你也能搖滾?”,更有網友直指“割韭菜的拼盤秀,搖滾和音樂節的名號都被玷污了”。

不可否認的是,即便音樂節本身就是商業產品,但由于與文化元素的深度綁定,自然在不同受眾面前產生了優劣對比。這種搖滾看不上說唱、流量扎堆的現象,在國內音樂節也不是個例。
比如2017年轟動一時的銀川樂堡音樂節上,夜叉樂隊粉絲與李宇春粉絲之間掀起的“看不起”罵戰,本為樂隊當眾提及“春哥”的鬧劇,卻在兩派粉絲的對線中擴大成為搖滾與流行之間的斗爭。如今,涉及流量藝人要素過度的音樂節穩坐鄙視鏈底層,市面上的音樂節更是被樂迷進一步區分為“迷笛音樂節和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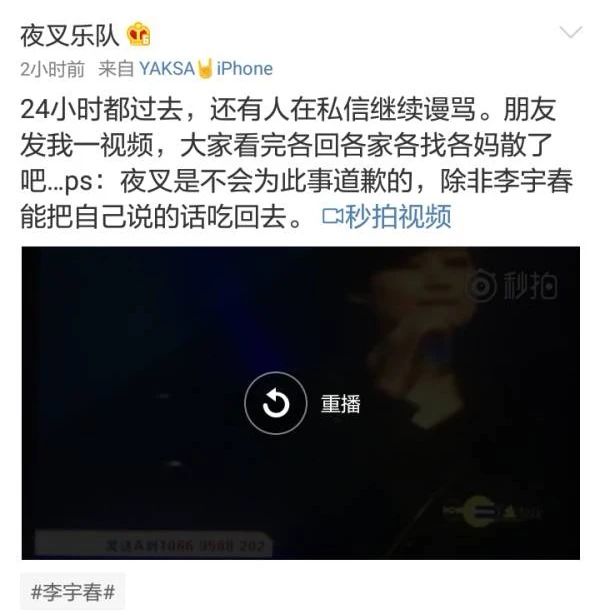
另一方面,海外音樂人、進口音樂節IP與本土音樂人、本土音樂節IP之間也存在一定的鄙視鏈條。
在全球化視野下,歐美樂壇多年來一直處于世界流行文化的C位,這也就導致歐美音樂節IP在很多時候成為內地樂迷追捧的風向標。比如在電音類別下,樂迷們普遍默認歐美先鋒實驗音樂節、歐美主流電音節牢牢占據鄙視鏈頂端,而國產電音節IP則“算不上電音節”;同理,入圍小眾DJ、百大DJ地位也遠遠高于國內DJ、土嗨DJ等。在社交平臺上,還出現了“內地音樂節不如香港音樂節,香港音樂節比不上歐美音樂節”的激烈言論。
此外,部分由新消費品牌冠名或主辦的音樂節,也同樣被一定的有色眼鏡看待,諸如甜啦啦、江小白等新玩家的入場,因達不到與傳統音樂節IP不相上下的操辦量級,甚至大量填充網絡主播、網紅音樂人、流量偶像乃至高人氣相聲演員等來保證高票價、出票率,而被看作是打撈快錢、攪亂市場的行為,且也因身為跨界新手難以保證場地設備標準,引發樂迷的吐槽。

尤其在今年演出市場復蘇以來,愈來愈多的新音樂節扎堆入市,這一“審判”也更為頻繁。不同音樂節品牌在消費受眾心中形成了所謂的優先級排序,不少新生音樂節就被指為“野雞”或“山寨”音樂節,進入音樂節鄙視鏈的底端。比如在社交平臺上,魔音音樂節、芒禾音樂節、嵩山音樂節、雁棲湖音樂節等均因售票混亂、觀演體驗不盡人意等情況獲封“野雞”音樂節。

不難看出,在消費受眾心中實則一直有一桿秤來判斷音樂節的好壞,盡管票價走高是一大影響因素,但制作水準更是被看重的焦點。而正是由于部分音樂節在內容制作、現場體驗上的敷衍,也令樂迷愈加以嚴苛的判斷標準來衡量音樂節。
音樂節需要鄙視鏈嗎?
話說回來,鄙視鏈對于音樂節而言,更像是“苦口良藥”。
音樂節之所以存在鄙視鏈,是由在受眾市場所建立的口碑決定的。據《2022年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演出市場消費主力來自于18歲至34歲的年輕人群,該年齡段在購票人群中連續單年占比超過76%,其中女性則占比超過66%。換言之,這一主要消費人群也決定了不同音樂節在大眾層面的觀感。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緣于在商業化的進程中受到樂迷消費直接影響造成的音樂節鄙視鏈,也是由消費主義所決定的。本質上,這些催生出的鄙視鏈更是受眾在彰顯個性消費、區別主流文化傾向所產生的反主流消費文化。在此基礎上,音樂節各個層面細節的專業化、良心化就成了關鍵因素,即從票務系統開始直至現場演出、售后服務,能否以成熟的運作體系為受眾提供別具一格的消費體驗。
比如在樂迷群體中擁有高口碑的香港Clockenflap音樂節,便是兼具大眾與小眾、陣容劃分清晰、場地設備專業、創辦可穩定交易的Ticketflap售票網站等完善運行的音樂節設置,歷經15年發展后仍然場場售罄、口碑不倒。

更重要的是,來自音樂節市場的現時反饋是促成鄙視鏈誕生的直接原因。回看2023年上半年,音樂節市場競爭已是陷入焦灼,但真正有口碑的音樂節寥寥無幾,整體上仍然是集中在低水準“內卷”的競爭范圍;同質化、快餐化、高票價低體驗等現象愈加嚴重,音樂節同行之間逐漸走向了“互相比爛”。
諸如迷笛音樂節、春游音樂節等因物有所值備受稱贊之時,也有耳浪音樂節、西柚音樂節等玩家以疑似詐騙、跳票等不良或違法行為挑戰市場底線,也令音樂節市場被迫遭受愈加激烈的“污名化”損害。
另一方面,在演出市場爆發期,大批音樂節加大馬力推動線上線下營銷,不免出現貨不對板,不少魚龍混雜的主辦方也拉低了音樂節的市場口碑。眼下,不僅有地方文旅部門加入,無名傳媒公司更是遍布音樂節內外,不管不顧音樂節提上日程之后,卻無法擔起一場音樂節的制作、執行,票務不規范、場地問題等亂象層出不窮。
比如被列出六宗罪的嵩山音樂節,因從宣傳到落地乃至落幕都狀況頻頻,被網友送上“不如不辦”的判詞,甚至一度牽扯違法行為。至于其還能否成為長久的音樂節IP雖然很難下定論,但很明顯的,主辦方及嵩山音樂節這一品牌的口碑已然是在受眾心中“臭名昭著”,無疑是在自毀IP。
很顯然,在積壓三年之后,遍地開花的音樂節使得早已存在的問題更為集中爆發。說到底,集中以回血賺快錢為目的,不重視內容制作和樂迷體驗,自然也難逃被受眾擇選和嫌棄的結局。
更何況,經歷上半年的混亂碰撞,受眾的所謂“報復性消費”也已回歸到了理性階段,個性化、多元化、高質量水準和制作的音樂節將更受青睞,而同質化嚴重的熱門演出陣容,也不再是盲目購票的吸睛手段。
比如天津烏戈世界音樂節,便因高票價、露天沙土地演出且同質化嚴重的演出陣容,門票賣不出去,陷入不得不在開演前一日降價的尷尬境地,被樂迷吐槽“史上體驗感最差的音樂節”。

不過,這也不難看出,音樂節鄙視鏈的排位順序,其實也是消費受眾在鞭策市場迭代、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的方式,助推音樂節市場回到正軌,而不是“萬物皆可音樂節”。
結語
不可否認的是,音樂節在時代的演進中也不斷進化出更為多樣化、更垂類的音樂節品牌。而其中一些愛惜羽毛的音樂節品牌,也不乏以新興選手的姿態成功打入主流圈層,或是擁有穩固的口碑,積淀出IP價值。
就像老狼對刺猬樂隊和斯斯與帆的合作感慨,“民謠和搖滾是有所謂的鄙視鏈的,我覺得音樂的相互理解和融合是很高的境界”,音樂節之間也是如此。
但歸根結底,音樂節鄙視鏈的存在代表著受眾圈層的分化趨向,同時也映射出受眾正在有意識衡量音樂節的性價比,不再過分盲目,而受眾的審美也對音樂節提出了一定的品質要求,而這并非是由所謂的優越感決定的。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被鄙視鏈敲響警鐘的音樂節市場能夠真正“向上內卷”,而不是毫無意義的擺爛式賺快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