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從前的考研名師、如今的高考志愿專家張雪峰在直播中為高三考生和家長指點迷津,提出了幾點有針對性的建議:生化環材不要碰,哪怕是名校;文科優先選漢語言和思政,大一就可以開始準備。張雪峰的幾條建議經總結后在網絡走紅,也為廣大家長與學生盛贊——“打破信息屏障”、“講了大實話”。支持張雪峰的過來人也不在少數,微博大V Fenng 就明確表示,窮人家的孩子應該踏踏實實把安身立命的本事學好、賺錢養家。
與張雪峰的志愿填報建議幾乎同一時期,生物學家顏寧在微博上表達了對優秀高校畢業生的失望。在近期的一次博士生推免面試上,她提了一個開放性問題,然而在場同學無一人回答令她滿意。她的問題是,“假設十年后,你已經成為一位能獨立帶領實驗室的博導,你最想探索的科學問題是什么?換句話說,這輩子有什么科學問題或者技術難題,能解答或突破就覺得今生無憾了?”這些同學的課業成績都很優秀,有的人發表過不止一篇論文,為什么卻沒有dream big&dream high?顏寧在微博中發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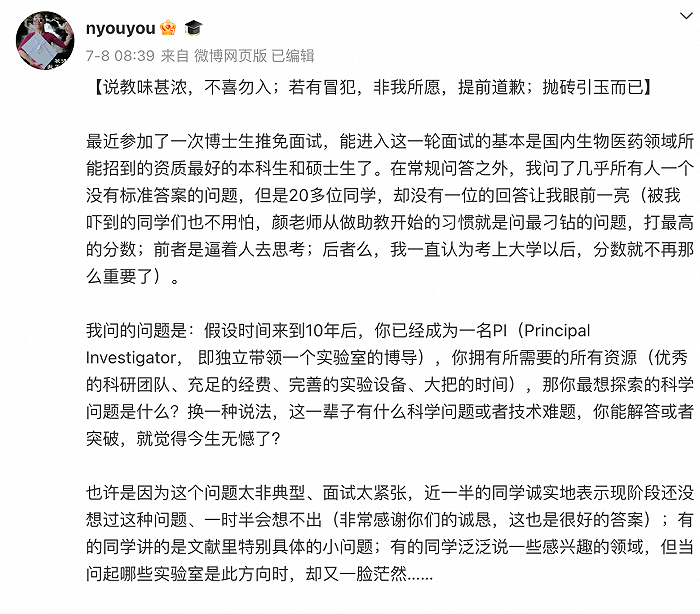
一邊是志愿專家張雪峰, 一邊是生物科學家顏寧,同樣是出于對高等教育的關切,二人卻指向了不同的道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張雪峰的大實話以及顏寧的夢想遠大?
“性價比”與“紅利至上”的大學教育
張雪峰為人稱贊的一點,在于切身實地為考生著想,讓窮人家的孩子分數不白考,填報到最具有性價比的專業,進而掌握安身立命的本事。“性價比”與“實實在在的本事”指向經濟利益的考量,也符合了“上大學是為了就業”的意愿。這一點本身無可厚非。在中國的高校教育及就業現實里,計算機、醫學和師范類受到張雪峰及百度985吧的追捧,正因為這些學科不“浪費”學生的分數,畢業生收入較高,身份也較為體面。

不僅學生在乎“性價比”,“務實”已經成為全球高校競爭的關鍵因素。英國劍橋大學思想史、英國文學教授斯蒂芬·科利尼在《大學,有什么用?》(Stefan Collini)中寫道,現如今不僅大學的學科設置與科研需要證明滿足經濟需求,大學工作人員在為大學辯護時,也紛紛證明自己的學科對國計民生有所貢獻。一方面這樣務實的要求直接導向了對經濟效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令人們對務實的語言習焉不察,默認有助于“經濟增長”和“提升國際競爭力”正是科研的目標。
對于后者的追逐引發了大學國際排名的激烈競爭,國際排名的上下變動都會引發民族自尊心的震蕩。在英國,人們會關心牛津和哈佛到底誰排名更高,就像在中國,清華北大超過了多少美國高校會登上熱搜。大學排名如同國際經濟競爭的縮影,人們對此信賴又焦慮,仿佛全球大學之間存在著“零和博弈”,別國大學的成功會損害本國的學術表現。

[英] 斯蒂芬·科利尼 著 張德旭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3-6
可問題是,“如果大學從事的活動要滿足經濟需求,那么經濟又該滿足誰的需求?”科利尼問道,如果說經濟提供了財富使人們能做非常重要的事,那人們得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換言之,繁榮(prosperity)本身足夠成為目標嗎?如果將經濟活動看作一種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一種積累資源的方法,那么繁榮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經濟和財富提供了提升人類理解力需要的資金。理解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如若不然,科利尼寫道,我們就可能走向凱恩斯譏諷的,“若不帶來紅利,我們連太陽和星星都能關掉。”
“紅利至上”的思維不僅影響到大學的評估,也發展至對科學與人文的學科評價。百度985吧中回蕩著“文科無人權,計算機人上人”的聲音,雖然是句玩笑話,也間接透露出了某種價值傾向。回報率影響了人文學科的聲譽,因為科學領域的發現和發明能夠直接改善人類的境況(不過作者專門表明,純數學或天體物理學除外),而人文學科的意義不能被輕易概括或理解。人文學科適用的評價體系應當是判斷而非計量的,這指向了人文學科中富于個性的部分——人文學科的說服力總與個人聲音相連,某種程度上取決于批評者的性情氣質與文學技巧。抹煞掉這些部分、僅僅套用數字指標是尷尬的,就像不能用粉絲數量和電視劇改編來評價文學作品的成就一樣,如果用莎翁戲劇的票房收入為莎士比亞辯護,恐怕也顯得十分無力和荒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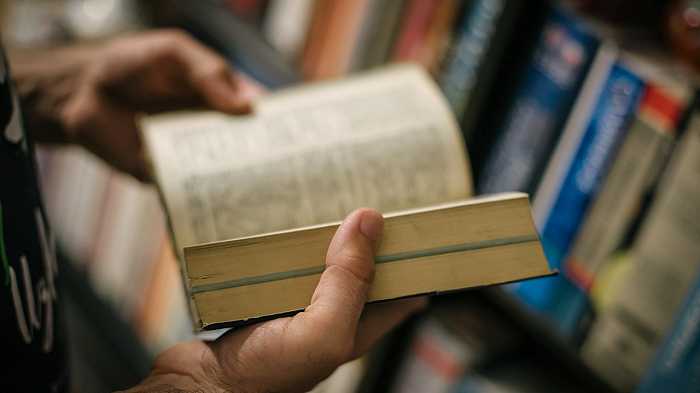
“紅利至上”還會帶來另一個難題,就是到底應當如何決定有多少人去從事相應的工作,或者說,應該怎樣評估一個冷門學科的市場。比如,“亞述考古學領域應該有多少位學識淵博的學者呢?”或者用張雪峰的話說就是,“世界語的市場到底有多大呢?還有必要學嗎?”
對此,科利尼回應道,與其尋求精確計算,不如反問:對于這樣的活動,所謂的市場真的存在嗎?科利尼舉例說,本科生對古代伊朗語言與文學的研究沒有所謂的需求,但這門學科不應該被放棄,因為它擁有強大的學術傳統,也連接到許多相關的智識與文化領域,還有許多評論現代伊朗的學者需要了解古代的文本、近東和中東領域的研究需要簡介伊朗研究的成果,“我們決不能失去這個冷門學問,不僅需要教授和培養該學科的下一代學者,還需要向社會推廣自己的專業知識。”
人文學科的工作目標不是知識,而是理解
顏寧期盼的是夢想遠大、求知若渴、走出原創道路的學生,她在微博中寫道,(優秀的科研者)不一定要從文獻里尋找科學問題,也不必因循實驗室的套路和方向,不給自己設限到自然、臨床和社會中觀察,會發現時時都有好問題。這點出了紅利思維所不能通向的求知道路,以及大學智識生活理應如何。如果引用哲學家陳嘉映對良好生活的論述至此,那就是通過高等教育,有人希望過上掙錢養家、送孩子出國的好日子,而追求智識生活的人不想要好日子壓倒一切,不滿足于過平穩重復的好日子。
顏寧的期盼亦點出了高等教育的使命,即鼓勵智識發展。大學教育與專業培訓的區別就是,培訓僅僅傳遞信息,而教育把這些信息相對話、關系化、并不斷提出質疑。科利尼在《大學,有什么用?》中指出,在這個意義上,教育鼓勵學生認識,知識并不是固定的、永恒或普遍的。大學之所以不同于培訓機構,其本質就在于大學鼓勵的智識生活不是單一的、有先前預判方向的或明確可知的。當知識的探索是開放的,而非受制于驗證假設或修正錯誤,就能夠導向更深入的理解。大學作為一個受保護的空間,鼓勵學生了解任何知識的偶然性及其與不同知識的關聯性。要做到這點,教師也需要不斷超越自己所教授的知識范圍,因為在陌生的領域,教師將無法預判哪些方向有效、哪些無效。

在人文學科領域,這樣的探索更加具體,“技能+知識=信息”并不是一個對人文科學適用的公式;如果非要用公式,也應當是“經驗+反思=理解”。科利尼的提醒相當有趣,人文學科的工作目標,最好被描述為理解,而非知識。理解與知識的區別就在于,知識在某種意義上是客觀的,不管你是否在意,它都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爬到知識倉庫的頂端,而理解是一種人類活動,取決于理解者的素質。
順著這個思路,我們可以發現人文學科中對話(而非說教與耳提面命)的重要性。與科學發現新知不同,科利尼說,人文學科經常是在更多的點上激發人們的理解與共鳴,優秀的思想往往是與早已作古的人物的思想再次交流與碰撞的結果——新思想不僅能對舊思想做出充分的思考,也能對其有敏感而積極的反應。陳嘉映也曾在書中回答“對話為何重要”的問題:對話的目的不是科學真理,而是對話式的、翻譯式的理解,因為在對話中,人們總在調整自己的視角,了解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才將真理說明白,達到放棄唯一性,堅持真理性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