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彩色旋風迅速席卷了整個夏天,就像是一場久違的情緒釋放。從“報復性出游”“報復性看演唱會”,如今年輕人終于迎來了“報復性穿搭”。放在以前,不少穿搭博主會苦口婆心地勸說:同時穿到身上的顏色,不要超過三個。如果五顏六色地走在街上,大概率會被劃到“非主流”那撥。
但現在,迎面而來的路人會像對上暗號似的來一句:“快看,是多巴胺!”
文 | 肖思佳
編輯 | 辛野
運營 | 橙子

“快看,是多巴胺!”
換上新衣服的那天,30歲的北戈在合租房里興奮地蹦了半小時。
這是她第一次嘗試往身上堆這么多顏色——一件牛油果綠的抹胸加開衫外套,外加一條芭比粉的褲子。她打開音樂App,切換到了告五人樂隊的歌曲,提前開始了一個人的狂歡。
這套“辣妹裝”是北戈專門為音樂節準備的,花了將近400元。彼時距離五一假期不到一周。她早早就在線上搶好了成都仙人掌音樂節的門票,只等假期一到就立馬奔去現場,來一場沉浸式的“精神馬殺雞”。
18歲的小涵,也在不久前大膽嘗試了一種“很新的穿衣風格”——從上到下依次是:彩虹色的圍脖,玫紅色的背帶短褲,和一雙粉色的毛絨腿套。穿上衣服出門的那一天,她既忐忑又期待,得到了許多人的側目注視。
這是她前所未有的體驗,每走一段路,就會收獲一句“好看!漂亮!”的夸獎。贊美者無一例外都是女性,包括一位帶著小孩的媽媽,也“哇”了一下。起初,小涵覺得很不好意思,她有著難以擺脫的容貌焦慮,覺得自己臉太大,鼻子也不高。每次拍照,她要尋找特定的角度,搭配精心畫好的妝容,但成片效果仍然不能讓她滿意。
這一次,捕捉到肯定的目光后,她向前走的步子都堅定了些。
回到學校寢室后,小涵在小紅書上發了一條動態,附上了幾張精心拍攝的寫真照,標題是“學習多巴胺穿搭的第一天!”。吃個飯的功夫,再拿起手機時,點贊數已經突破了99+。
“多巴胺穿搭”,今年夏天最火熱的流量密碼之一。截至目前,小紅書話題“多巴胺情緒穿搭”瀏覽量達3.2億次,抖音話題“多巴胺女孩穿搭”播放量則超過93億。剛剛過去的618期間,“多巴胺風”甚至以近1000萬的搜索熱度,力壓第二名“TFBOYS十周年應援”和第三名“梅西球迷同款尤尼克斯球鞋”,穩居淘寶搜索第一。

▲ 淘寶熱度榜單。圖 / 淘寶截圖
2023年初,時尚博主陳采尼發布了一條視頻,預測“多巴胺穿搭”將成為今年最熱門的穿衣風格。簡而言之,這是一種通過身穿大面積的彩色服飾,來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以此來喚醒快樂心情的做法。
早在2021年下半年,這股風潮就已經在歐美國家開始流行,2022年,instagram上出現了不少多巴胺穿搭的話題。國外社交媒體Pinterest宣稱,多巴胺穿搭將成為席卷未來的潮流趨勢,許多大牌秀場上也運用了這一元素。
多巴胺穿搭在國內的全面走紅,則是在今年4月,短視頻博主@白晝小熊發布了一條卡點視頻。畫面中,她身穿不同風格服飾,在各個場景中行切換、行走、對鏡自拍。鮮艷的穿著,花哨的配飾,可愛的笑容,再加上富有感染力的音樂,被網友戲稱為“行走的QQ秀”。這條視頻在平臺上獲得了超350萬次的點贊。這也是她入行三年以來,點贊首次破百萬的“大爆款”。
小涵買的那套衣服,就是“白晝小熊同款”。這也是全網多巴胺穿搭中,最出圈的一套造型,除了色彩搭配外,精髓在于——一定要把頭發扎成兩個鼓鼓的丸子包。

▲ 小涵的“白晝小熊同款”同款穿搭。圖 / 受訪者提供
彩色旋風迅速席卷了整個夏天,就像是一場久違的情緒釋放。從“報復性出游”、“報復性看演唱會”,如今年輕人終于迎來了“報復性穿搭”。放在以前,不少穿搭博主會苦口婆心地勸說:同時穿到身上的顏色,不要超過三個。如果五顏六色地走在街上,大概率會被劃到“非主流”那撥。
但現在,迎面而來的路人會像對上暗號似的來一句:“快看,是多巴胺!”
需要一點色彩
北戈最初并沒有接觸到“多巴胺穿搭”的概念。她只是本能地覺得,“我的生活需要一點色彩了”。
去音樂節蹦完迪,北戈把用了兩年的小狗頭像,換成了自己在音樂節現場的全身照。照片里,她穿著那件衣柜中唯一的亮色“辣妹裝”,笑容燦爛。兩周后,她又去理發店將兩側的頭發挑染成了寶藍色。直到五月底她去做美甲,美甲師看著她遞來的彩色樣式圖,脫口而出“多巴胺”三個字時,她才發覺原來這已經成為了一種人人熟知的時尚風格。
盡管“多巴胺美甲”之旅,最后以翻車告終——暈染不到位的五彩色,生硬地貼在指甲蓋上,像極了小孩用水彩筆涂下的惡作劇——可北戈還是止不住地開心。第二天上班,她和往常一樣坐在狹窄的格子間里,每次低頭,就能看見在鍵盤上跳動的彩色。

▲ 北戈的翻車美甲。圖 / @小石的北京周末
“多巴胺穿搭”的走紅,并不在孟亮的意料之外。
作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孟亮開設過《消費者行為學》的課程。他告訴每日人物,類似的消費流行趨勢曾經多次出現在人類歷史中,比如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迎來了以華麗聞名的二十年代。
在他看來,“多巴胺穿搭”的底層心理機制是“具衣認知(enclothed cognition)”。這一理論認為,人們會為特定服裝賦予相應的屬性,這一聯結非常強大。當我們穿著這些服裝時,這些聯想會改變我們的感受,甚至改變我們的行為方式。
《時尚心理學》的作者、行為心理學家卡羅琳·梅爾(Carolyn Mair)也認為,衣著是人類感知的基礎,反過來也會影響人們的自我價值感,并最終影響人們如何看待自己。
疫情期間,很多人將衣服的實用性置于審美性之上,而在新冠結束后,消費者自然會對所有能帶來感官愉悅的事物,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興趣——包括新的、時尚的、色彩鮮艷的衣服。
北戈一度覺得,生活的底色是暗沉的、灰色的。在她的記憶中,上一次參加音樂節已經是四年前的事,疫情尚未開始,她也還沒開始北漂。
兩年前,北戈辭去了大連穩定的工作,不顧家人反對,只身來到北京。和每一位揣著理想北漂的年輕人一樣,她經歷了漫長的認清現實的過程,互聯網小公司的工作賺得少、強度大,她像一只陀螺,從早旋轉到晚,天天都要轉到十點才能下班。
合租的生活也讓人疲憊。她住在五環邊上一套四室合租房內,隔音很差,總是能在半夜被隔壁租戶打游戲時的叫罵聲嚇一跳。
有一次,她加班到夜里兩三點,剛剛躺下,就聽見門口先后傳來了巨大的關門聲、“噠噠噠”的急促腳步聲,以及,劇烈的嘔吐聲。過了一會兒,直到馬桶嘩啦啦的沖水聲將一切都淹沒,屋內才恢復了寧靜,但她卻睡不著了——第二天,不出所料,她看到廁所的地面上,還殘留著些許飛濺出來的嘔吐物殘渣。
她想過要搬走,曾在一天內連看了七八套房,最終還是作罷——條件好的、心儀的房子,不是沒有,可是全都超出了預算。她還換過兩次工作,但工資并沒有上漲多少。她認為自己尚且不具備為心儀的生活買單的能力。
就是在這時,“多巴胺穿搭”闖進了她的生活。很難說,一套衣服能真正改變什么,但北戈的確覺得,自己的心情被點亮了。
卡羅琳·梅爾相信,讓人感覺舒服的不是服裝本身,而是與之相關的積極聯想。
孟亮則提到,當年輕人因經濟條件限制無法進行大宗消費時,手中反而會有“小閑錢”,可以去購買一些“廉價的非必要之物”。作為時下的時尚潮流,“多巴胺”單品價格不貴,可以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欲,讓他們以較小的代價獲得即時滿足感,能對消費者起到安慰的作用。
相比起從中產圈里風靡起來的露營、滑雪等消費活動來說,通過“多巴胺穿搭”來獲取快樂的門檻更低。幾十元的彩色T恤,和幾塊錢一把的彩色發夾,消費起來并沒有太大負擔。在消費心理學上,這也可以被歸結為“口紅效應”。
“不要叫我多巴胺女孩”
這場聲勢浩大的彩色狂歡中,并非都是積極的情緒和贊美的聲音。
北戈覺得,這種彩色的穿衣風格其實一直都存在,只是又被重新定義了一輪。都說時尚是一個輪回,曾經流行過的非主流、原宿風、泫雅風,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些喜歡小眾穿搭的人群,更覺得“多巴胺”的火爆莫名奇妙。
跑跑魚就是其中之一。她喜歡個性化的著裝,衣柜里從復古長外套、朋克金屬風到新中式旗袍,什么樣的衣服都有。通常,她每天穿什么都看心情,并沒有什么規律。唯一的共同點,只在于服飾搭配上,色彩的豐富性。
但“多巴胺”走紅后,一切含有彩色元素的穿衣風格,似乎都要被這三個字統稱概括。
有一回,跑跑魚穿了一身藍綠色裙子,搭配了粉、黃、藍相間的重色眼影,還帶了一個紫色的發夾。地鐵里碰到幾位初中生,指著她大喊:“快看,是多巴胺!”當時,她覺得有些不舒服,但只是和朋友對視了一眼,尷尬地笑了笑,小聲地抗議道:“不要叫我們多巴胺女孩。”

▲ 跑跑魚的彩色穿搭。圖 / 受訪者提供
PP龐是一家原創設計手作的品牌主理人,她也注意到這類現象。原本,她對自己產品的定義是:你是什么風格,配飾就是什么風格。但現在,她總會被前來選購的顧客問道:“請問這是多巴胺風格嗎?”
因為就讀于哲學專業,PP龐本能地更關注這類現象。在她看來,商品或者說資本,似乎需要通過這種標簽化的行為,來打造一種消費符號,制造顧客對商品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并非基于自身的真實需要或感受,而是基于某種外在形象的建立。
“這時的個人不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被人為打造的一種社會景觀。”她說。
事情的確朝著熟悉的方向發展開去。隨著話題的不斷發酵,不斷有新角色加入“多巴胺家族”。多巴胺文學、多巴胺手勢、多巴胺盲盒、多巴胺手機殼……年輕人甚至連手串都盤起了多巴胺款的,大有“萬物皆可多巴胺”的趨勢。
商業的延展似乎是每股潮流一定會有的歸宿。對風向敏感、想要抓住年輕人每一次購物沖動的消費品牌,不會錯過這次營銷良機。
比如星巴克,雖然沒有提到“多巴胺”這三個字,但嘗試了以更鮮艷明快的色彩推出新品。先是在五月底推出粉粉、莓粉、粉紫、玫紫四款新品生咖,又在高考季聯合B站推出粉、綠、藍、黃、白五款“聯名拋瓦手環”。就連店內的咖啡師們,也換上了最新款的火龍果色圍裙。
更早的還有三月底就推出新品“櫻花烏龍”的霸王茶姬,不僅將品牌的全網logo和線下門店裝飾換成高飽和的亮粉色,還以“多巴胺粉”為關鍵詞,聯合一眾媒體將話題傳播開去。
盡管知道這是某種噱頭,大家也樂于嘗試。對此,孟亮解釋,參與“多巴胺潮流”可以幫助消費者獲得社會認同和歸屬感,“年輕人在社會化媒體上更活躍,他們受到各種時尚博主、潮流達人和明星等意見領袖的影響,也更渴望得到社會認同與他人關注,因而更有動力參與到穿搭潮流中”。
但另一方面,顏色、服裝和情緒間的聯系也很復雜。不同的語境和獨立個體的主觀感受,都會對情緒產生影響。
小涵發在小紅書上關于“多巴胺穿搭”的狀態,最終吸引來幾百條評論。有夸她的,也有人說自己也想嘗試,但缺乏勇氣。還有刺耳的聲音,質問她為什么要跟風模仿博主的穿搭,覺得她并不適合這身衣服。
剛剛漲起來的信心,又被拽回谷底。小涵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適合“多巴胺穿搭”。“畢竟確實如評論所說,我皮膚不夠白,也沒有白晝小熊那么瘦”,她有些沮喪。
三天后,她又發了一條動態,“普通人只能穿黑白灰嗎”。她希望鼓勵那些渴望穿得鮮亮,卻害怕被他人指點的女生,勇敢去嘗試自己喜歡的風格。只是沒了顯眼的“多巴胺”三個字,流量也一落千丈。相比起前一條800多個的點贊數,新的動態只得到30個點贊,7條評論。
風波過后,小涵再沒有完整地穿過那身衣服了。

▲ 小眾群體的反對聲。圖 / 小紅書截圖
僅存的掌控感
盡管“多巴胺穿搭”在互聯網上很火,但不得不承認,現實生活中,真正敢于將高飽和、高亮度顏色服裝穿出門的人,還是小部分人。
不少受訪者表示,只有在特定場合,比如迪士尼樂園、野餐或live house,才會穿上色彩搶眼的衣服。一旦脫離了這些特殊的場景,過于鮮艷的穿搭只會讓自己覺得尷尬、“社死”和無所適從。比如,上班通勤時,北戈從來不會將兩件亮色的服裝,同時搭配在一起。即使穿上了衣柜里唯一的一條粉裙子,也會找另一件黑色或白色的上衣“壓一壓”。
對于那些勇于打破常規的人來說,她們也不是天生無所顧忌。
跑跑魚至今還記得,中學時期因容貌問題而遭受到的挫敗感。青春時期,她和大多數女孩一樣,生活在外界的評價里,敏感、脆弱、容易受到傷害。
那時流行黑長直發型,她也跟風將頭發拉直。課間,她和同學走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背后傳來戲謔聲。一個男生喊道“去看看”,話音剛剛落地,兩道帶風的身影就出現在了眼前。對方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帶著嘲笑的語氣說:“原來是背影殺啊。”接著,又像風一樣在大笑聲中跑走了。只剩下她愣在原地。
有一段時間,她成為一個沉默的人,不發表言論,不與人交流談心,習慣性地封閉自我,“后來好起來,可能是因為我開始好好打扮自己了”。通過穿衣風格的變化,她又重新開始面對復雜的生活。

▲ 跑跑魚的彩色穿搭。圖 / 受訪者提供
在卡羅琳·梅爾看來,衣服是幫助人們保持身份和常規感的一種方式,“缺乏控制感是生活中最大的壓力來源之一。為自己選擇穿什么衣服,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掌控感”。
如果工作和生活都無法被改變,北戈覺得,至少在穿什么衣服,做什么發型上,自己還能找回一點兒生活的主動權。
在乏善可陳的學生時代的回憶里,她總是穿著一模一樣的校服,梳著多年如一日的馬尾辮,學校和家里兩點一線。高中最后一年,她任性地剪了帶劉海的短發,遭到了母親的數落。
如今,她已經過了30歲,終于明白對自己來說,更重要的是什么。
幾天前,父母來北京看她,母親看到了她挑染的發色,照例抱怨了兩句。在等候地鐵的過程中,她看到對面站臺上,恰好站著一個染著薄荷綠發色的女生。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她,那么亮眼,那么動人。
她指著那個女生對母親說道,以后我也要把頭發全染成藍色。母親大吃一驚,脫口而出:“絕對不行。”但北戈已經不放在心上了。
不僅僅是頭發。未來,她還要再買更多彩色的衣服,嘗試更多鮮艷的穿搭。即便穿上身后,小肚子若隱若現,她也不在乎。
“我已經錯過太多夏天了。”她說。
(除孟亮外,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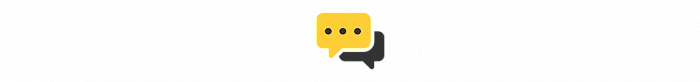
每人互動你怎么看待“多巴胺穿搭”的走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