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今日上午,作家王安憶與余華在華東師范大學思群堂的對談上再次談及先鋒文學,而王安憶認為余華是先鋒作家里唯一一位清醒自覺地找到小說倫理的人。“他開始根據他的現實邏輯敘事了,而很多先鋒作家很快就折戟沙灘,包括馬原和孫甘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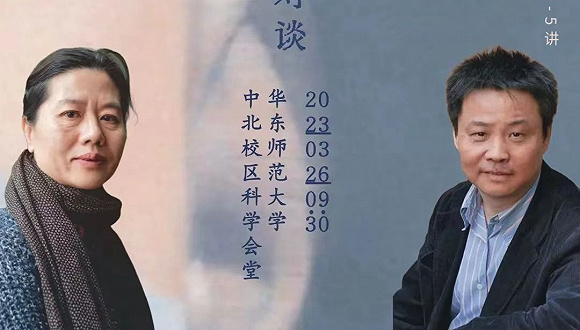
余華:假如沒有現實基礎,文學像斷了線的風箏會飄走
王安憶回憶最初看余華的作品《現實一種》,正是先鋒文學風行的時代。那時她對于先鋒文學的風潮抱有警惕性,因為懷疑這種敘事的方法不能持久,同時也懷疑其可讀性,因為讀作品一定從常識出發,而先鋒文學的世界跟人們有距離。
王安憶將余華的文學創作從先鋒寫作到敘事小說的轉變形容為從陷阱中跳出,“1980年代我們已經封閉了那么多年,每個人都要反抗,做出與前輩不同的姿態,但他能跳出來,既服從現實邏輯,又能從中跳出,大部分人是不能脫身的。”
而王安憶對于余華作品的評述,則讓后者回想起1998年他們一起在中國香港地區等待轉機去中國臺灣地區的情形。余華還記得25年前的一個場景——王安憶找到他說,“余華,現在你的小說讓我看到人了。”

“余華給人的印象就是找爸爸的男孩子,他的很多小說也都是寫父子關系。” 王安憶也對那次的經歷印象深刻,當時中國作協組織一批中國大陸作家從北京出發去臺北,當時還需要在香港轉機,這些作家第一次去臺北,感到十分茫然。“大家下了飛機在機場走,迎面走過來一個看起來像浙江農民的人,大包裹小行李的,他看到余華一下子就笑了,說你是去臺灣(地區)找你爸爸吧。可見余華給人的印象就是找爸爸的男孩子。”王安憶說道。
余華承認,在寫先鋒小說時,他覺得自己是筆下人物的主宰,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但寫了《活著》和《在細雨中呼喊》后,才感覺到人物有自己的命運。“前面的作品里人人以符號的方式出現,后面的作品人以人的形象出現。”余華講道,所有的文學,不論是寫實還是荒誕的,假如沒有現實基礎,會像斷了線的風箏會飄走、被人遺忘,所以現實是文學的基礎也是出發的地方。作家總要去現實里提取素材,但提取出素材之后處理的方式不同。他以魯迅的小說《風波》為例,講述小說與時代的關系。

“《風波》里我認為寫的最好是趙七爺,皇帝坐龍庭了他要把辮子放下,革命軍來了他要把辮子盤上去。魯迅洞察到了辮子這個細節,寫出了普通民眾如何面對時代的巨變,這個細節就足夠了,不用再往前推了。”而有些素材光提煉還不夠,還需要再推一步。余華以澳大利亞作家理查德·弗蘭納根的小說《河流引路人之死》為例,“小說的結尾寫得很漂亮,講的是父親如何把母親騙到塔斯馬尼亞島。接近島嶼的時候,有一段描寫,寫島上海邊那破舊的歪歪斜斜的房屋,以及陰暗的天空,寫得都很好,但顯然還不夠。作者往前推了一步,兩人下了船,見到一個男人正在跟電線桿吵架,他的老婆拉住他,不要讓他丟臉,他說滾開,這是私人談話。兩人遠涉重洋來到這個破地方,本身已經非常不安,下了船聽到的又是這樣的對話,這是寫作中的一種方式。 "
王安憶:當下又有了一種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寫作風潮
與余華所說的將現實再推一步的寫法相關,王安憶進一步表示,如果不是有傳奇性吸引的話,作家何必要去寫枯乏的日常生活呢?她還是渴望著書寫一個平民英雄,戰爭中英雄很多,日常中英雄是很難的。她從自己的寫實主義寫作中生出的體會是,寫作者太被日常邏輯纏繞,特別不容易生長。而據她當下的觀察,目前又有了一種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寫作風潮,“這種寫作對日常有莫大的尊敬與肯定,也有反啟蒙的意義,不能到達精神的一種境界。”王安憶說,前段有人介紹她看小說《同和里》,這部小說寫上海市井生活,小孩子在革命波動里的狀態,小說的細節特殊,故事的家庭也很特別,但一切都使她感到和現實生活一樣地厭倦。

小說中有一個細節,存在著升華的可能,但作者把這個細節給放過了,或許也沒注意到,王安憶有些可惜地說道。
“故事里有一個老太婆過著很疲乏的生活,她住在老虎罩的樓上,親人也很少,忽然有一天,她搬著一條長凳要去小石橋跳河。跳河時有人問她怎么了,她說沒意思,要自殺。老太婆也不是個知識分子,也不是個赤貧到沒法生存的人,她也沒受到很大的凌辱,這個市井中人忽然有一種靈感和神思,覺得做人沒有意思。關于活著沒意思的問題,知識分子成天考慮,但考慮的都是抽象的,老太經過了那么多年忽然要跳河了。”當下有一種寫作非常普遍,它強調日常生活、普通人的不容易與堅忍,但放過了升華的可能。重視傳奇性不僅需要想象力,還需要對世界的認識。比如《許三觀賣血記》這樣的故事在憶苦思甜的傳統里看過太多了,但余華有一些特別的處理,讓主角老實人接納了不是自己親生兒子的“兒子”,還要這個兒子在親生父親去世時去喊魂。
王安憶在《許三觀賣血記》里讀出了傳奇性,2021年余華出版的《文城》也被評論家以“傳奇”定性。對此,余華說,《文城》的傳奇與超越日常的傳奇有些不同,但也有相通之處。他故意將《文城》寫成傳奇,因為年輕時讀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很受鼓舞,再加上《文城》的年代久遠很適合用傳奇小說的方式書寫。
余華:描摹生活時,小說家比詩人和理論家靠譜
余華發現傳奇與敘述關系密切,2022年他錄一檔電視節目,制作方讓他與蘇童、西川待在島上,派歐陽江河和祝勇去了漁村,那兩人回來給他們描述漁村的情形卻不能令余華滿意,“歐陽江河用詩人的方式描述完全不靠譜、祝勇用理論也不靠譜。回來看到王安憶的《五湖四海》寫的就是水上漁村,對漁村一展現就清晰了。描摹生活時小說家比詩人和理論家靠譜。”一種傳奇如王安憶所說的生活中的傳奇,另一種傳奇是時間段拉長的傳奇,古代歷史中的刺客故事就是拉長了時間段的傳奇,“我不明白為什么那幫笨蛋老去編荊軻,其實最好的是豫讓和聶政,聶政是快刀斬亂麻,豫讓是鈍刀子割肉。 ”余華說。
王安憶:ChatGPT這樣的人工智能涉嫌抄襲
對于時下熱門的人工智能ChatGPT王安憶與余華也有各自的評述。“ChatGPT這樣的人工智能涉嫌抄襲,因為要搜索內容。”王安憶說。余華雖然沒有用過ChatGPT,但是使用過國內的類似軟件,不太好用。“我首先問它,文學是個什么東西,結果搜索出現故障。我就問文學有什么意義,搜索又出現故障,可能故障就是最好的回答。”余華認為,人工智能大概能寫出中庸的小說而非充滿個性的小說,而在文學作品里優點與缺點其實是并存的。很多偉大作品都有敗筆,ChatGPT沒有缺點,反過來也沒有優點。像是卡夫卡的《變形記》有明顯的敗筆,余華說,格里高爾的尸體處理得太草率了,“當甲蟲終于死了,一家人終于過上正常的生活,你不要輕描淡寫地說已經處理掉了,那么大一只甲蟲,要寫如何艱難地把蟲子的尸體從門里移走,除非你前面寫得比較跳躍,而不是絲絲入扣的。”余華覺得這點是卡夫卡的疏忽,而他寫小說時也會有忘記人名的疏忽,“人腦會犯錯誤,這也是人腦最可貴的地方,因為人不按常理出牌,我認為人工智能起碼現在不會對我和安憶構成什么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