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早在1985年,中國就已經出現了第一部關于代孕的科幻小說,即萬煥奎的《代人懷孕的姑娘》。在這個故事里,科幻作家預見到了商業代孕在今天引發的爭議。在中國的科幻小說歷史上,作家們是怎樣想象未來的生育和家庭的?在日前舉辦的“科幻視野下的親子關系與人類未來”講座上,科幻作家寶樹認為,隨著科技發展,親子關系面臨著現代轉型與危機,這些現實在科幻作品中已有反映和投射。
妊娠技術和基因技術
不少生殖技術原本是科幻小說中的情節,如今已經變成了現實。寶樹把這類技術分為兩類,即妊娠技術和基因技術。前者包括人工授精、代孕、人造子宮,冷凍卵子等,后者包括克隆、基因編輯、嵌合體等。“除了人造子宮之外,這些聽起來很科幻的技術99%都實現了。”
萬煥奎《代人懷孕的姑娘》的女主角愿意幫不孕不育的表姐懷孕,這件事成為新聞后,有人問她是不是和表姐夫有婚外情,也有一些闊太太找上門來,讓她也幫忙生一個。寶樹認為,這篇科幻小說涉及了包括倫理在內的多方面的代孕爭議。科幻作家陳楸帆2019年的作品《這一刻我們是快樂的》也涉及了生殖技術的幾種情況,包括代孕、男性懷孕、人造子宮、通過基因技術直接制造嬰兒等。寶樹指出,寫作代孕母親的若干作品有一個共同之處,即設想代孕的母親和嬰兒還是會產生某種親子的情感關系。《這一刻我們是快樂的》中就有這樣的母親自白:
“我還是會感覺到它的心跳,像是在和我的心跳對話。我還是會因為它無緣無故的高興、生氣或者哭泣,一想到有一個在你身體里的小生命正在觀察著你的一舉一動,喜怒哀樂,雖然不知道它能感受到多少,可是你能感受到它,并相信它也能感受到你。這種感覺太奇妙了,跟你肚子里的生命是否屬于你沒有一點關系。你和它已經被某種東西牢牢地綁在了一起。”

與基因編輯技術有關的科幻作品有王晉康的《豹》,其中,科學家把獵豹的基因編到兒子的體內,孩子成為百米跑健將,但身上同時殘留著豹子的獸性,使他容易憤怒和攻擊別人,因此釀成悲劇。
在顧適的《嵌合體》中,科學家的兒子患上罕見疾病,需要換腎,她決定在豬身上植入兒子部分的基因,培養出人的腎,但問題出現了——豬和人嵌合在一起,生長出來的生命既不是豬也不是人,它長著人一樣的眼睛和大腦,擁有人的情感,甚至對科學家“母親”產生了依戀。與這部小說主題相類似的還有李安的電影《雙子殺手》,影片展現了威爾·史密斯與用他的基因克隆出的孩子之間的羈絆和情感。

寶樹認為,生育過程本來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如今借助高科技變成“制造”過程,制造一個孩子的時間、地點、數量都可以選擇,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是不是自然的就好,違背自然就一定不好呢?他表示,實際上現在的人類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都是不自然的,親子關系也是可以被創造出來的。人們不僅可以創造親子關系,還可以制造和傳統親子關系完全不同的關系,形成仿親子關系、類親子關系、半親子關系等。
當人與AI成為親子
在肖建亨的科幻小說《沙洛姆教授的失誤》(1980)中,沙洛姆教授發明了一種善于照顧孩子的機器人。沙洛姆教授就讓它照顧一個父母疏于照料的人類小孩,但孩子內心仍然愛他的親生父母,教授于是感嘆:人的情感并不能用理性來衡量,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并不可能用機器取代。這是肖建亨在那個時代的結論。王晉康的小說《生存實驗》則揭示了人與機器人母親之間的愛。孩子知道母親是機器人之后生出反叛和排斥,機器人母親容忍了一切,直到母親要被銷毀,孩子才突然意識到了對母親的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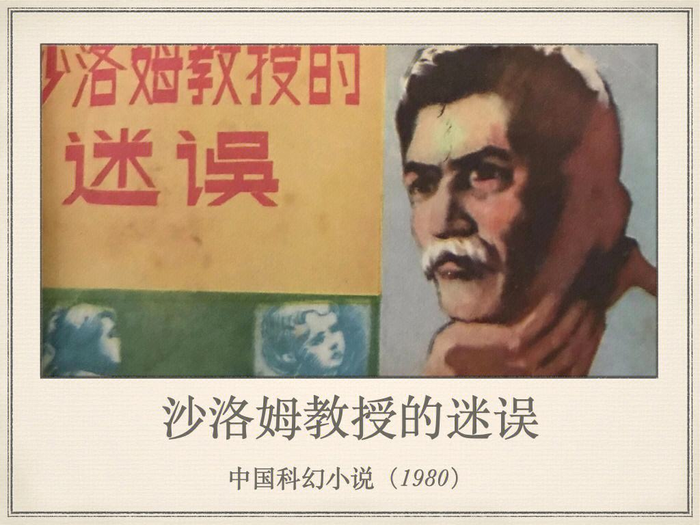
寶樹認為,在科幻作品中,親子關系中的他者“不僅是生物學上的兒女,在未來,一些賽博格、數字生命、AI等也可能會和我們形成親子關系”,它們是更加陌生、更加奇特的他者。“這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我們既不能像一些浪漫小說一樣,一廂情愿地決定它們也有人性;也不能像另外一些作品一樣,認定它們一定要消滅我們。未來可能是其中一種,也可能兩個情況都不是。”
代際沖突
在科幻世界中,親代會用什么高科技的方式來養育子代呢?他們之間是否也會產生代際沖突?
寶樹看到,在劉慈欣的小說《人生》中,遺傳技術發明之后,一位母親把自己的記憶和人生體驗傳遞給胎兒,想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但孩子認為母親在這個世界上遭遇到了很多挫折和痛苦,并對此產生恐懼,不想再度經歷這些,已經覺醒的孩子于是選擇在母親的肚子里用臍帶自殺了。《黑鏡·大天使》中的母親用芯片監控女兒,每時每刻了解女兒的位置和感受,芯片還能控制女兒的視野,會自動屏蔽眼前的不雅動作或血腥暴力場景。
這些科幻作品促使寶樹思考親子之愛的本質,“不管是使用現實的還是虛構的技術,父母的目標是希望子女成為獨立的、有自己生活的個體,”如果控制孩子的科技手段和這一目標相互矛盾,最后一定會面臨失敗。
他在活動上說,“毋庸諱言,我們愛自己的子女,當然因為他們有我們身上的一面,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他們是不同的個體,因此親子之愛在自我和他者之間。”科幻作家修新羽《陌生的女孩》反思的也正是這個問題。在小說里,每個人只能把自己的克隆體放在自己的子宮里,男性生出男性,女性生出女性,每個人只能生出自己,故事的男主角和女主角是一對戀人,他們不想生出自己,而想生出一個融合他們基因、兼有彼此特征的一個“陌生的女孩”,卻無法做到。寶樹認為,這篇小說就表明人的愛指向了一個和自己不同的他者。
死亡與永生
每個人都要通過死亡和親人分離,但寶樹看到,科幻小說里的數字人格、仿生機器人與意識上傳等技術,正在嘗試使人復生。“現實中就有一些人把過世親人在網絡上各種發言收集起來,喂給一個程序,讓程序模仿說話,形成數字人格,只不過因為素材非常少,目前還非常粗糙。”
寶樹稱,科幻小說作家設想了多種方式,幫助人們克服和親人分離的痛苦,意識上傳、仿生機器人等做法就是形成某種“紀念品”,如果“紀念品”有自己的人格就成為了“替代品”,可它們也可能成為“吞噬未來的過去”,“某種意義上似乎能感覺到背叛了真正屬于你的親人”。
長壽技術也將改變和動搖親子關系。如果親代可以活幾百年,也許就不會把更多資源投資在子女身上,而會更多地投資于自身,“雖然聽起來有點兒悲哀,但這也是必然的趨勢。”寶樹說,“隨著現代人壽命的延長和各種長壽技術的發展,會有不少問題出現。比如人到了五六十歲看上去和三十歲差不多,還要和比自己小二十歲的人一起生活和工作,這些都是非常獨特的挑戰和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