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期主持人 | 尹清露
“好多年來,人們把讀書的目的設置為一份惹人艷羨的白領工作,可是,焦慮、抑郁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生活的終極目標難道不是開心嗎?”
這段話來自豆瓣小組“輕體力活探索聯盟”,小組創建于2022年11月,短短幾個月已經擁有兩萬多名成員,年輕網友們在組里求師問道,希望降薪辭職去做不費腦子的體力工作,其中不乏一線大廠員工。此外,更多人選擇在主業之余探索一份副業,既給生活找一個喘息的空間,也多一個賺錢的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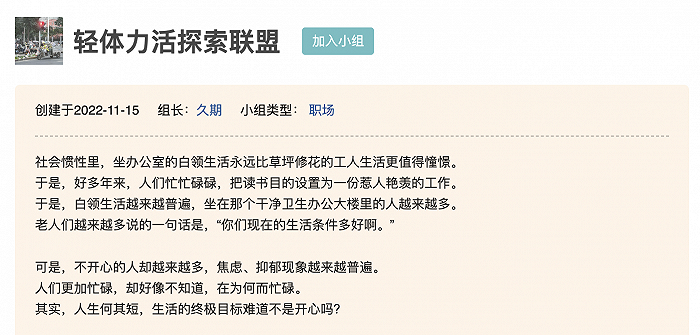
想做體力活的理由很多:為了擺脫長時間思考以及神經緊繃的折磨,試圖在體力勞動中找尋類似冥想的“心流感”和“內心的平靜”,這也是為什么收納整理師是組內呼聲最高的職業之一,近藤麻理惠就在《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中提到過:“不用特意游玩山水,在家動手整理就能體驗到瀑布修行的快樂。”也有備受艷羨的口腔科醫學生看不到就業前景,索性放棄職業規劃去做保潔員,表示自己“真的喜歡理東西,也不怕臟”,這些例子似乎說明,我們對理想工作的標準正在發生松動和改變。
實際上,大多數人期待中的體力活是不太累又要有足夠尊重的體面工作,比如寵物理發師和瑜伽老師,分揀快遞或者保安這種工作則要“離得遠遠的”。也有不少人給體力活戴上天真的濾鏡——有人愛吃某品牌的零食,就想去那個公司打工,結果被提醒那可能是“一家壓榨人的企業”;有人辭職去連鎖咖啡店工作,以為可以逃離辦公室的繁瑣工作,卻要受制于機械勞累的操作流程和超高的客流量。這一方面折射出我們不了解體力勞動的現實——它大概率又苦又累,沒有田園牧歌風情,且同樣會在工業體制下被異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腦力打工人與體力勞動者的疏遠和陌生,他們往往疲于謀生,并沒有太多選擇。
體力勞動真的可以放松身心嗎?

葉青:前段時間農村田園生活視頻特別流行,視頻中呈現出的多是輕松從容、遠離喧囂的生活方式,許多在一線城市從事繁忙工作的年輕人會在這類視頻中尋找慰藉,不少人在評論區表達了向往。我可以理解為什么大家愛看這種視頻,但其中多少有一些對農活的美化和幻想。看似獨立完成且信手拈來的農活其實通常是團隊合作的成果,有過種地經驗的人想必都知道,這是一項難度不小的勞動,對體力也有一定要求,在烈日下辛苦勞作半天后是絕不可能像視頻中那樣妝容完整還大氣不喘的。
我小時候也對農活很感興趣,覺得長輩們在農田里一邊插秧一邊聊天有趣極了,看上去似乎也沒什么難度,鬧著要一起“玩兒”,但下田后才知道這完全不是什么我想象中的趣事。田里滿是淤泥,插秧過程中泥水濺得渾身都是,并且全程都得彎著腰,這可不是什么舒服的姿勢,不一會兒就腰酸得不行。實在佩服長輩們還能一邊勞作一邊閑聊,我累得只想趕緊找借口放棄。
林子人:真正的農村生活當然不同于視頻中的田園牧歌幻想,這是李子柒在收獲了全球粉絲的同時,也招致不少人反感的重要原因。前兩日讀《克拉克森的農場》,看一個當紅汽車節目主持人、專欄作家,一個五谷不分四體不勤的暴躁老頭如何突發奇想去當農場主,樂得不行。我印象很深的一個細節是克拉克森提醒讀者注意木工不是那么好做的——我們以為電鋸很拉風帥氣上手又很簡單,其實完全不是這樣:
“鋸子啟動之后你會發現,操縱電鋸和你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你會感到超級恐怖,因為你清楚地知道,它隨時都可能脫離你的雙手,反過來鋸掉你的腦袋。于是你小心翼翼地拿著它走向你準備開刀的那棵樹,下一秒你卻掉進了獾的洞穴。因為地上長滿蕁麻,你根本看不清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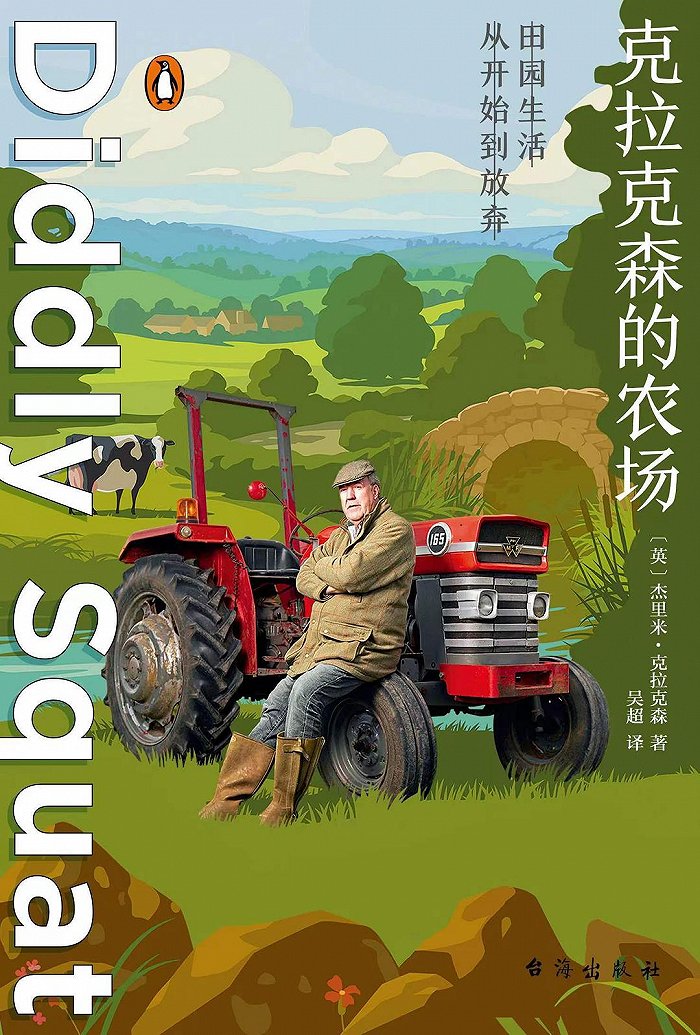
[英]杰里米·克拉克森 著 吳超 譯
臺海出版社 2023-2-21
據說講述他農場生活的紀錄片非常受歡迎。我想這是因為它找到了一個很微妙地滿足觀眾心理的敘事角度:它向你展示一個此前毫無務農經驗的都市人(恰如很多正在觀看這部紀錄片的觀眾一樣),在面對真正的農村生活時會出多少令人忍俊不禁的洋相,同時又告訴你,雖然做農活很累很操心,但它切切實實在“創造”一些東西(食物),確實能讓你獲得一種簡單的快樂。
潘文捷:看音樂會如果遇到全體起立,大家會覺得音樂家好成功。但是你知道嗎?演奏家演奏結束,大家站起來鼓掌,倒不全是因為演出太棒了,也可能是因為坐太久了,想要活動活動。這件事是《久坐危機:如何讓你更愿意動起來》的作者彼得·沃克談到的。在整天坐在辦公桌前的工作和快遞員工作之間,沃克自己選擇了后者。他每天騎車在倫敦派送文件,每天要騎行八九十千米,隨后他發現自己的身體出現了很大的變化,騎車速度變快了,耐力增強了,腿部還有了肌肉,還不知不覺中擺脫了身體虛弱的舊形象,給了他一種自己可以做到任何事的快樂感。

如今,日常活動的減少是在城市中全面發生的。我們身處于一個久坐不動的世界,這種生活方式對我們的健康帶來了可怕的威脅。越來越多人對“輕體力活”的向往,當然是對現今工作環境的有力質問。可其中也不乏一些天真的幻覺成分,比如說,我也曾經想過一些體力活兒會不會比坐著的工作好一些,比如說送餐送快遞,想必可以緩解久坐不動導致的問題。后來發現真是想多了——北京的快節奏送貨甚至不會允許你騎自行車,大家都是騎著電動車飛馳,速度變得更重要,倒計時給人壓力驟增,為了趕時間,逆行、撞車等問題屢見不鮮。
董子琪:昨天一下子與三位師傅同時打交道,一位是幫忙抬家具的,一位是負責裝柜子的,還有一位是專門來丟舊家具垃圾的。有一個時間點三位師傅齊聚,他們彼此毫不相干,誰也不認識誰,各忙各的,但卻有一些有意思的交互,丟家具的師傅看見裝家具的師傅在找地方攤平木板,問要不要幫忙抬起來,于是他倆合作把餐桌和沙發都挪開,還互相問候對方老家哪里,大家都很樂呵。雖然不構成競爭關系,能看出來還是略微有點差別——裝柜子需要技術,收入也高一些,師傅性格更沉穩;丟家具的師傅似乎更為開朗,頭發已經白了,活也最辛苦瑣碎,搬死沉的家具上樓下樓這件事需要一點野蠻的肌肉與精神。聽見樓道口低悶的吭吭聲就知道了,他所做的是讓這些舊東西消失,回到空無一物的狀態,可是空無一物竟然是要這么拼命才能實現的。看到了這些,就不太相信體力勞動放松身心,甚至是相反的,體力勞動是為了人們放松身心地享受但最好無聲無息像從來沒存在過似的。
尹清露:體力活無法放松身心甚至相反,這讓我想起“輕體力”豆瓣小組里有人說,只要有搬東西的機會都會很開心,因為可以當做健身鍛煉,但如果單純是為了生計而勞動呢?我高中暑假做過大賣場的冷飲售貨員,要推著貨物在電梯間奔波,全天站立外加大喊“歡迎試喝”,于是發明出不太累發聲技巧,“歡迎”二字語調向下,“試喝”二字語調向上,聽上去果然很像餐廳服務員慣用的語氣——那是當然,因為這樣就是最省勁兒的方法。

既想看見勞動成果,也要得到優質回報
董子琪: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曾經說,很多白領大概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不是重要的以及成果是什么樣的,而人們的天性就是想要影響世界、看到結果。親力親為的體力活,比如種地,就是一個能看見結果的誠實勞動,它可能會幫白領洗刷掉一種假裝在做事的愧疚感,減輕心理的負擔?
先不說體力活有多么復雜細致,從《勞動者的星辰》里我們能看到,那些普通的活計,比如漏粉條、種植棉花,都需要長久的經驗,那些構成經驗的名詞好像都能成為一門語言。真實地從白領工作切換到體力工作,一個人所感受到的心理落差想必也很大——你是否能真的放棄對于窮達貧富的考量呢?陶淵明“聊為隴畝民”并不是真的變成了農民,真的變成農民也沒必要以陶淵明的視角來寫詩了。

范雨素 郭福來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 2022-8
徐魯青:我很認同“看見結果”對人心的安慰,如果把和身體行為緊密連接的工作看作體力活,那織毛衣是體力活,做木工是體力活,再往前推一點,其實做雕塑、畫油畫都可以算體力活。但在很多人眼里,它們和送外賣、流水線拼裝這些工作又是不一樣的。細想起來,這是不是創造的可見性的區別?做飯賺外快的女孩喜歡的是和顧客創造的一段段直接關系,大廠下班搞縫紉的年輕人看到的是自己做的成衣,他們在大廠感受不到每天加班創造出的結果——機器太大了,我怎么知道我做的那一部分真的有任何意義?
能放松的體力活往往是流水線的反面,人不隱蔽在機構之內,不作為流程圖的一部分,個人直面物件,個人直面個人。格雷伯便認為自由不是無所事事,而是對一件事情感到有掌控能力,我們在工作里得到的快感不是投入精力少而獲取多,更多來自于發現自己有改變什么的能力。體力活的這些特點都挺明顯的。
不過也有一些時候,放松是因為投入的精神價值少,同時成效立見。我洗過一些盤子也送過一些外賣,最大的解壓之處在于沒什么意義寄托,比起辦公室工作更能感到是實打實的交換,我的行為就是交換籌碼的全部,不帶任何精神附加值,不會為做不好一件事懷疑自我價值。很多人提到的體力活“不用想太多”,估計就是這個層面。
林子人:辭職去做體力活倒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我多年前出于好玩的心態去上過一節木工課,大概花了一天時間做了一只木盤。當時木藝工坊剛剛在杭州興起,工坊提供很多零基礎木工課程,頗受年輕白領歡迎。2016年我寫過一篇特寫報道《發現杭州“創藝青年”:做一番有趣的事業并以此為生》,其中就采訪了這家木藝工坊的聯合創始人。他原本是一個建筑設計師,木藝是他工作之余的自娛自樂,但因為感到工作壓力太大、缺乏成就感,他就干脆辭職創業了。他教對木藝感興趣的人如何做木工,有一位學員甚至也因此走上了木藝的道路,開創了淘寶上聲名鵲起的家居品牌。

在那篇報道里我采訪了幾個類似的脫離“正統”白領職業發展路徑,去做和“手藝”相關的事的人。現在回頭再看,感到那些采訪對象可能和現在豆瓣小組里探索“輕體力活”的年輕人在心態上有些區別。但不變的是,給人帶來體面感或趣味的體力活,不僅是那些對體力要求不那么大的“輕體力活”,更重要的是它們是能夠在現行經濟制度中得到優質回報的勞動。
在ChatGPT橫空出世、人工智能威脅白領工作的可能性陡然提升的當下,辦公室工作和體力活之間的階級界限正在模糊——畢竟兩者都有被機器取代的風險——但也有研究發現,那些和“對人的服務”相關的工作是最難被機器取代的,比如小學老師、老年人的照護人員等。但我們會發現,在現行經濟制度中,這些人群的報酬和他們的工作重要性是不成比例的。我們對體力勞動的偏見甚至污名化,可能正是因為如此。
日本學者廣井良典在《后資本主義時代》中提出過一個我印象深刻的觀點。他認為,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已經進入了勞動力過剩(慢性失業)、資源不足的困境,為此我們應該改變“生產率”的定義,從勞動生產率(用更少的人生產更多的產品)轉向環境效率,即積極地使用人力勞動,減少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及環境負荷。廣井良典指出,生產率的概念發生如上轉變后,我們就會發現,原本被認為“生產率低下”的、對人服務的領域,變成了生產率最高的領域。結構性的社會變化將表現為,“人們關心的焦點將逐漸轉向服務和人與人的關系(或‘關懷’),以人為核心的勞動密集型領域必將走上經濟的中心舞臺。”如果那樣的未來真的成為現實,我們對做體力活殘余的顧慮與偏見,應該也會消失殆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