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兩會鄰近,一系列代表提案正在社交網絡掀起關注和討論。昨天登上新浪微博熱搜的是全國政協委員熊水龍的一項擬提案,他建議適時調整“雙休日”,試點開展周休日實行“隔周三休”的制度,即首周休息一天,次周休息三天。“這樣做既保障了公共休假制度的剛性約束,又提供了全年多個分布均衡的‘三天小長假’,還能助力分散休假、緩解旅游高峰壓力。”
就在幾天之前,關于“四天工作制”的討論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2022年,英國61家企業和約2900名工人參與了一項歷時半年的實驗,在保留原有工資的前提下減少工時,每周工作四天,休息三天。實驗結束后,其中56家公司(占92%)選擇不恢復五天工作制,繼續試行四天制,18家公司決定永久改為四天工作制。《工人日報》2月24日發表了評論文章《少上一天班,究竟“香不香”?》,稱盡管近年來全世界四天工作制試驗的節奏明顯加快,但現在要下定論或許還為時尚早。“盡管在多國試驗中收獲了一片叫好聲,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肯定地說,四天工作制一定‘沒問題’。”
借著當前對于休假制度的討論熱潮,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特此重刊2019年勞動節的一篇舊文《加班、失業與打零工:互聯網如何改變了我們的勞動?》。我們默認和習慣的“雙休日制度”似乎出現了動搖的可能,每一次關于勞動、加班和休假制度的討論都熱鬧非凡,其根源正是勞動者對于自身權利的珍視和捍衛。事實上,無論是雙休日制度還是8小時工作制,都是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全球勞工抗爭取得的成果。
《加班、失業與打零工:互聯網如何改變了我們的勞動?》
撰文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長久以來,不合理的加班一直是勞動者抵制的對象。五一勞動節的設立初衷,實際上就是為了紀念這一反抗。1866年9月,“國際工人聯合會”在日內瓦召開會議時首次宣布將8小時工作定為全球勞工運動的共同目標;1886年5月1日,美國工人舉行芝加哥大罷工,要求實行8小時工作制,為了紀念這一事件,5月1日被確立為勞動節;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8小時工作制首次在國家層面立法頒布;1919年,剛剛成立不久的國際勞工組織(ILO)通過的第一號公約即規定了工作時間每天不得超過8小時,每周不得超過48小時。

1995年5月1日起,中國開始執行雙休日制度。2018年修訂版《勞動法》規定“每日8小時、平均每周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與上述國際公約保持基本一致。當下中國勞動法中規定的8小時工作制,是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全球勞工抗爭取得的成果。
需要注意的是,長時間加班在中國職場——特別是傳統制造業——實際上是一個長期且廣泛存在的現象。超額工作撐起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令中國人引以為豪的“中國速度”,但承受加班之痛的工人通常很難在主流輿論場中發出聲音。在長期加班對個體精神和肉體雙重折磨的問題上,無論收入高低,各個勞動群體實際上殊途同歸,這一點不能被任何冠冕堂皇的加班理由抹殺。某種程度上來說,加班合理化更是個社會分配不均的隱喻,一個互聯網時代勞資關系日益失衡的標志——隨著科技發展,即使是自詡中產的專業技術人員也將發現,自己在勞資關系中討價還價的能力越來越少。
加班合理化:過勞時代中被裹挾的無力個體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雖然物質享受日益豐盛,但工作壓力也日益沉重的“過勞時代”——這是關西大學經濟學家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一書中呈現的觀點。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全球化發展、信息通信革命、消費社會的成熟、雇傭與勞動限制的放寬、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席卷世界等資本主義的跨時代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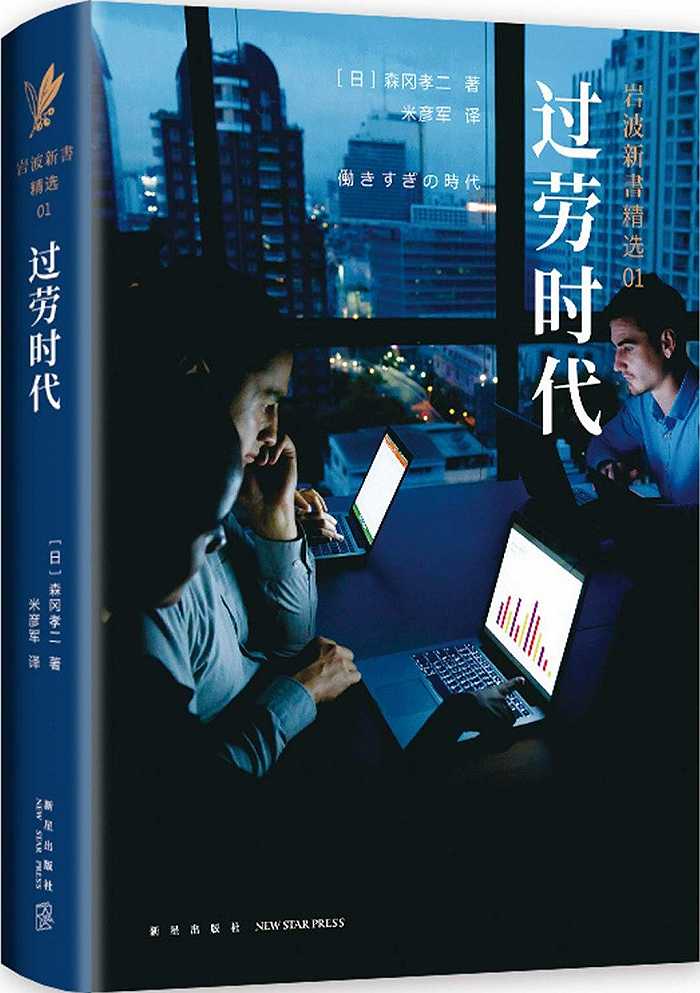
[日] 森岡孝二 著 米彥軍 譯
新星出版社 2019年
在“過勞時代”的時間軸上,1980年代占據重要位置,因為自那時起,發達國家縮短工時的趨勢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工作時間開始變長。這與發生于同一時期的全球新自由主義轉向有著密切關系:1980年代初,撒切爾和里根分別在英國和美國執政,國家福利政策緊縮,讓位于市場導向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開始伴隨著全球化進程席卷全球,并在1989年冷戰結束時成為了資本主義陣營勝利的最佳注腳。
新自由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社會組織和人類生存價值的認知——競爭是人類活動唯一合理的組織原則。而為了提高企業競爭力,企業開始擯棄關系穩定的雇傭關系、較多的閑暇時間和優厚的員工福利,采取較為嚴酷的經營方式。
進入1990年代,一個對當下職場影響同等重要的趨勢發生了——電腦、手機、電子郵件等通信工具的不斷普及讓員工工作與生活的界線日益模糊,而信息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工作速率的不斷提高亦讓基本單位時間內的競爭變得愈發激烈。
與此同時,包括中國、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融入市場經濟,成為跨國公司降低人力成本的出口,全球化格局被深刻改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開始在工資和工作時間上同臺競爭。為了增強生產率、提高競爭力,延長工作時間的做法越來越普遍。
“新型信息通信技術是減輕、省去工作量的強有力的工具,然而它同時也加速了業務運轉、加劇了時間競爭,商品和服務種類多樣化,經濟活動出現了無國界和24小時化的趨勢。”森岡孝二同時指出,即時通訊手段的推陳出新也為“員工全天候在線待命”式的工作方式鋪平了道路,即使雇主不強制要求員工加班,也能通過電話、電子郵件和即時傳訊把員工拉回到工作狀態。“24/7”(一天24小時,一周7天)開始成為一個職場熱詞,用來描述這種超高強度的工作模式。

“24/7”的超強工作模式實際上是永不休眠的全球化市場要求。森岡孝二援引前美國勞動部長羅伯特·B·賴克的觀點指出,技術革命的飛速發展讓競爭日趨激烈,速度成了抓住消費者的關鍵。消費者在互聯網時代被培育出來的對更快、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務永不饜足的需求,實質上變相催生了勞動時間的延長和就業的不穩定。
24小時便利店、網購和快遞——如今的都市人不僅已經完全習慣甚至已經無法離開這些異常便利的服務,然而一個容易忽略的事實是,撐起城市便利生活的群體正在默默忍受越來越長的工時。以便利店為例,森岡孝二發現,日本便利店從業者中約八成為小時工和兼職員工,他們在不同時段倒班工作,保障了24小時的營業模式。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超市、百貨店、快餐店、參觀及其他零售業、飲食業和服務業也在越來越“便利店化”,支撐這些行業的從業者也因此承受著超負荷工作。
即使是在職業聲望階梯上占據更高位置的白領工作者,也無法避免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被迫貢獻出更多的工作時間,很多時候這甚至無需雇主強迫,而是在一種強有力的企業文化中潛移默化地得到了規訓。在這一方面,硅谷科技公司對全天候工作(all-hours work)的狂熱可謂是樹立了一個典范。
美國學者尼基爾·薩瓦爾(Nikil Saval)在《隔間:辦公室進化史》一書中指出,從1980年代起,硅谷的辦公室氛圍被不斷神話并被全美(乃至全球)視作榜樣。在科技創業者們的刻意引導下,這種辦公室氛圍有意地挪用了斯坦福等大學的校園生活方式,“對自發性的強調,對娛樂性的壓倒性關注,兄弟會般的氛圍,這一切都在消解著舊有的——或者用硅谷人的話說,過時的——對工作和閑暇的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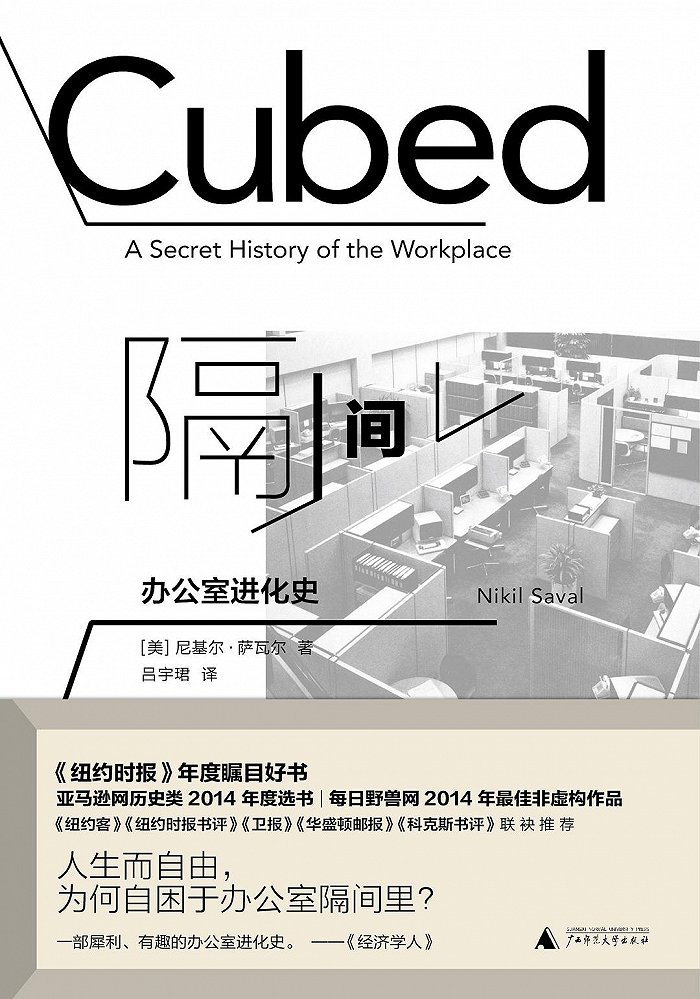
[美] 尼基爾?薩瓦爾 著 呂宇珺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年
這一切被包裝為企業文化販賣給員工,讓員工相信自己是在從事一項自由、自主又有創造性的工作,長久地工作不是為了他人,而是為了自己。與此同時,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在硅谷興建包羅萬象的園區,如校園般為員工提供包括免費食物、日托、醫療、健身在內的一切服務和生活便利,我們當然可以認為這是大公司為員工提供的慷慨福利,但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也是變相“慫恿”員工花更多時間在辦公室里工作,甚至將全部的個人生活都托付給公司。
如今我們看到,這種企業文化也已蔓延至中國互聯網企業,這也是為什么某位企業家能夠侃侃而談“福報論”。員工擠出個人時間投入到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實際上大部分由企業收入囊中,員工本人看似得到了高薪回報,卻在精神和肉體兩個層面都遭受了壓抑和損耗。在年齡漸長體能跟不上快工作節奏,或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這些員工通常會迅速淪為棄子。另外,個人在企業中充其量發揮的是一枚螺絲釘的作用,縱然有自愿加班的拼搏精神,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發揮自主學習和思考能力,獲得實質上的個人提升呢?
一個更有可能的場景是,員工在令人窒息的加班環境里筋疲力盡,喪失了探索未知領域的激情,甚至無力掙脫令人不滿的現狀,從而墮入某種職業生涯的惡性循環之中無法脫身。
外包、零工經濟與結構性失業:互聯網加劇社會分配不均
在互聯網剛剛開啟狂飆突進發展模式的1990年代初,紐約大學教授、媒介理論家、批評家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在《技術壟斷》一書中警告人們不要迷信技術進步一定能夠解決一切難題、給人類帶來更多自由。他認為,歷史證明了每一次重大的技術革新,實際上就是在摧毀傳統知識壟斷的同時,塑造一種由另一群人把持的新的知識壟斷。也就是說,在技術進步的過程中,既有贏家,也有輸家。因此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誰會是贏家,誰會是輸家?是贏家多還是輸家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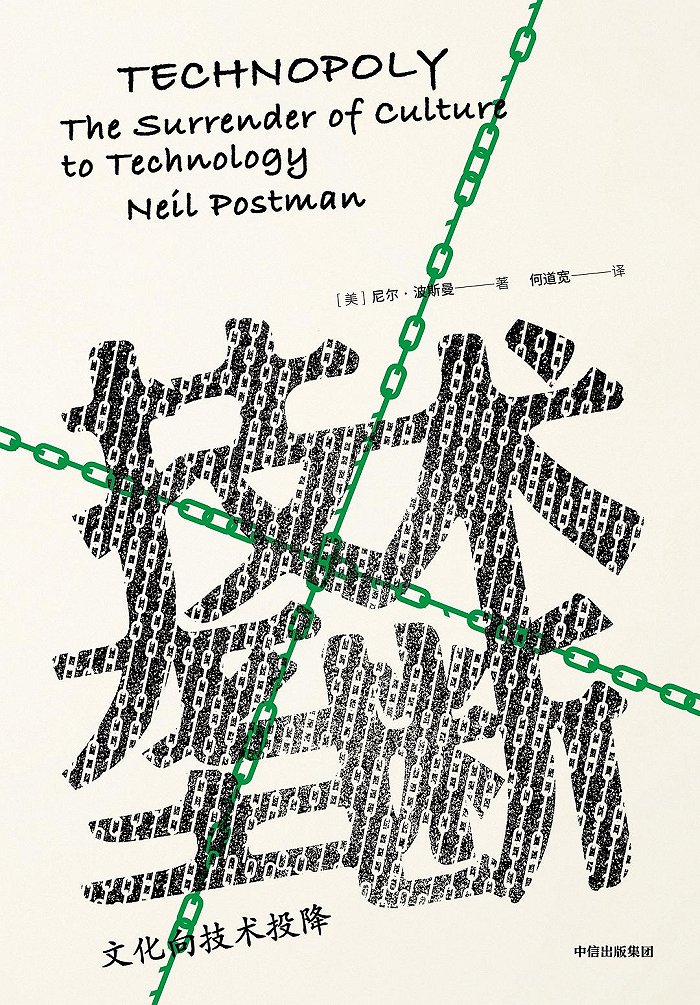
[美]尼爾·波斯曼 著 何道寬 譯
中信出版社 2019年
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互聯網時代的輸家就是那些IT技能不足的人,且這一群體正在不斷擴大。《大分流:美國不斷擴大的不平等危機與我們的策略》(The Great Divergence: America’s Growing Inequality Crisi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作者Timothy Noah認為,數字革命將個人的就業競爭力與高級IT技能深刻綁定,對就業產生了破壞性影響。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Bradford Delong也提到,縱觀人類歷史,任何一種解放人力的機器都促使人們轉向那些對智力和技術要求更高的工種,但隨著IT技術慢慢地入侵智能要求較高的領域,人類擅長且不易被取代的好工作就會越來越少。
當下我們已經隱隱可以看到這一趨勢。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經濟學家Loukas Karabarbounis和Brent Neiman發現,1970年代中葉以來,全球工人的收入配額都在減少。經合組織(OECD)于2019年發布的報告則顯示,在全球最大的一些經濟體中,中產階級正在萎縮。平均而言,中產階級人群比例從上世紀80年代的64%跌到了61%左右,且呈現一個逐年平穩下降的趨勢。與此同時,中產階級的經濟影響力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大幅下降。千禧一代躋身中產階級的難度越來越大,門檻也越來越高。這不僅是因為生活成本的增加,也是因為收入增長的緩慢甚至停滯——報告指出,1/6的中產崗位因自動化而面臨被淘汰的威脅。
“人們越頻繁地使用當今的數字網絡,從中獲得的經濟利益越少。網絡無法促進經濟平等,反而是貧富差距拉大、中產階級被蛀空的罪魁禍首。”CNN專欄作家安德魯·基恩(Andrew Keen)在《科技的狂歡》序言中做出此番論斷。互聯網時代不斷擴大的不平等與不公正不僅是技術進步造成的技能和經濟區隔的結果,也是科技公司充分貫徹自由主義市場邏輯,破壞顛覆傳統行業的變現。

Barry Gordon 著 趙旭 譯
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基恩首先指出,谷歌、亞馬遜等科技巨頭形成了贏者通吃的規模經濟,造成了結構性的失業危機。以亞馬遜為例:規模效應對線上經濟變得前所未有重要,亞馬遜的成功取決于一個事實,它的規模越大,產品價格越豐富,服務越可靠,就越有可能擊敗競爭對手。數據顯示,1990年代中期,美國有大約4000家書店,到2015年這一數字已經下降了一半,也就是說幾千個零售崗位消失了;2014年英國書店數量已經不到1000家,比2005年減少了1/3;小出版商在亞馬遜強勢的定價策略面前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
與此同時,科技巨頭在掌握越來越大的資源和財富。互聯網提供的免費工具——比如谷歌、Facebook、微信、微博——一方面方便了互聯網用戶,另一方面實際上也是在通過用戶創造的數據來為自身創造價值,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是這些網絡公司的免費勞動力,我們使用得越多,搜索引擎的服務就越精準,社交網絡的價值就越大。當傳統行業被打擊,少數科技公司掌握大量資源和財富時會發生什么?按照紅杉資本董事長邁克爾·莫里茨(Michael Moritz)的說法,“如果你是窮人,生活會極其艱難。你是中產階級,生活還是極其艱難。那意味著你必須接受對的教育,最終到蘋果、谷歌工作才行。”也正因此,在科技行業與其他行業相比薪資差距明顯的大背景下,即使對工作環境不滿,員工也是很難輕言退出的。
另外,由互聯網創新者們一手打造出來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雖然賦予了勞動者更多的自由,但也加劇了勞動者的職業不穩定性。為了降低人力成本,企業完全可以減少全職工作,用短時工取而代之,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可以轉嫁正常全職員工所需的保險、福利等人力成本了。基恩在書中援引《紐約時報》一篇報道的觀點:“這種高度不穩定的勞動力模式、自給自足的資本主義模式正在成為新型網絡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長此以往,工作將日益碎片化,勞動者將日益原子化,薪資水平的發展也不容樂觀。
自由職業者在歐美國家勞動力中的比例躥升,引起了部分學者對“辦公室無產階級”或“朝不保夕階級”的討論。薩瓦爾援引美國圣約瑟夫學院勞工史學和社會學教授理查德·格林沃爾德(Richard Greenwald)的觀點指出,這些“朝不保夕階級”的成員有些是自己主動離開全職崗位,但大部分是不得已為之。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沒有醫保,許多人總是“超級缺錢”,并且有些人有“一種錯覺,覺得他們中很少有人正在被剝削著”。
自由職業的問題在于,對于部分佼佼者來說,他們的確享有工作自主權和勞動定價權,并在出售勞動的過程中獲取滿足感,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孤身作戰的危機感始終懸在腦后,而脫離工作組織的一個后果是,事情出了任何差錯,都只能歸咎于自己——這可以說是新自由主義信仰的最極端內化。
零工經濟的另外一面就是,即使是有幸躋身科技行業的程序員也無法獨善其身。森岡孝二指出,IT技術不僅創造了新型的技術崗位,也造成了工作或業務的標準化和簡單化。這些崗位往往只需要可替代性強的非熟練工人,這使外包業務變得更容易,方便了由正式員工轉向非正式員工的操作。小時工、兼職員工、派遣制員工等非正式員工人數不斷增加,這一現象在高科技產業領域愈發常見。森岡孝二援引日本《勞動經濟白皮書》的數據指出,信息通信技術領域的派遣制員工人數是最多的,早在1998年,從事軟件開發、辦公機器操作、辦公自動化教育等工作的勞動者就占所有派遣勞動者的46%。

反思與反抗
當下,我們在很多時候將勞資關系斗爭史的歷史性成果視為理所當然。誠然,進入工業社會后,自古以來不斷增強的政治和經濟不平等趨勢出現了重大逆轉。在美國社會學家格爾哈特·倫斯基(Gerhard E. Lenski)看來,這一逆轉趨勢發生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現代工業社會專業化趨勢和對有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增強,導致精英階層不得不越來越倚賴專業人士的勞動,以犧牲權威的代價來增進效率和生產力;在另一方面,由于生產力迅速提高造就了物質豐裕、經濟富足的社會,精英階層傾向于對下層做出一些經濟上的讓步,以減少敵意和革命的危險,增大勞動報償。
因此,專業技術人員的不可替代性很大程度上是縮小社會不公的重要因素。“這些專業技術人員不可能被大規模地替代,這就給勞動力市場引入了一定的有利于勞動力出賣方的剛性,在對技術性能力的要求急劇增長的時期中更是如此。”
然而倫斯基同時指出,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幾乎總是會出現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趨勢:“在過去,由于交通和通信系統的不發達,加上合理化的經濟組織和行政機構的發展也有限,這一傾向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隨著當代社會中技術和社會組織的進步,這些限制在很快地消失。”也就是說,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邏輯的驅動下,資本方一直都有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不斷擴大資本積累的動力。在這之中,技術發展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變量,不少學者認為,如若我們放任技術自由發展,勞資關系的天平將再一次以一種幾乎不可逆的態勢倒向資方。

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就在《未來簡史》中預測了一個令人驚駭的前景:“隨著人工智能加速進化,未來99%的人類將變成無用之人。”他認為,未來的智人有可能分裂為兩個物種:一部分人可以通過尖端生物技術來改造自己或子女的胚胎、增強器官功能、減少免疫缺陷,從基因上成為更高級的智人物種;而難以負擔這種改造的則會降格為低級智人。“隨著AI、機器人逐步取代人類的職業,許多人都將會失去經濟價值。更可怕的是,一旦低級智人喪失了軍事和經濟價值,精英階層與政府可能會喪失投資教育、健康、福利的動力,最終導致他們被整個系統拋棄。這將是無以倫比的噩耗。”
在當下,赫拉利描述的未來還顯得相當遙遠,但在細微處,技術進步對勞動者的鉗制在不同職業、不同群體中皆可見端倪:一位某獨角獸公司基層員工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告訴記者,公司為了防止員工磨洋工,實行了一套稱為“資源利用率”的工作飽和評估機制,員工每天做了哪些事都要在系統中登記,一天12小時的工作時間,“飽和度”要在90%以上。據當地媒體報道,南京河西區的環衛工人配發了一款手表,除了定位功能之外,工人們只要在原地停留休息20分鐘以上就屬于違規停留,手表將發出“加油”的報警聲;南京雨花臺區則通過手機攝像頭對環衛工人進行實時監控。
勞資關系和階級沖突是個亙古已久的問題。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新自由主義允諾我們可以通過充分競爭和平等的機會獲得成功。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這一機制的無情一面也在顯現,在“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個人主義環境下,弱者的權益被冒犯,聲音被遮蔽,勞工問題被重新包裝為一個個人選擇問題。
是時候意識到個人努力的局限與邊界、反思當下經濟運行機制的弊端了。事實是,社會的結構性壓迫是無法通過市場調節的,必須由國家立法兜底提供安全保障網,確保個人不會因失敗而毀滅。正如《窮忙》作者戴維·希普勒(David K. Shipler)所說:“市場經濟的鐵律只會向更嚴格的政府監管和良心的尺度低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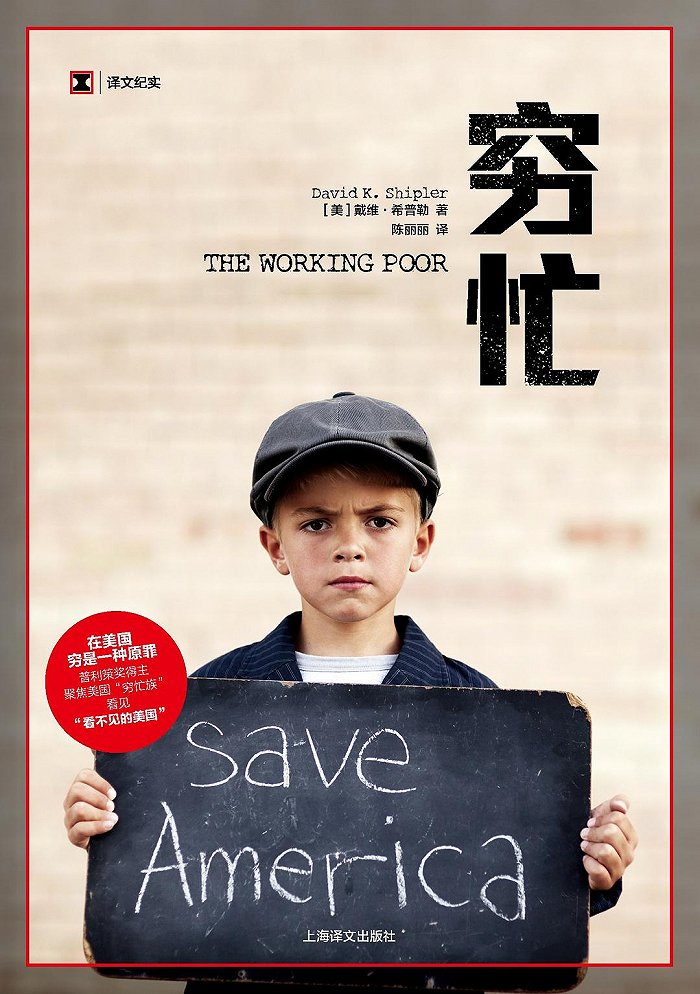
[美]希普勒 著 陳麗麗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5年
參考資料:
《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美]尼爾·波斯曼 著,何道寬 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4月
《過勞時代》[日]森岡孝二 著,米彥軍 譯,新星出版社,2019年1月
《科技的狂歡》[美]安德魯·基恩 著,趙旭 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6月
《隔間:辦公室進化史》[美]尼基爾·薩瓦爾 著,呂宇珺 譯,新民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
《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美]格爾哈特·倫斯基 著,關信平、陳宗顯、謝晉宇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月
《未來簡史》[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 著,林俊宏 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2月
《窮忙》[美]戴維·希普勒 著,陳麗麗 譯,譯文出版社,2015年1月
《新自由主義是如何節節頹敗,極右民粹主義又是如何步步蔓延的?》
http://www.cfztjj.com/article/2567847.html
《經合組織經濟不平等報告,收入停滯正將千禧一代擠出中產》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2924.html
《996背后,那些真實的人們和真實的工作》
http://www.cfztjj.com/article/304247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