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根據雙雪濤小說改編的同名劇集《平原上的摩西》目前正在熱映中。該劇導演是中國青年導演張大磊,他出生于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因而出人意料地將原著故事的發生地遼寧沈陽轉換為了內蒙古呼倫貝爾,為作品注入了更多內蒙的氣氛、美學和經驗。
2016年百花文藝出版的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是雙雪濤第一部中短篇小說集。書中同名中篇小說《平原上的摩西》是其創作早期最受關注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世紀之交的東北,革命與下崗、罪案與命運,種種因素交織出一幕幕隱痛,也奠定了雙雪濤作為小說家的顯著風格之一。除了此次迷霧劇場的劇集之外,這部小說此前還被改編為由劉昊然、周冬雨主演的電影。

雙雪濤日前出版了他的首部雜文集《白色綿羊里的黑色綿羊》,從實操角度分享了自己的寫作經驗:從小說的開頭、氛圍,到人物的塑造、意象與語言、結尾與修改……他的分享樸實而懇切,似乎不僅僅是在邀請讀者從作家的角度理解作品,更是在邀請我們以寫作的方式理解文學與生活。
在人物塑造這一節里,雙雪濤分享了《平原上的摩西》的創作過程。沈陽的一連串殺人搶劫答案最后如何發展成了這樣一個故事?在眾多人物的復雜線索和錯綜敘事里,雙雪濤先寫的是哪一個人物?怎么想象一個警察、一對父女?怎么寫出普通人心里藏著的那些不普通的東西?“人物的形象可能會在你的腦海里先出現,然后情節再展開,人物和情節是一個相互推動的關系。人物會發明情節,情節再建立人物。”雙雪濤說,“可能很多人以為要很了解一個人物才能動筆,其實在我的經驗里不是這樣,有時候你并不了解,但正因為你不了解,才令你興奮。”

《人物非人亦非物》(節選)
節選自《白色綿羊里的黑色綿羊》
撰文 | 雙雪濤
《平原上的摩西》是以人物為單元來展開的,通過它的創作過程也許可以試著給大家說說人物形象的建立。
我初中的時候,沈陽出現了一樁搶劫殺人的串案,在沈陽這是一樁很有名的案件,比我寫的東西還要更嚴重一百倍了。案件的過程是一些下崗工人和無業人員,組成了一個五人的團伙,他們前一天先預約一輛出租車,然后第二天在荒郊野外把出租車司機殺死,把尸體放在后備廂,駕駛著出租車去搶個體批發商或者儲蓄所,搶完之后,把出租車遺棄在郊外,分錢,分手。每次作案用時都很短,手法非常老到。
這個團伙中間還停下了幾年,不知道為什么有段時間沒干,應該是覺得風聲太緊,先躲躲,后來又重出江湖了。當時我在電視上看到他們幾個人被捕后還接受采訪了,每個人都有很長時間的專訪,死刑執行之前又有一個簡短的采訪。這件事對少年的我震撼還是蠻大的,因為它就在我們沈陽電視臺滾動播放,那幾個人的臉就在那里不停地閃爍。這個故事其實我也跟我的朋友講過,每次講的內容都不一樣,因為我總抑制不住自己去修改它。
寫《摩西》的時候,這個案子就在腦海里浮現了,但是并不是想正面寫這個案子,也并不是想用這個案子的全部來寫我的小說,前面也說了,現實材料只是個誘因,這個小說的出發點是想寫一個發生在我比較熟悉的故鄉,人物眾多、時間跨度比較大的故事。但具體怎么弄,其實沒有想好,就是想寫一個野心勃勃的、全景式的中篇。我決定案件在里邊穿插著寫,并且案件是我一開始準備寫的東西或者說是一個引起這個小說的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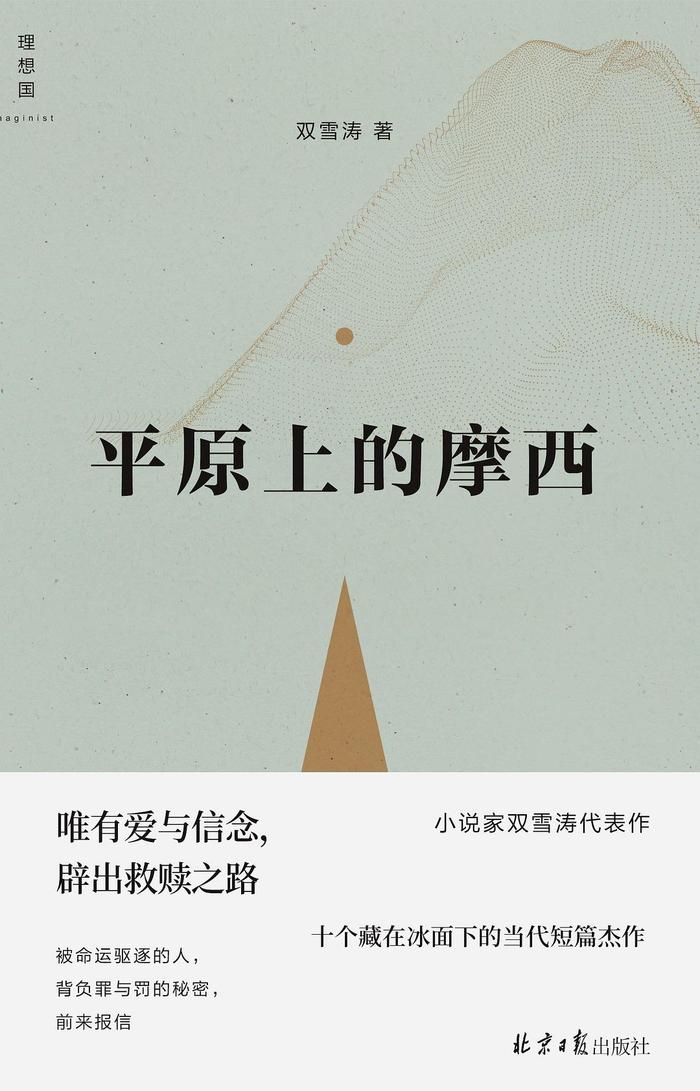
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1-04
我先寫的蔣不凡,小說里調查一樁劫殺案件里死掉的警察,好像還寫了一部出租車,后面放著尸體,在夜晚的馬路上飛馳。第二章寫的莊德增,一個跟案件不直接相關的人物,就繞圈寫,等我寫到莊德增,發現前面寫蔣不凡那部分是沒有意義的,蔣不凡只是其中一個人,最開始因為他跟那個案子關系很近,我才寫了他,就像你伸手拿起離你最近的那件外套披上,但寫著寫著覺得不太對,畢竟我不是一個偵探小說的作家,我追求的肯定不是案件這個事情,根據天氣,這個外套穿著不合適。
既然案子并不是這里最重要的事情,我就打算從離中心比較遠的地方開始,然后我就把前面的刪了,直接從莊德增那一章開始:1995年,我的關系正式從卷煙廠脫離,帶著一個會計和銷售員南下云南——也就是現在的《摩西》的開頭,我發現當這個莊德增作為一個普通人開始敘述的時候,這個小說就好像感覺舒服了,進入了一種合適的口氣。雖然當時什么情節都還沒想出來,但故事的氣氛和重量已經出現了。
那個案子依舊是一個轉折點,蔣不凡那個部分對于很多人的命運來說都是個轉折點。以前有個作家,我忘記是誰了,說了一句話,“小說像氣球,你要保證它的壓力,不能老用針去扎它”。大家都知道案子奪人眼球,但它并不是重點,這個案子的用法并不是要在這個小說里無時無刻地出現,它只是這個小說里眾多事件中的一個,小說里有些生活化的東西,有些日常的東西,案子可能比較強烈一些,但它也是其中的一環,它就像白色綿羊里的黑色綿羊,但是要一起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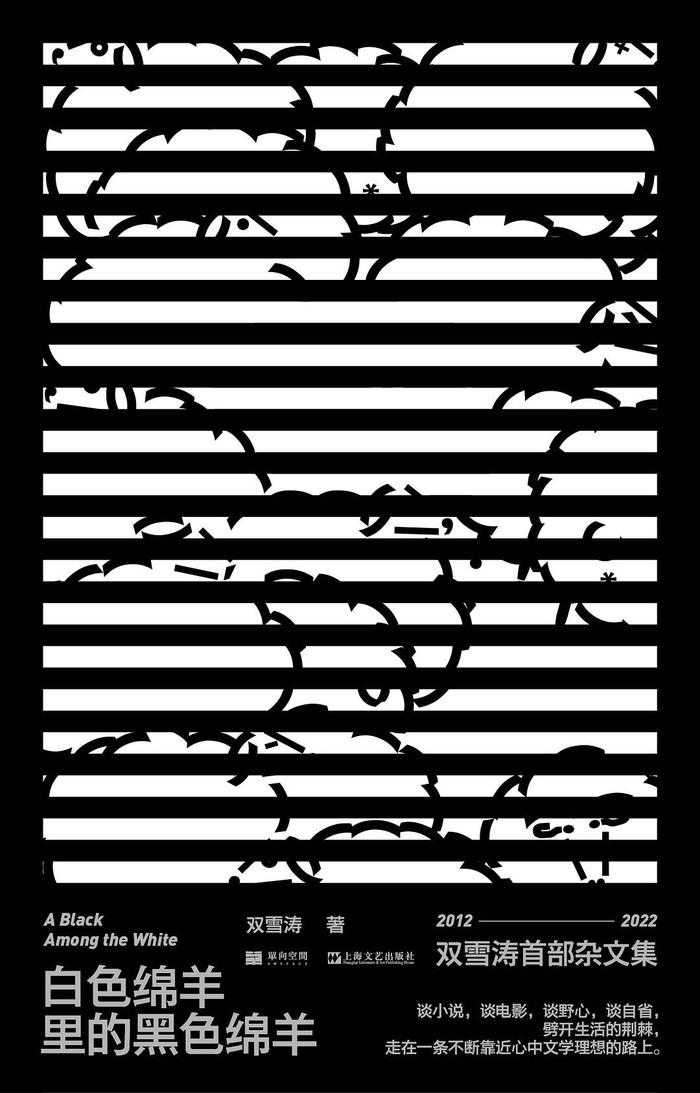
雙雪濤 著
單讀·鑄刻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3-01
那個布局就不是上來就把案子拿出來,還是一點點、一點點到達那個案子上,然后再引出更復雜的人與人關系的變化,才比較有意思。所以《摩西》現在看來那個案件也是蠻簡單的,沒有像它的原型那么復雜。但是人物之間的關系、人物之間的勾連變成了最主要的內容。
那我是怎么把每個人物逐步建立起來的?這其實并不是一個很復雜的創造過程,大概的人物并不難想,案子里的兇手、警察,警察的爸媽、同事等等,我寫著寫著每個人的性格就慢慢浮現了,我把他們當做我認識的人、身邊的人來寫。最重要的是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普通人,但是內心里又都有不普通的東西,然后讓他們彼此勾連起來,用網狀的情節支撐。我之前也說過,建立人物的過程不是生造一個人,而是適合這個小說的人物已經存在了,他只是被遮蔽了,你作為作者在你的小說世界里去發現他們,用一把小鏟子挖掘出來,從你的內心里托舉出來。
莊德增是第一個出現的人物,也許是因為他和世俗生活連接得比較緊密,所以他第一個跳了出來,引領故事。莊德增之后是傅東心,傅東心這個人物在我生活里極為少見,或者說基本沒有原型,主要是這個年齡段的女性我從小認識得就比較少,但是我能感覺到世界上也許有這么一種人,間接的,我在文學作品中也發現過這種人,我怎么能夠把她自然地鑲嵌到小說中呢?就是與莊德增組成家庭,這一組人物的反差營造出一出小小的戲劇,利用這個反差也打開了一道非常舒適的敘事的縫隙,很多東西可以應運而生。

李守廉是最早就想要寫的人物,類似于《水滸》中的一個人物,現代社會沒有梁山,沒有游民的棲身之地,最后怎么處置他我沒有完全想好,但是人物形象和走勢我心里大概是有數的。下面就是最重要的一組人物關系,李斐和莊樹的關系,李斐的形象也是一個文學性的形象,因為從她小時候開始寫,可以很好地消解掉一部分這個東西,可以說她和傅東心是一脈的人物,但是又截然不同,最大的特點是傅東心保守,李斐表面馴良,其實內心激進,這是我在考慮人物的時候比較明確的設計,新一代的人物要有不一樣的東西,表面看起來她和莊樹的感情是傅東心和李守廉的翻版或者是倒裝,但實則不是。
李斐和莊樹的關系要復雜得多,兩個人都對對方的生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莊樹沒有覺察,李斐是覺察到的,當莊樹覺察到,哦,這個人對我經常這么重要,我是因此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那時候已經是小說的末尾了。可以說,兩人之間的情感不能描述成任何一種具體的情感,他們兩個互為彼此的命運,互為對方命運的形象化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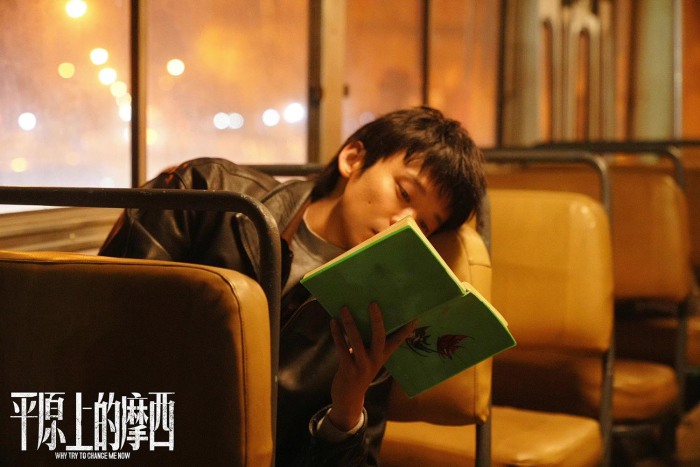
人物的形象可能會在你的腦海里先出現,然后情節再展開,人物和情節是一個相互推動的關系。人物會發明情節,情節再建立人物。比如說你可以先想到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這樣的人會做什么樣的事情,也可以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寫,那么適合這個事件的人物會在這件事中怎樣出現。如果事情沒想清楚,可以先去想想這個人是什么樣的性格,如果人沒想清楚就再想想事件,再去完善人物形象。當你想到這個人,他再往前走,才能產生一些事情,一些事情反過來可以幫助你理解這個人,寫小說就是你不斷在發現的過程,發現原來我這么了解這個人,這個人這么有意思,他竟然能干出這么一件事,或者有時候我只了解他一個層面,但是已經足夠了,足夠把他作為一個零件組裝在小說上了。
可能很多人以為要很了解一個人物才能動筆,其實在我的經驗里不是這樣,有時候你并不了解,但正因為你不了解,才令你興奮。有時候你以為你寫這個人,你就了解他了,其實你并不了解,你在寫的過程中會深化你對這個人的了解,他會自己產生一些敘述的前進,前進過程中你就發現原來情節這樣是可以的,或者是原來構思的那個人沒有特別地有意思,但寫的過程中會發現這個人要是這樣一個走向會更有意思一些。他就會不停不停地在探索的過程中出現,人物就是慢慢這么建立起來的。甚至隨手寫的人物會慢慢成為你的主要人物,這也是經常出現的,比如莊樹其實本來寫出來的時候,我并不知道他將來是最重要的人物,他只是莊德增和傅東心的孩子,但是寫著寫著,我就越來越喜歡他,喜歡他的無情,喜歡他的轉變,喜歡他最后的一些選擇。
但是你最開始出發的時候,肯定有一個大概的想法。不可能是從特別無知的一個起點開始,肯定是對這個人物有一定的了解,在寫的過程中不停地深化對人物的了解,不停地修正你對人物的了解,但不是圖解他。小說肯定不是圖解你內心本來就存在的一個東西,至少我不喜歡這種方式,所有機械執行的工作我都不喜歡。

一個創造者或者是一個普通人都沒有那么了解自己。發現人物的過程也是你了解自己的過程。很多人具備獨立的寫作人格,跟生活里的自己截然不同,因為藝術創作所運用的心理機制是非常復雜的,它調動的遠遠不是你在日常生活里使用的東西,而是很多另外潛藏在你內心深處的東西,自己也尚未了解的東西。當你寫作的時候,其實是不斷地在里頭發現自己的一個過程。那個樂趣存在于你會發現以前并不知道的部分,你會發現自己是這么理解這個人物的,你會對自己有很多有趣的認識,這也是寫作好玩的地方。有些人寫作上癮,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小說本身就是一個在自然生長的過程,會有長出來的東西,會有你在里面的探索,也會有它自己的出走,小說人物對你的叛逆也會有,這是比較自然的一種發展。不要害怕困惑,困惑的時候,或許就是產生價值的時候,很順溜反而會有點危險。
本文正文部分節選自《白色綿羊里的黑色綿羊》,較原文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發布,標題為編者自擬。內文圖片除注明外,均來自豆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