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在感官文化研究者康斯坦絲·克拉森的眼中,中世紀曾經是觸覺的時代,人們喜歡圍爐而坐、用手抓飯來吃,使用刀叉反而會被認為是做作可笑的。在中世紀的文學世界里,人們對觸覺也有著敏銳的意識。在喬叟的小說《賢婦傳說》中,講述者整日游蕩于綠草如茵的的田野,“顧盼著新鮮的雛菊,直待太陽由南方而轉向西沉。”對于那時的寫作者來說,大自然曾經只有前景。
后來的事我們都知道了,從十六世紀開始,城市里到處都是陌生人,消費行為無需跟鄰里接觸就能完成,身體接觸越少越好,親密的擁抱留給家中的愛人就夠了。我們變成更受規訓的、更加文明成熟的身體,而現代性的箴言變成了:“可以看,但不要摸。”
在《最深切的感覺:觸覺文化史》一書中,克拉森發現,所有人文社會科學對于觸覺體驗的忽視都十分嚴重,這種明顯的忽視對應著視覺的中心地位,也勾連出一系列人類歷史中的不平等偏見:注重隱私的貴族和擠作一團的平民、高高在上的人類和依賴觸覺的動物,當然,還有運用心智、習慣于凝視的男性和依賴身體感官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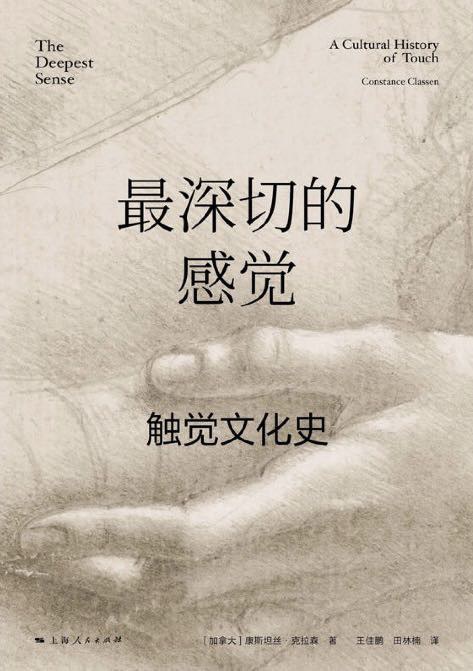
[加拿大] 康斯坦絲·克拉森 著 王佳鵬 / 田林楠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9
為了讓歷史事實不再是干癟的骨架,克拉森找到了許多具身性的歷史案例。在這其中,她還單辟出一章來講述女性的觸覺,以及它所代表的、迥異于現代的宇宙觀思考,而這對于今天不斷滑動著手機屏幕、與朋友相隔萬里的我們來說,無疑是深具啟發性的。
如同編織的女性寫作,超越藩籬

“女人說出的言語可能是輕柔的,也可能如薊草一樣鋒利,如荊棘一樣刺人。”
這句話既表明了女性的感官特征,又說明了女性觸覺的二重性:既能治愈人心,也潛藏危險。在克拉森看來,即使是富裕的女性也會被限制在家庭里,做一些縫補衣物、照顧孩子的工作,而一個出門在外的女人是與周遭格格不入的,即便她什么都不做,也會被看作威脅。因為女人的身體本來就具有令人愉悅的觸感,在一幅以感官為主題的十九世紀諷刺畫中,其他四種感覺都是由男性來表現的,唯有觸覺是由一名裸體女模表現。
那么,寫作的女性應該被放在什么位置上?這個問題頗有點復雜,克拉森認為,書寫和編織衣物有相似之處——都可以在家內進行,也都是某種手工作業。但寫出的作品有獲得公眾關注的可能,所以女性寫作時常被視為混亂的、流變的,會威脅到男性的社會支配,因而受到懲罰。詩人艾米莉·狄金森喜歡待在家里,墻壁柵欄和悉心照料的花園保護著她,她對公開出版不以為然,評論家便拿狄金森的自我隔絕大做文章,認為她在文學上”沒有母親,也沒有女兒“,如此一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把她掃除于傳統之外。

“少用她們的舌頭,多用她們的針線。針越是尖利,產出和快樂越多,但牙尖嘴利,卻會咬掉快樂。”詩人約翰·泰勒在1624年的《針的贊美》中這樣寫道。
但是,一旦嘗到甜頭,“牙尖嘴利”的快樂又豈能被輕易地收回?寫作如同編織,織成的不只是文本,也是多彩的幻想和女性交際網,這些幻想沖破了閨門,引起更多人的訝異和贊嘆。另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在著作《閨塾師》中,作者高彥頤注意到,那一時期存在著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婦女結社,結社中的女性通過讀和寫的創造性行動,在家內和公眾、想象和現實的界線間穿梭,即使生活在異地,婦女們也會互相傳遞詩集、序跋和隨筆。
有時,這種傳遞甚至超越了世俗的藩籬、陰陽的相隔。在當時的女性中間,湯顯祖的名作《牡丹亭》十分流行,讀者們著迷于它的新奇和熾烈,因受到感動而自己撰寫評論,因為她們認為男主角柳夢梅沒能理解杜麗娘的感情。最著名的《吳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還魂記》就出自三名女性之手,她們在不同時期嫁給了同一名男性吳人,其中兩名女性陳同、談則在寫完評論后就患病死去了,再由后來的妻子繼承她們的精神、完成評注的撰寫。最終,就如高彥頤所說,“一個愛情受創的女人杜麗娘的簡單故事,被編織成了一套有著沖突信息的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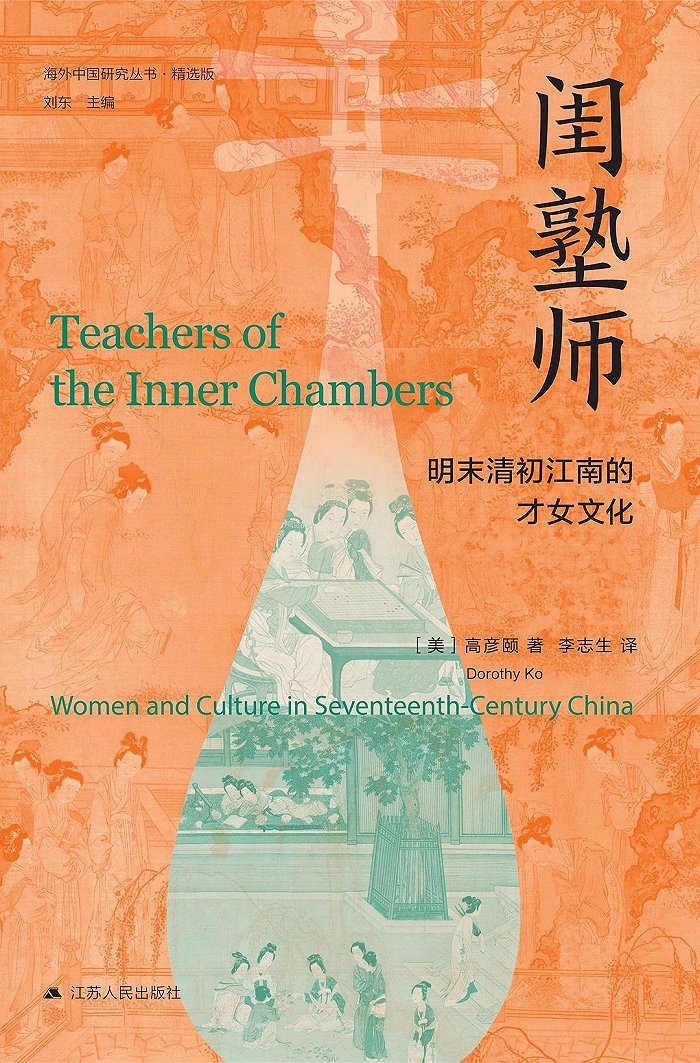
[美] 高彥頤 著 李志生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2-5
觸覺藝術與空間:從圍墻的家中眺望窗外
高彥頤認識到,雖然中國社會經常被認為是建立在“男女有別”、內外空間的分離基礎上的,但真實的實踐更加復雜,比起這個理想中的規范,女性棲居的領域更像是一個從內向外延伸的統一體,高彥頤將其稱為“浮世”,在浮世中,城市商品化而增長的財富讓婦女受教育的機會不斷增加,社會關系不再是預設的,而是因情境關系而定,儒家秩序中的長/幼、男/女、舊族/新門也日漸松動。
于是,婦女結社在閨閣的私人領地內組成,并延伸至親屬關系、鄰里和社會,她們一方面依賴著男性文人的交際網絡,一方面也自覺地參與印刷文化、訴訟、反清復明的顛覆行動,更重要的是,她們運用著才智和想象,棲居于遠大于閨閣的世界。
從內向外、不斷延續的空間塑造了女性的創作,這一點在《最深切的感覺》中也有所提及。手工藝品經常被看做是瑣碎和微不足道的,人們期待女性用她們靈巧的手工技能,為家里增添一點溫柔的氣息,但又不至于喧賓奪主,就如同打掃、縫縫補補那樣,可以被安全地帶回到女性的感官領域。
但事實上,克拉森發現,許多女性承擔了大規模的室內設計,而當眾多女性,比如母親、女兒和朋友們一同合作完成項目時,她們的成果尤其引人注目。
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富裕的酒商約翰·帕明特的女兒簡·帕明特和她的表妹曾經建造了一座舉世聞名的“圍屋”,據說是基于大教堂的形狀建造的,但又更像是鄉村的度假屋。它有著不同尋常的十六邊形設計,墻上覆蓋著親友們周游外地帶回來的貝殼、羽毛、樹枝和地衣,會客廳里裝飾著精致的海藻和沙地景觀。克拉森認為,這些材料產生了一種“持續轉化”的感覺:
收藏品變成了墻,墻變成了桌子,桌子變成了畫。房子里那些保持著平坦光滑的表面,通過對比的方式,使自身具有了一種令人頗感興味的質地。

通過這些自然材料,房子周圍的田園風光也被引入了室內,人們可以從房里向外眺望風景,也可以和風景建立親密的關系,八扇菱形的窗戶創造出既統一又裂變的視覺,簡直像是萬花筒的隱喻。克拉森寫道,帕明特姐妹不僅僅是在用手工裝飾房子,房子就是她們的作品,她們生活在自己的藝術之中。
無論是“圍屋”,還是閨秀創造的文學“浮世”,它們都不只是女性的手工實踐,而對應著一種與觸覺更為相連的空間概念。克拉森在書中描繪這種空間的模樣:人們在世俗世界仿效宇宙的同心圓模式,建造起四周城墻環繞的城市、屋子和花園,從界限到界限,從宇宙層次到宇宙層次,一直到最后在上帝之城之中安息。
在相當程度上,這樣的宇宙觀在現代已經失落了,人類的思維直接暴露在無限和失控的空間中,但同時又把自己作為主體封閉起來,身體陷入了孤獨的境遇。在《性差異的倫理學》中,女性主義學者露西·伊利格瑞曾經這樣寫道:“看筑起屏障,凍住觸覺的姻緣,麻痹感覺之流,結冰,讓觸覺沉淀下來,取消它的節律。”

伊利格瑞認為,我們其實一直擁有對觸覺的渴望與激情,只不過這種渴望被扼殺了,就像是把編織和手工藝品貶低為無關緊要,或者否認女人們的寫作能力那樣——“男人給她買房子,把她關在里面,憑借墻壁來擁有她、包裝她”,然后,男人就可以自己去受苦、背離肉身,為了營生去開發自然。跳出這種孤獨的封閉回路,不僅能夠讓女人擁有言說的機會,也意味著找回我們的觸覺。當相遇的機會愈來愈珍惜,或關愛的空間愈來愈狹窄,試圖擁有一點肌膚之親,也算是為這具身化的歷史,增添了一把小小的火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