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福爾摩斯和俠盜亞森·羅蘋初到中國時,民國的偵探小說家紛紛效仿。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學習了柯南·道爾塑造的福爾摩斯與華生的偵探組合,孫了紅的“俠盜魯平”則學習了法國作家勒伯朗筆下的羅蘋故事。程小青之子程育德在談到父親的創作時稱,《霍桑探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偵探小說”。它并非只寫歷險式的破案故事,也涉及社會問題,或多或少地反映小市民的苦難生活,且會突出其愛國的一面。
在《現代與正義 : 晚清民國偵探小說研究》一書中,復旦大學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員戰玉冰認為,偵探小說“與生俱來”的核心價值觀是正義,但在當時的中國,現實司法環境的匱乏使得偵探小說中的“司法正義”觀念難以為繼,很多中國文人是借著武俠小說中的“俠義”去理解“正義”觀念的。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民族國家危機的出現,“民族大義”也逐漸在偵探小說中出現。

戰玉冰將書名定為《現代與正義》,是想要特別強調“正義”的問題。“正義”一輯所選的三篇文章,在歷史時間和邏輯線索的層面逐步推進、環環相扣,從俠義書寫到正義想象,直至孫了紅的個人經歷——他筆下的“俠盜”魯平兼具俠客風采、現代偵探的才干和民族氣節的擔當,但“孫了紅本人卻貧病潦倒、一無所為”,在現實中證明了這種正義想象不過是一種“正義的虛張”。
01 有一青一紅,有搞笑滑稽:晚清民國偵探小說什么樣?
界面文化:為什么本書中使用的是“偵探小說”這個詞,而不是推理小說或犯罪小說?這些不同的命名之間有什么區別嗎?
戰玉冰:這里需要澄清一個由翻譯造成的歷史性問題。在中國,晚清民國時期“偵探小說”的名稱直接翻譯自英文“detective fiction”,日本當時將其譯作“探偵小說”。1946年日本推行“當用漢字表”,一度取消了“イ”為部首的漢字(后來又恢復了“偵”字),日本的“探偵小說”卻借機改名為“推理小說”,成立于1947年的“日本偵探作家俱樂部”也于1955年更名為“日本推理作家協會”。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江戶川亂步、松本清張、森村誠一等日本該類型小說作家作品譯介進入到中國,中國出版界和大眾媒體才開始將這一小說類型改稱為“推理小說”。
當然,如果進一步細究起來,“偵探小說”和“推理小說”的不同命名背后還是各有側重。“偵探小說”更突出對偵探形象的塑造,很多早期偵探小說都是一名固定偵探的系列探案故事。讀者讀過小說之后,印象最深的可能也就是偵探這個人物。而“推理小說”更看重推理與解答的過程,關注犯案的詭計是否足夠特別,以及解答的邏輯是否足夠嚴密。
至于“犯罪小說”,涉及范圍可能要更寬泛一些,凡是和罪案題材有關的小說都可以算到這里面,甚至不一定有偵探出場,也不一定要最終破案。比如我非常喜歡的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或是前些年被大衛·芬奇改編成電影的吉莉安·弗琳的小說《消失的愛人》,都是很精彩的犯罪小說,但它們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偵探或推理小說。
界面文化:你認為晚清民國有哪些最值得關注的偵探小說作家,為什么?
戰玉冰:民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偵探小說作家首推程小青。絕大多數民國偵探小說都在報紙雜志上發表,能出版小說單行本的人寥寥無幾,特別有名的也不過出版五六種單行本小說,這已經很了不起了。據我目前的統計,程小青在民國時期至少出版過七八十本偵探小說單行本,當然其中有一些小說的重新收錄和不斷再版,還有不少冒他之名的盜版之作。其中1941-1945年由世界書局陸續出版的《霍桑探案全集袖珍叢刊》為集大成,共計三十冊,堪稱民國時期本土原創偵探小說最大規模的一次出版行動。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也稱得上是后來影響力最大的民國偵探小說系列,直到前幾年,導演周顯揚還拍過一部電影《大偵探霍桑》,可見“霍桑探案”的IP影響力還在延續,只可惜最后影片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另一位可與程小青比肩的民國偵探小說作家是孫了紅,后來的研究者喜歡將其并稱為“一青一紅”。如果說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學的是柯南·道爾塑造的福爾摩斯與華生的偵探組合,那么孫了紅的“俠盜魯平”學的就是法國作家勒伯朗筆下的亞森·羅蘋。他倆一個寫偵探,一個寫俠盜,孫了紅的小說中還經常“請”霍桑過來客串,讓自己的俠盜魯平捉弄霍桑。
現在很多讀者可能知道福爾摩斯,但對于亞森·羅蘋不太熟悉,但這兩個小說系列在民國時期的影響力幾乎是旗鼓相當的。現在我們的流行文化中也依舊有亞森·羅蘋的影子。比如《名偵探柯南》中的怪盜基德,便是一個典型的亞森·羅蘋式的人物,他的對手就是頗有福爾摩斯風格的柯南/工藤新一。
此外,比較有趣的還有以趙苕狂、朱秋鏡、徐卓呆等人為代表的滑稽偵探小說創作,主要寫偵探查案如何犯蠢、出丑、失敗的故事,走的是搞笑風格,這類小說單篇來看可能會顯得比較簡單,但集中閱讀還是挺有意思的。還有五四運動健將劉半農(筆名“劉半儂”)、后來的新文學諷刺小說作家張天翼(筆名“張無諍”)等早年間都寫過偵探小說,創作水平也不差。20世紀40年代還有“女飛賊黃鶯”系列,可以把她理解為“女版俠盜魯平”,后來這個系列小說引發了大量電影翻拍,甚至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電影類型——“珍姐邦”,即女性邦德題材電影,影響力很大。

界面文化:你使用了一些當時偵探小說作家的作品作封面和封底,書中還有一個藏書票式的圖案。是為了向這些偵探小說家致敬嗎?
戰玉冰:全書封面和每輯之前的圖像元素其實都加入了一些小“彩蛋”。比如書的封面,用的是《新聞報》副刊“快活林”1916年12月31日第四張第一版的版面內容作為基礎元素,在這一期報紙上,程小青發表了他的偵探小說處女作《燈光人影》,從此程小青正式走上了偵探小說創作的道路。在這上面又疊了一幅1943年《春秋》雜志第一卷第二期刊載的插圖,這是孫了紅小說《木偶的戲劇》中的插圖,這篇小說寫的就是俠盜魯平如何捉弄偵探霍桑的故事。把民國偵探小說中創作成就最高的“一青一紅”同時放在書的封面上,也是想表達對這些作家先輩的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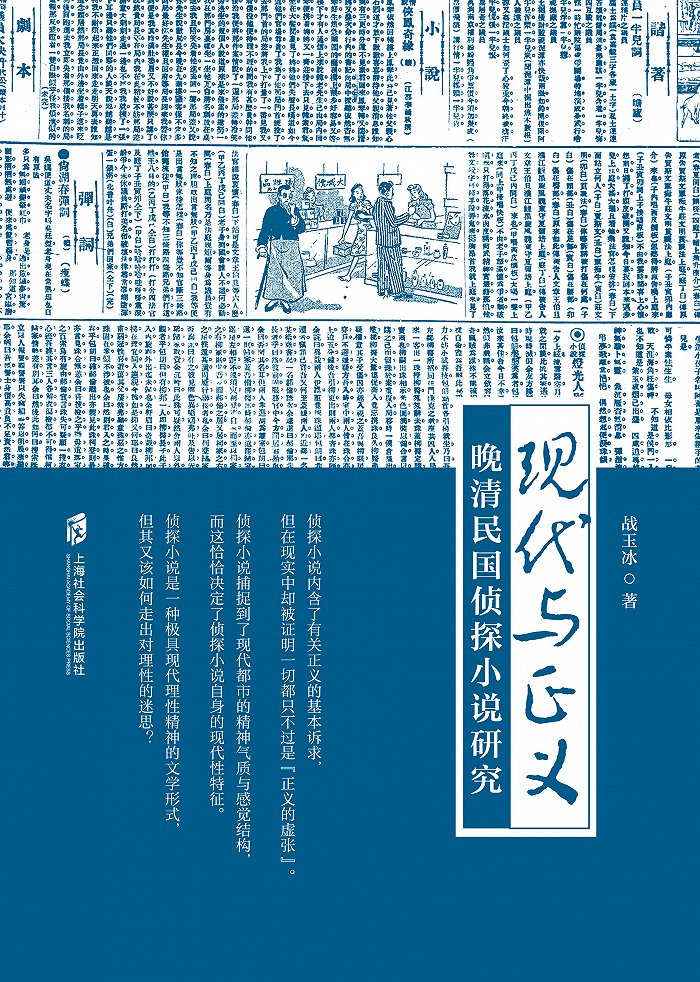
戰玉冰 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22-10
封底用的主要是1947年《新上海》周報第六十三期的報紙頁面,在這一期周報上,趙苕狂開始連載他的“胡閑探案”系列小說《魯平的勝利》。他的這個小說系列走的是滑稽偵探的路子,有點類似于今天《唐人街探案》的偵探喜劇類型,和“一青一紅”的正統偵探或俠盜故事都不一樣,我稱其為民國偵探小說的第三種發展路徑。

至于書中每一輯內容前面的圖案,用的是孫了紅小說集《俠盜魯平奇案》(上海萬象書屋,1949年3月三版)中的封面設計元素,其中四個圖像符號,分別代表小說集中的四篇小說《鬼手》《竊齒記》《血紙人》和《三十三號屋》。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小說封面就很喜歡,把它做成了藏書票的樣式。這還要感謝我的朋友華斯比,這本《俠盜魯平奇案》的原書來自于他的個人收藏。

總體上來說,《現代與正義》中這些圖像元素的選取和排布,還是有一點小小的設計心思在里面。或者說,這其中有一些我對歷史舊物的個人趣味,以及對前輩作家的致敬和懷念。

02 既是“舶來品”,也在“世界中”:偵探小說與中國
界面文化:讀者或許可以從書中理出一條線索——從過去的公案小說,到民國的偵探小說,再到反特小說,或許還能延續到今天的刑偵小說、推理小說與諜戰小說。它們之間有哪些繼承和不同之處?
戰玉冰:這個問題涉及到我近些年一個相對比較長期的研究計劃,就是對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發展歷史的整體性梳理與考察。《現代與正義:晚清民國偵探小說研究》是我對于中國偵探小說發展源頭,特別是其中一些比較有趣的問題所進行的個案研究。大概在明年上半年,會有一本上下兩冊共100萬字左右的《民國偵探小說史論(1912-1949)》出版,會更為系統地呈現民國偵探小說的發展歷史。
我今年剛寫完博士后出站報告《中國反特小說史論(1949-1976)》,探討了偵探小說進入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和變化,這時偵探小說是以反特小說的文類命名和形式特征出現的,其所關系到的核心話題也不完全是我之前兩本書中所討論的“現代性”問題,而是深度卷入到了“革命”的時代議題之中。目前已經完成的初稿有50萬字,主要討論了反特小說、電影、連環畫等幾種藝術形式。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增補、修改和打磨才能和讀者見面。
我現在正在著手展開的是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中國偵探小說研究。這里的“偵探小說”已經不能完成命名上的有效涵蓋,比如有以《啄木鳥》《東方劍》為代表的公安法制小說,有比較正統的本格或社會派推理小說,有麥家、小白、馬伯庸等人的諜戰小說,有相對寬泛意義上的驚悚小說或犯罪小說,還有新媒介語境下的網絡小說,以及大量相關影視劇作品或改編。其文學類型本身的復雜性和跨媒介形式的多樣性都意味著更大的研究挑戰。

我為自己訂下的一個小目標是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初步完成對中國百年偵探小說發展史的整體性研究。當然,中國百年偵探小說發展史也一定是在“世界中”的文學與文化語境之下才能獲得更為清晰的認知與呈現。同時,也像我在這本《現代與正義》一書的“后記”中所說,我對偵探小說的研究,并不是為了偵探小說本身,而更是想借助這一類型文學作為中介,考察百年中國的現代、革命、理性、正義等一系列重要議題。當然,這里涉及的問題就太大了,我所能做的也只是盡力而為吧。
界面文化:你談到,民國偵探小說的創作基本上還是“古典偵探小說”,而沒有進入現代偵探小說,甚至還是受到古典偵探小說中比較早期的作品的影響。在你看來,中國的偵探小說創作是何時真正與世界接軌的?
戰玉冰:一方面,偵探小說是一種文學舶來品,比如民國時期英國的福爾摩斯、法國的亞森·羅蘋、美國的聶格卡脫(現在統一譯作“尼克·卡特”)都經由文學翻譯進入中國,并影響了當時中國偵探小說作家們的創作,當然還有后來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埃勒里·奎因等人的作品。而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的肅反反特小說創作也是受到蘇聯同類型小說的影響。到了現如今,影響中國推理小說的源頭就更豐富了,比如來自日本的“社會派”或“新本格”,來自歐美的“冷硬派”或“舒適派”,或者好萊塢電影、美劇、日漫、游戲等跨媒介文化產品,等等。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偵探小說可以說從來都是和世界接軌的,只是不同歷史時期我們所想象和認知的世界并不一樣。而在民國時期,因為各種歷史原因,比如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對歐美偵探小說在譯介和接受上,存在一定的時間差。
另一方面,在我最近對相關問題的思考中,換一個角度來看,可能根本不存在所謂中國與世界接軌的問題,而是中國從來都是在世界之中。借用下王德威教授近些年很喜歡提的一個說法,就是“世界中”(being-in-the-world)的中國文學。簡單來說,偵探小說作為一種小說類型與文體形式,它是一直處在世界各國間不斷傳播流轉、“文學旅行”、譯介改寫與跨媒介改編的過程之中的,中國只是偵探小說在世界旅行過程中的一環。
其實,我們的偵探小說也可以反過來傳播到國外,比如早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新青年》雜志上就曾經刊載過四篇晚清民國偵探小說的日文翻譯,其中一篇的作者正是后來著名的歷史學家呂思勉,他年輕時也寫過偵探小說。當然,更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大唐狄公案》,這是中國文化元素成功進入歐美偵探小說與流行文化的一個典型案例。如果從這樣一個視角來看偵探小說的世界之旅,可能更有助于打破傳統的西方偵探小說“影響論”或者中國與世界接軌這種比較單向度的思考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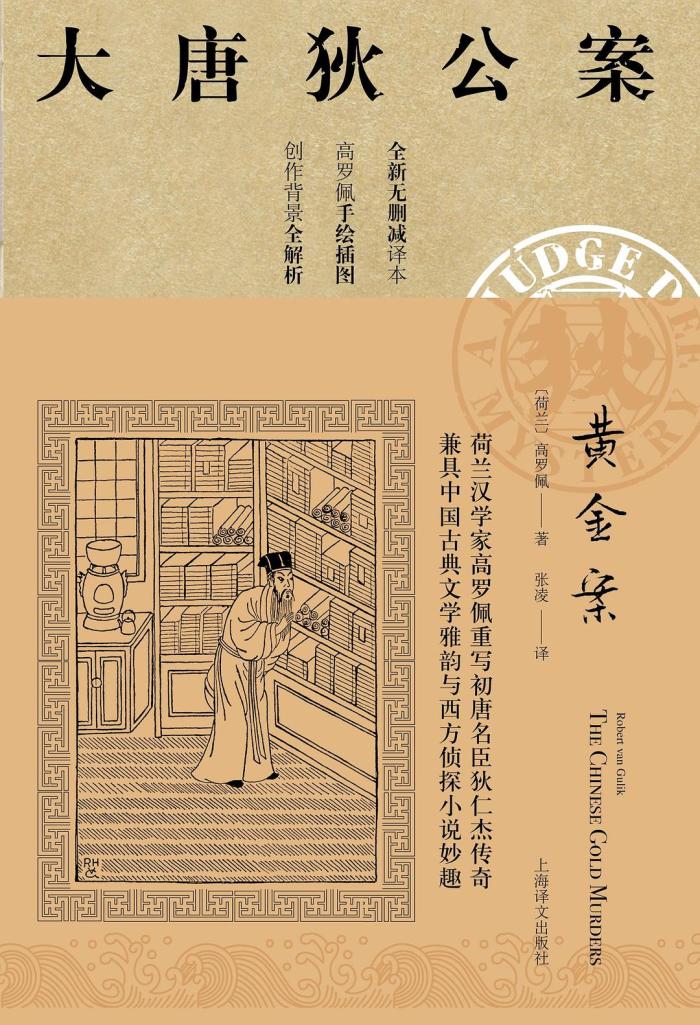
[荷] 高羅佩 著 張凌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9年
03 新或舊、嚴肅或類型?二元視野正失去有效性
界面文化:在你看來,晚清民國時期的偵探小說作為一種通俗小說,和當時的嚴肅文學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
戰玉冰:這里面包含著一系列有趣的學術史問題。首先需要辨析一組概念,我們現在所說的嚴肅文學/通俗文學,或者純文學/通俗文學的二元區分,其實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之后才發展成型的說法。回到民國時期的文學現場,當時被建構出來的一組二元對立是五四新文學/鴛鴦蝴蝶派文學,偵探小說被劃分在“鴛鴦蝴蝶派”陣營之中。
當偵探小說最初進入中國時,是被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作為“新小說”來進行翻譯和推介的。當時在梁啟超等人看來,偵探小說、政治小說、科幻小說等都是西方現代小說類型,對這些小說的引進是有助于中國現代化改革和發展的。從梁啟超、林紓,到劉半農、程小青,都曾說過讀偵探小說有利于啟發民智、改革司法,或者提高警察辦案效率,以及增強一般民眾的自我保護意識等等,他們強調的是偵探小說的“新”和“有用”的價值。
而作為“新小說”的偵探小說在“五四”之后則被歸入到“鴛鴦蝴蝶派”,淪為了“舊小說”。從實際內容上來看,把偵探小說和徐枕亞、張恨水等人創作的典型的“鴛鴦蝴蝶派”作品歸為一類顯然是有問題的,他們彼此間的差異要遠大于共性。換句話說,所謂“鴛鴦蝴蝶派”,并不具備某種文學本體論上的一致性,而是作為“五四”新文學的對立面被不斷建構出來的。在這里,他們突出的是偵探小說的“舊”和“消閑”、“游戲”等面向。
其實,無論是說偵探小說的“新”和“有用”,或者批評它“舊”、“消閑”、“游戲”,都有其具體歷史語境下的合理性。我們也需要注意,這里無論是說偵探小說“新”或“舊”,都有其潛在的文學參照系,即它是相對于中國傳統小說或五四新文學而言的。所以在我的研究中,有時會刻意回避使用“通俗文學”這個概念,因為這個提法其實還是沒有走出五四新文學的陰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論證的觀點好像永遠都是通俗文學其實也不比五四新文學差。相比之下,我更喜歡使用“類型文學”的概念,強調偵探小說作為一種小說類型自身內部的形式特征和發展軌跡,并且也可以像之前所說的,將晚清民國偵探小說放置于偵探小說世界旅行的背景之下來展開考察。
這里還需要兩點補充:第一,不同發展階段的中國偵探小說和與其同期的五四新文學,以及言情、武俠小說等等,共享了同樣的社會歷史與文化政治語境,因而具有某種相關參照的可能性和比較研究價值。第二,“類型文學”的概念自身也帶有通俗文學、大眾文化的意義內涵,即我們必須承認,通俗文學這個概念本身還是很準確地揭示出了這些文學作品所具有的消費市場和市民讀者取向,只不過除此之外,“類型文學”更強調這種文學形式獨立發展的脈絡及特征。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談到作家小白的作品《租界》《封鎖》等雖然是以諜戰小說為內容取材和類型框架,但本質上是“反類型”的。這也讓我想到一些文學作品看起來是犯罪題材,但大家從來不說它們是推理或懸疑,而是直接將其納入嚴肅文學。在你看來,類型小說與文學的邊界在何處?
戰玉冰:我們所說的類型小說與嚴肅文學的分野,或者說雅俗分野,其實是各種話語不斷建構之下的產物。這種建構確實能揭示出歷史上文學發展的一些基本態勢,但并不一定具備長時段視野下的解釋力。比如從莎士比亞戲劇最初上演到后來不斷被經典化的過程,就是一個由俗變雅的動態過程與典型案例。

小白 著
讀客文化·河南文藝出版社 2022年
特別是到了今天,越來越多的作家其實是在通過自己的創作來不斷打破這種分野。小白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代表,他之前寫的小說多是諜戰題材,但我們不能僅僅把他歸類到諜戰小說這一小說類型之中,他作品中所帶有的知識分子的、先鋒的甚至后設意味的寫作傾向,完全是嚴肅文學的,但他小說中的基本題材內容與情節推動方式又是類型文學的。這樣的例子其實還有不少,比如近些年很火的“東北作家群”,雙雪濤、班宇、鄭執作品中所觸碰的核心內容,是時代轉型之下的個體創傷性回憶,是典型的嚴肅文學,但他們進入這段回憶的寫作手法又往往是基于犯罪小說的懸疑框架,通過對罪案真相的找尋來恢復記憶與歷史的真實。
在西方,運用偵探小說或犯罪小說框架來寫嚴肅文學的作家就更多了,比如博爾赫斯、莫迪亞諾、保羅·奧斯特等等。簡單來說,他們在小說中借用偵探小說的類型框架,主要是將偵探小說中的“找尋”作為自己故事展開的基本動力,只不過要找尋的東西不僅僅是某一起案件的真相,而更多是有關于身份、記憶、歷史,乃至“找尋”本身是否可能等問題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來看,類型小說與嚴肅文學之間的邊界似乎是在不斷模糊的,或者說我們為歷史上一些文學發展狀況所建構出來的這種二元視野,在當今文學創作的新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失去了其解釋的有效性。
04 文學與文化,文本與文類:學術研究不應存在鄙視鏈心態
界面文化:過去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或評論家貌似只讀純文學而輕視流行小說,但現在很多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好像越來越關注流行通俗小說,比如近期研究晚清民國時期的科幻似乎也很流行。你認為這股研究潮流從何而來,它們是最近幾年才熱門起來的嗎?甚至有人會擔心這樣會將文學研究引入“媚俗”或“庸俗”的歧路,你對此有何觀察?
戰玉冰:這其實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首先我覺得學術研究不應該存在這種“鄙視鏈”心態,比如認為研究通俗文學不如研究純文學,按照這個邏輯我們就會得出研究現代文學不如研究古代文學、研究明清不如研究唐宋、研究近古不如研究先秦等等一系列奇怪的推論和認識。
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文類屬性的文學都有其各自的特點,都有其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比如海外學者在面對流行歌曲、色情小說、都市怪談或肥皂劇等具體文本與文化現象時,同樣可以做出相當精彩的研究。
當然,我們必須要承認民國偵探小說作品不具備某些純文學作品所能夠達到的審美價值,在文學品質上也遠不能和某些嚴肅小說相提并論。但一方面,文學研究不能局限于狹隘的審美研究,這在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興起之后就變得更加明顯了。我自己書中的很多內容也是受文化研究,特別是受其中所謂“物”的關注與轉向這一趨勢的影響,比如我在書里討論火車、照相機、易容術等相關內容。
另一方面,也正如我在書里所說,對于傳統經典作品,我們發展出了“文本”這一超級概念,“文本細讀”是我們面對經典文學作品時的重要處理手段之一。但面對偵探小說這樣的類型小說時,我們則要提倡“文類”的概念,即如詹姆遜所說的將文類的整體作為勾連具體文本與社會歷史進程的中介物,這里存在著研究路徑上的各有側重。當然,偵探小說研究也并不排斥“文本細讀”,其中也有一些作品具有足夠的文本復雜性,是經得起我們的“細讀”的。
最后,我想說,我自己雖然做偵探小說研究,但我也承認對通俗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熱潮提出批評并非完全沒有意義。作為學者,你研究什么當然都可以,只看你能不能把這個研究做好。同時作為一名老師,我也清楚地知道,文學與文學教育還承擔著某種經典傳承和審美教育的功能。也就是在我們的文學課堂上,需要讓同學們了解從莎士比亞到卡夫卡、從李白杜甫到《紅樓夢》、從魯迅到沈從文的文學意義之所在,需要幫助同學們養成判斷文學作品好壞并欣賞優秀作品的基本能力——當然這種標準與能力也是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的。在這個意義上,對未來可能會過于泛濫的文化研究傾向提出警惕的聲音,我認為也是有必要的。或者不妨說得稍微極端一點,如果對經典文學缺乏足夠的感受力和判斷力,其實也很難真正做好類型小說或通俗文學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