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我無法呼吸,心臟劇烈跳動。只見一個少年沖進來,朝我小跑而來。
我往前跨了兩步,把他抱進懷里,勒住他。我沒來得及把他看清楚,只模糊地意識到他比我高一些,可我還是感到他很幼小,像一個小小的脆弱的胚胎一樣在我懷里。我必須捧著他、拽緊他、容下他,把他放回我的骨頭里、血液里。”
14年又57天后,孫海洋再一次地,把兒子孫卓抱在懷里。他們的擁抱隔著跨越千山萬水如大海撈針般的苦苦尋覓,隔著一次次日升日落帶來的希望與絕望,隔著一位父親的頑強與堅持:他在自己的包子店打出了“懸賞二十萬尋兒子店”的招牌,引起全國媒體注意;他在尋子途中結識了越來越多背負著相同傷痛的家長,與他們一起尋找孩子,呼吁公眾對兒童拐賣問題的重視;他向導演陳可辛講述自己的故事,陳可辛聽罷感慨萬分,以他為重要原型拍攝了電影《親愛的》……
他的執念引起了社會的回響。公安部門相關人員、學者、記者、公益機構負責人等形形色色心懷正義的人促成了兒童失蹤快速查找機制、流浪兒童救助和管理制度,以及全國打擊拐賣兒童DNA數據庫等制度的完善,大大提高了拐賣兒童案件的偵破效率。2021年,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開展“團圓行動”,截至6月11日找回了1737名被拐兒童,其中包括孫海洋熟知的多件舊案。到這一年的12月6日,孫海洋終于與兒子重逢。

2007年孫卓被拐失蹤時,姐姐孫悅還是個9歲的孩子,父親的尋子經歷自此填滿了她的成長過程。孫悅從小就有寫日記的習慣,也曾嘗試寫過一些短篇小說。隨著自己逐漸長大,一個想法在她的心頭醞釀開來:作為“孫海洋尋子事件”的親歷者和最近距離的旁觀者,在十幾二十年后的將來,在自己足夠成熟能將這如亂麻般的現實理順的時候,把這個故事記錄下來。這個想法成型后的第二年,一家五口的團圓就給了孫悅立刻動筆的契機。她說,“覺得這個故事已經完整了,已經有了一個句號了,那它本身就有意義了,我就覺得好像一個幸存者一定要把這個故事記錄下來。我是一個證人,無論是見證了我們家的故事,還是這個小小的歷史片段。”
她花了四個月的時間構思、采訪、寫作,將這個故事記錄在《回家:14年又57天》一書中。日前,孫悅接受了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的采訪,與我們講述了她寫作過程中的思考與感受。

01 近乎隱身的姐姐,發掘記憶與夢境
《回家》以孫海洋第一人稱的口吻和視角講述了孫卓回家的故事,作為執筆人,孫悅既是父親尋子之旅的旁觀者,又是這個被拐兒童家庭的一份子。在孫悅看來,這個雙重身份讓她相對于一般從事此類紀實寫作的調查記者有更多的優勢。“這個故事從小就發生在我身邊,我本人常常在故事現場,對這個故事來說有絕對的近距離,比如說我不用去克服采訪或挖掘故事的難題,采訪過程中爸爸對我全盤托出,沒有太多建立信任的困難。”她說,“書里其實有很多細節來自我自己的童年回憶、親身體驗和理解,我覺得這可能會讓文本更細膩,更加真實。”
“那天我猛然間發現,自己的妻子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她跪坐在地上,還張著嘴哇哇地哭。那哭聲像一個瀕死之人發出的呼救,像生不如死的人在病榻上告饒,那種無意識的呻吟從她的身體里無力地涌出來、溢出來。那張連日浮腫的面孔浸滿了淚水,因為過于用力而扭曲變形。兩道鮮血蜿蜒著從額頭流下來,把她的臉割裂了。”
孫悅在書中描述了孫卓走失三年多之后,孫家經歷過的一段異常動蕩難捱的時期。彼時孫海洋在家的時間不多,但一旦在家屋里的人——他、妻子四英和母親——總會爆發爭吵,在彼此傷害中發泄痛苦。有一次,孫海洋與四英再次爆發激烈爭執,四英一邊大哭一邊用頭撞墻,突然跳起來沖進廚房,拿了一把刀跪在孫海洋面前,磕著頭說:“你把我殺了吧!”
“孫悅就在旁邊看著這一切,沒有什么反應。”孫悅用寥寥數語點明了自己的在場,但種種如昨日重現般的細節,又為我們揭示了這個在爭吵中被冷落一旁的孩子絕非“沒有什么反應”,她將大人們的悲傷與絕望牢牢記在心底,又在長大成人后付諸筆端。
她在采訪中提到,“他們吵架的畫面,媽媽磕頭的表情、聲音、動作還有狀態,來自我自己的記憶,我按照我真實的記憶去寫媽媽發瘋、崩潰的樣子,我有我的理解和感情。過了這么多年,爸爸的講述是沒有辦法把這些細節還原出來的,他只能告訴你這個故事是怎么樣的、當時是怎么吵的、他的心情是怎么樣的。但很多細節來自我的記憶的話,(文本)會更加回到當時的情境,讀的時候可能更有畫面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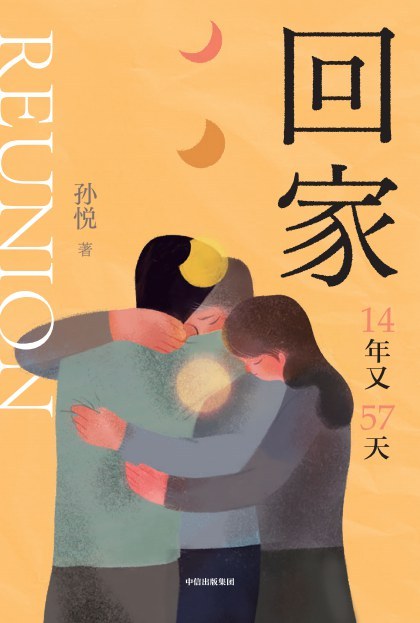
孫悅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2-9
孫悅在書中出現的場景屈指可數,她近乎隱身的狀態甚至會讓讀者在閱讀《回家》時,不自覺地忘記這個故事的講述者其實就是孫海洋的女兒、孫卓的姐姐。她認為“隱身狀態”不是刻意處理的結果,十多年來,她確實在父親的保護下置身事外——為了保護女兒,孫海洋刻意杜絕孫悅與記者或其他尋子家長接觸。
回憶過去十多年的時光,孫悅用“逃避”一詞形容當時的心理狀態,“就像爸爸把我保護起來,我從很小開始就自然而然建立起了一種防御心理和自我保護機制。我幾乎不會和身邊的朋友說我還有一個弟弟,別人很難理解這么沉重的事情。我自己也不會天天去想這件事會給我造成什么影響,他能不能回來,或者如果沒有這件事的話我們家會怎樣。”在采訪中,她依然注意不讓自己流露出過多的個人情緒,我們只能在文字間想象,當弟弟被拐的沉重現實砸向這個剛在深圳扎根的家庭時,當父親為尋找弟弟常年在外奔走、母親和奶奶因自責而心碎時,當另一個弟弟因孫卓的“消失”而“來臨”時,被動承受著這一切的孫悅的內心感受。
有讀者對孫悅說,覺得《回家》的前半部分明顯更忠于孫海洋的直接經驗,后半部分更像她的摹寫。她也承認,在寫前半部分的時候,特別是父親年輕時的經歷,“沒有找到屬于我的位置”,寫作前期像是父親的代筆,僅是把父親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記錄下來。這種狀態在寫到第八章“夢”時發生了變化:2008年,步履不停尋子的孫海洋在愈發沉重的心理壓力下頻繁地做噩夢。
夢作為極度主觀、白晝到來消失無蹤的東西,既真實又很難處理。孫悅一直知道父親在弟弟丟失前做的那個夢:一大家子人圍著桌子吃飯,只有孫卓不在。在寫到父親噩夢頻頻的那一章時,孫悅頓悟——夢境這樣的虛構空間,反而能為表達人物心理狀態留住一個更感性、更能自由表達的空間。
“一切都在流動,只有黑夜在我的頭頂紋絲不動,平靜、漠然地俯視著我。在我出生之前,黑夜就這樣存在著。當我在大街小巷里狂奔,而我的孩子正離我遠去時,黑夜也無動于衷地注視著這一切。等到有一天我死去了,黑夜依然巋然不動,人類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對它毫無意義。在黑夜的看守下,世間萬物有序地流動與交替。”

從那時起,她感到自己不再只是父親的代筆,而是一位在創造的寫作者。“我找到了‘假如我是孫海洋’的感覺——他的眼睛看到的,他的心靈所感受到的,我能夠代入進去,通過我的口吻去想象,去講故事。我琢磨了很久要怎么把它呈現出來,既有表達力,又不那么尖銳。我琢磨了很久,就想通過夢的形式。當我代入到主人公身上,去想象他在當時的心情和經歷下會做什么夢,我就完全進入到這個人物的視角里了。”
02 找尋比“小家回憶錄”更大的意義
“把孫海洋尋子”放到更大的社會圖景中去,是孫悅從動筆開始就有的野心,她希望《回家》能有“比一個小家的回憶錄更大的意義”,但要怎么做呢?編輯程利盼給了她很多意見與鼓勵,特別是向她推薦了很多書。孫悅閱讀了不少非虛構作品,邊讀邊揣摩別人是怎么寫的。在寫了幾章后,她從梁鴻的《中國在梁莊》汲取靈感,決定在每一章的結尾引用相關新聞報道、評論分析或法律條文,話題涵蓋改革開放城市化進程中影響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大趨勢與時代隱痛,包括農民進城、流動人口與留守兒童、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法律條文、司法實踐和相關評論、拐賣兒童的新聞報道等。
這給了孫悅一個超越個體家庭的、更宏觀的視角,“就像書里所寫,進城對父母來說意味著改變命運。他們的命運確實也改變了,只不過難以預料還有如此重大的附加代價。改革開放之后經濟飛速發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其中就包括人口拐賣犯罪的猖獗。”
她努力在書中呈現兒童拐賣犯罪的成因:“比如說內因是思想觀念,有的地方比較重男輕女,一定要有兒子傳宗接代、養兒防老,如果這戶人家沒有生兒子,村民就會對他們指指點點,這個思想內因很難改變。外部也有很多問題沒有處理好,比如說買孩子登記戶口的問題。一個孩子買回去后可以輕而易舉地上戶口,還有人會去買出生醫學證明來幫助孩子上戶口,那出生醫學證明又是從哪里買的呢?存在很多問題,如果我們不投入更大的力度去管制,就很難得到解決。我們也希望引起公眾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只有當大家都知道這事是有問題的,問題被解決的那一天就會來得更快。”
孫悅記錄了許多孫海洋在“尋子打拐”行動中的見聞,部分地區居民對人口拐賣麻木漠然,買家賣家振振有詞,令人心悸。孫海洋曾在湛江見到四位服刑過3-10年的出獄人販子,不僅毫無悔意,而且憤憤不平地認為自己將因超生無處可去的女嬰送去福利院而不是任她們自生自滅是做善事,咬定真正的人販子是將大量幼童送出國牟取暴利的不正規的福利院。
在書中,孫悅還記錄了一個讓她本人震驚不已的案例:廣西藤縣的農民梁某花了1萬塊買了一個男孩,花了3000塊買了一個女孩,他們都有“合法”的出生證明和戶口,更令人吃驚的是,連他的老婆也是從越南買來的。她憤怒又難以置信地寫道:
“他一個人購買了三口人,就這樣湊成了‘幸福的一家四口’。這簡直是荒誕至極。可當地的村民都習以為常,不以為意。這是中國鄉村存在的情況——沒有孩子就買孩子,沒有老婆就買老婆,也不會有人去舉報買家。在許多人的觀念里,只要買進了家門,門一關,這就是別人的家事。誰又管得著呢?”
查閱了大量案例資料及法律條文之后,孫悅覺得,法律法規的滯后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上述情況的發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的軟性條款為買方提供規避法律責任的漏洞——《刑法》第241條第6款規定,“售賣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他們屢次犯法卻從未獲罪,買賣同罪依然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目標,也因此難以有效遏制人口交易的需求端。
2022年6月,孫卓被拐案的嫌疑人吳飛龍被建議判處五年有期徒刑,此事迅速在網上引起熱議。爭議源自司法實踐中“拐賣”和“拐騙”相距甚遠的量刑標準(前者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處死刑,并沒收財產;后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孫悅在書中以孫海洋的口吻直言,無法接受這一量刑建議。在本次采訪中,她再次表示了拐賣和拐騙區別定罪的不合理,“(拐賣和拐騙)唯一的區別是人販子究竟有沒有收錢,有時候你找不到證據,可能確實是送給別人養,但人販子肯定拿到了其他的好處,這中間沒有那么大的區別,但給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給被拐兒童家庭造成的傷害是一樣的。”

從數據上來看,兒童拐賣問題正在好轉,得益于兒童失蹤快速查找機制、流浪兒童救助和管理制度,以及全國打擊拐賣兒童DNA數據庫等制度的完善,今天的被拐兒童和十多年前相比已經少了很多。孫悅對此表示樂觀,但她同時也承認這是一個難以根除的社會問題。在《回家》的結尾,孫悅寫到了孫海洋認識的最年輕的尋親家長,已經是90后了:
“‘90后’在我眼中已經是下一代人了,連我的下一代人都走在這條無窮無盡的路上……當人都成了商品,我們丟失的究竟是什么?”
孫悅提出了這個她無法回答的問題,社會沉疴的復雜程度或許遠遠超出了這個年輕女孩的理解范圍。根據美國歷史學家任思梅(Johanna S. Ransmeier)在《清末民國人口販賣與家庭生活》一書中提出的觀點,中國人口販賣問題之悠久頑固,建立在儒家等級制與中國式家庭的交易本質的基礎之上,對(男性)子嗣、家族傳承的追求合理化了買賣家庭成員的行為。回頭再看《回家》中記錄的種種,我們不難發現,巨大的文化慣性依然驅使著社會隱秘角落中的一小部分人鋌而走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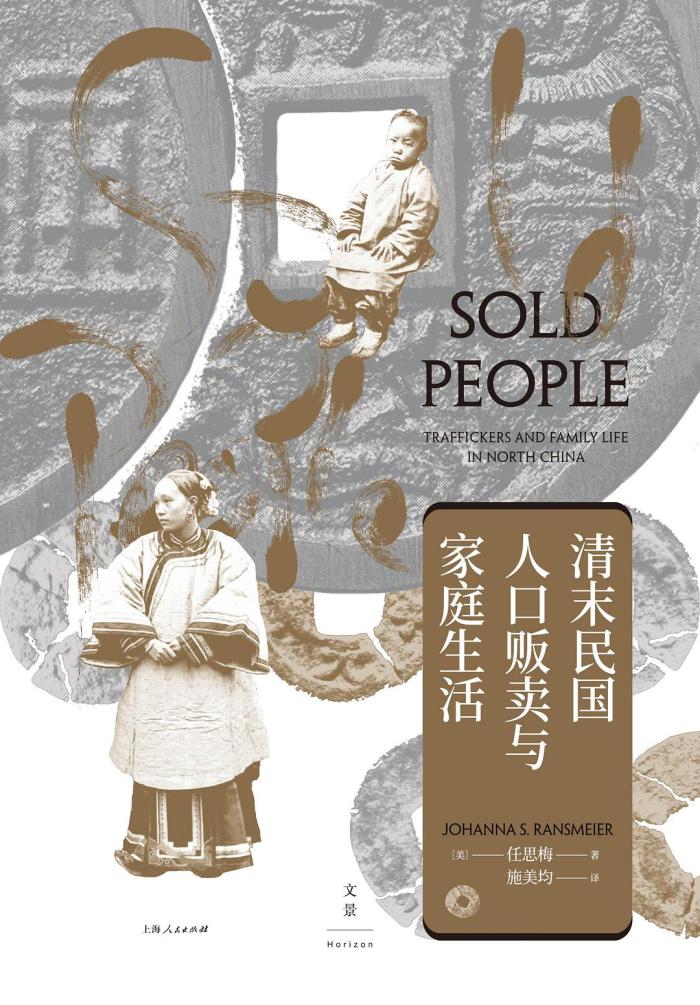
[美]任思梅 著 施美均 譯
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9
03 尾聲:每個人手里都舉著火把
在寫作《回家》的過程中,孫悅對父親有了全新的認識。前幾章寫的是孫海洋從農村來到一線城市扎根的前半生,對于孫悅來說,這是她第一次認認真真地聽父親講過去的事情。她對過去十多年中父親跌宕起伏的心路歷程有了更深的體察,也不回避在書中展示父親不那么“偉光正”的一面:常年在外奔波疏于對家人的照顧與體諒,在其他尋親家長找到孩子時難以遏制嫉羨交加的復雜情緒……“我不想把他塑造成一個全能的,或者完全沒有負面情緒的英雄,”孫悅說,“他就是一個人,是人的話就會失落,會絕望,甚至會嫉妒。我希望他是一個‘人’,我覺得人的呼喊和掙扎是更有力量的。”
《回家》是孫悅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她承認對這本書仍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比如語言和結構仍可再好好打磨,人生閱歷不夠導致思考不夠深入,雖然想把很多問題寫得很深刻,但難以用語言表達到自己想表達的程度。“但無論如何,雖然它有很多缺陷,對我來說是非常真摯的聲音,就像我來到世界上學會說的第一句話一樣。”
“一方面想讓大家通過《回家》了解到拐賣兒童的問題,呼吁大家站在一起保持發聲,讓‘天下無拐’早一天到來。另一方面希望通過‘絕望之下希望尚存’的故事,給人們帶來面對生活、命運和未來的力量。就像書的結尾所說,‘總有一個明天會積雪盡消,到那個時候,我們抬頭一看,只見每個人手里都舉著火把。’”她說,“火把是書里多次出現的一個意象,象征著人們心中的信念和勇氣,它一定會為我們照亮那些黑暗的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