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社交媒體制造的“成功媽媽”范本,正在闖入縣城媽媽的世界。
當另一種生活突然近在咫尺,縣城媽媽們所面對的,是既割裂,又千絲萬縷的兩個世界。她們既看到了培養出一個“精英牛娃”的誘惑與焦慮,也看到了自己所遭遇的話語權、婚姻、母職焦慮等困境。
當焦慮和誘惑開始下沉,一些縣城媽媽,開始渴望“逃離”。她們的共同畫像,是年齡都在30歲左右,是社交媒體的深度用戶,都關注育兒、女性等話題。而她們的“逃離”,往往也跟育兒有關。比如,有位縣城媽媽,寄希望于在縣城開一家高端母嬰店,來逃離縣城生活方式,結果因為當地人買不起,最后瀕臨倒閉;還有位媽媽,遭遇了失敗的婚姻,在刷了一堆谷愛凌的短視頻之后,定下目標,要“向谷愛凌看齊”,把逃離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這是一個巨大而沉默的群體。截至2021年底,全國共有2843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約2.5億人常住在縣城里,其中有相當數量的縣城媽媽。她們多數在縣城出生,又在縣城實現多個社會角色的轉換,完成家庭、生育直至所有的人生。
而當腳下縣城的土壤,生長出遠方的城市鏡像,卡在母親、妻子和縣城女人三重身份之間的縣城媽媽們,正試圖重新定義自己的人生。
文 | 鐘藝璇
編輯 | 易方興
運營 | 月彌
鏡像與現實
鏡子,出現在了縣城媽媽王小鈴的生活里。鏡子里是谷愛凌,鏡子外是36歲的她。她在河南新鄉原陽縣生活,離了婚,正獨自撫養一個讀大班的5歲女兒。
因為“想向谷愛凌看齊”的言論,在社交平臺上,她甚至遭遇了一場“網絡暴力”。今年2月中旬,她發了這條視頻之后,熱度是過去的十倍。在那之前,她一直在網絡上分享單親母女的縣城生活。幾百條評論涌來,有人說她做白日夢,還有人說,“沒有谷愛凌的命,得了谷愛凌的病”,更有人拿出谷愛凌的三代,證明她是癡心妄想,“首先你得是斯坦福的博士,外公外婆也得是國家級科學家、數學家……”
但王小鈴總記得自己第一次刷到谷愛凌短視頻的感受。她的第一反應,不是谷愛凌優秀,而是“她的媽媽一定很厲害”。她努力想了一下措辭——那是一個成功的單身母親,一種精英的感覺。
而她自己也是單親媽媽,也有一個女兒。短視頻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一個新的可能,“雖然起點不一樣,天賦不一樣,家庭背景不一樣,但我還是想給孩子創造一個好的起點”。
然而,這面鏡子的背面,是一個縣城媽媽深陷其中的生活。王小鈴和丈夫在3年前離婚,與許多縣城女性遇見的問題相似——她遠嫁到其它縣城,遇到一周回一趟家的丈夫,以及沒好臉色的婆婆,沒有社交圈,生活里總是退讓。
在這段婚姻里,她沒收到彩禮,還要為沒寫她名字的房子和車子還貸。結婚前夜,丈夫跑去和朋友喝酒,酩酊大醉;懷孕產檢,她挺著肚子,獨自去收費臺付錢、跑檢查項目。她從未見過丈夫的工資卡,連對方的手機都打不開。明明兩個人坐在彼此面前,在一間屋子,甚至躺在一張床上,“卻比陌生人都要遠”。
有一次,她因為將上衣與褲子晾到了一塊,又被身后的婆婆吼了一頓。那天,她也挨了領導的罵,終于忍不住,與婆婆大吵了一架。隔天,丈夫來了一個電話:“離婚吧,一周之內搬走。”
王小鈴的婚姻就這樣結束了。
與面對失敗婚姻的王小鈴不同,豎立在另一個縣城媽媽陳芳鹿面前的,是另一面鏡子。
對31歲的陳芳鹿來說,這面鏡子所映照出的,是社交媒體里大城市的精英式生活方式,還有那里的媽媽們所培養出的“精英牛娃”。
她住在河北張家口涿鹿縣,家境不錯,有一兒一女。由于離北京近,她所選擇的一切,都與北京對標。懷二胎的時候,為了給孩子“好的東西”,她開了一小時高速,去張家口市區母嬰店,開了張3萬元的會員卡。她極少在縣城消費,幾乎都網購,有一天她驚奇地發現縣里又新開了家甜品店,朋友卻告訴她,已經有小半年時間了。就連點痣這樣的小事,都要去北京,“我在北京安貞醫院點的痣,花了240塊”。
踐行這樣生活方式的極致,體現在她加盟了一家高端母嬰店上,她渴望通過復制城市的生活方式獲得成功。但是,店里紙尿褲要賣158元一包,面對這樣的高消費,縣城人來了又去,問清價格轉頭就走。不得已,價格一降再降,從158元一包降到了99元一包,幾乎沒有利潤。
“有顧客問我,這個價格在網上都可以買3包了,我說能一樣嗎,一包紙尿褲,她們恨不得里頭有100片”——從交談里,你總能感受到她對于縣城的一種排斥。
回頭客的周期也格外長。最近來陳芳鹿店里的一位媽媽,上一次到店里還是6月,一包紙尿褲用了3個月。因為,這個媽媽只有晚上才舍得給孩子穿紙尿褲,至于白天,“就晾著”。
作為社交媒體的重度用戶,鏡中的世界,原本讓她覺得,“現在年輕的寶媽,要求也會高一點”,所以才開了這家母嬰店。但另一面的現實是,就連她母親都反對她,“一盒奶粉400元,孩子一個月得喝2、3罐,在縣城打工一個月不過3000塊,誰會花1000多塊給孩子買奶粉?”
像陳芳鹿和王小鈴這樣,盡管她們面對的現實不同,但無論是婚姻還是創業的失敗,這些縣城女性最后都要回歸到同一個身份上——縣城媽媽。
這是一個巨大而沉默的群體。截至2021年底,全國共有2843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約2.5億人常住在縣城里,其中有相當數量的縣城媽媽們。她們多數在縣城出生,又在縣城實現多個社會角色的轉換,完成家庭、生育,直至所有的人生。

▲ 圖 / 《成為母親》截圖
孩子是唯一目標
在遭遇失敗之后,人們有時候會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對于縣城媽媽來說,在事業、婚姻等為數不多的選項中,孩子幾乎是唯一可寄托的目標。
成為單親媽媽之后,王小鈴決定“逃離”縣城。曾經生活的縣城看不到高樓大廈,看不到人擠人,一天下來,甚至連公交車都少見。她不想再回到那個“自行車20分鐘可以繞遍”的地方。
“壓根就不想在縣城待,縣城把你磨得光光的。”她說。
她采用的方式,是試圖讓女兒的生活與縣城脫離。比如,她從不給女兒講述縣城,更多會講國外的故事。盡管她從未出過河南,但她和女兒會躺在床上,刷著關于埃及金字塔、意大利古建筑的短視頻。她提起“埃及金字塔”的頻率很高,據她所說,小時候,她第一次在課本上看到這個尖尖的三角體,就一眼被迷住了,后來給女兒看了小紅書上的游客照,“她也很著魔”。
為了培養女兒,按照社交媒體上學來的育兒方式,她的女兒同時學七種課外項目——魔方、桌游、畫畫、手工、輪滑、羽毛球、游泳。
只不過,她沒錢,只能自己學,等學會了再親自教給女兒。比如魔方,她喜歡刷B站,在平臺上搜了六階魔方的教程,每天花半小時背誦公式,再練習半小時,一個月下來,她已經能把魔方在一分鐘之內還原。
“雞娃先雞自己。”孩子聽不懂魔方公式,她就用白話解釋,“實在聽不懂,再畫張圖”。
在經濟拮據的情況下,陪讀是縣城媽媽唯一的教育出路。另一位縣城母親張瑤瑤,她今年32歲,來自江西撫州宜黃縣,有一兒一女,這是她的寄托。但讀小學的兒子卻學不好英語。她沒有逃過大數據的監控,接收到社交媒體上的精準廣告之后,她給孩子充了幾百元的英語網課——這已經是她的全力,過去母親和孩子三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不超過3000元。
但兒子卻從來不聽,拿到手機第一反應是玩游戲。張瑤瑤把游戲鎖了,兒子又打開微信小程序玩游戲,直到她鎖住了微信,把兒子揪到座椅前,一個一個單詞教,一晚上過去,兒子還是記不住,“我自己都背下來了”。
相比之下,家境相對富裕的河北的縣城媽媽陳芳鹿,也沒能在這樣的焦慮中幸免。她的做法就更為“極端”,她幾乎無時不刻都在用行動“逃離縣城”。
她的兩個孩子從出生開始,每回身體不舒服,她都要跑到北京去,就算只是感冒,也會選擇兒研所,“不能耽誤了孩子”。她的小兒子經常過敏,陳芳鹿就在小紅書上搜到了一個北京的知名兒科大夫開的私立診所,“說是好多明星的孩子都去那兒”,診所里最普通的一個保健號都要500元,她并不介意,帶著兒子一趟一趟開車去100公里外的北京,后來養成習慣,小兒子所有的疫苗、體檢都在這里完成。
大女兒不到1歲時,她對標“外面的世界”,特意離開縣城,去附近張家口市里報了個總價快3萬的早教班,折合下來,一節課200多元。早上8點不到,夫妻倆抱上孩子,開車上高速,一個多小時抵達市區,孩子在車上已經快睡著了。
等到45分鐘的早教課過去,一家人又得等著下午的課程。“上完課總得在市里吃飯吧,吃飯后到商場里你不得逛一圈,基本一次消費加上高速費、油費,去一次就得花1000多塊錢。”
待到小兒子出生,高額的成本,讓她暫時斷了去市里上課的心思。最后,她給兒子在家附近報了一個縣城早教中心,6000塊錢,80節。
然而,一個縣城媽媽有多么渴望大城市的“精英式育兒”,就會對縣城產生多么大的排斥。這一點在陳芳鹿身上體現得極為明顯。她感受到一種落差,縣城早教班,“和市里完全不能比”。市里的早教中心純英文教學,有各種專業課,而縣城的早教中心“就像個托兒所”。
最終,觀念的沖突在一次親子活動中達到了頂峰。
那一次,縣城早教中心組織端午節包粽子活動,她給兒子穿搭了一下,背個小包,再塞個水壺和一些小零食。結果母子倆一進早教中心,“就好像你穿了個禮服,去參加了一個睡衣派對”。
她感到苦悶。對縣城來說,她越來越像一個外人了。

▲ 圖 / 《82年生的金智英》截圖
逃離的根源
對王小鈴自己來說,關于縣城的回憶,幾乎都是灰暗、晦澀的。
2019年,丈夫提出離婚,并將這一切推到了她的頭上。在她所在縣城里,這被解釋為是一個女人“活該”。在電話里,丈夫指責她:“如果你能掙錢,如果你會來事,你會處理婆媳關系,我們就不會離婚。”
他要求王小鈴帶著孩子凈身出戶。
搬走的那天,王小鈴看著自己買的家具、餐桌和鍋碗瓢盆,“都帶不走”,最后拎著幾包衣服沉默離去。她所在的縣城,不流行起訴,妥協往往是常態。她甚至承認,“說實話,我那時候覺得是自己的問題,就是不想離婚,還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聽了他的話,先搬走。”
搬走后,她從別人口中得知,丈夫在鄭州認識了一個“更能掙錢”的女人,當時王小鈴一個月才掙3500元,沒有了遮蓋真相的那層窗戶紙,他們的婚姻也真正走到了盡頭。
她和孩子在那座縣城又生活了3年,她們搬進了一個10平方米的出租房,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起初飯都得蹲著吃。房間太小,衛生間直對著床,下水道反臭的氣味始終縈繞在記憶里。
她嘗試過開童裝店,但“在縣城里沒有熟人,沒有老客戶”,幾個月,店鋪倒閉了,留下了一堆存貨和7萬外債。即便是她有本科學歷,過了英語六級和日語二級,但每一家公司都告訴她,不讓她把孩子帶到辦公室。有回加班,女兒一個人在家,她透過監控看到“孩子哭得不行”,哭著哭著直接昏睡過去。
正常的工作也沒法干,“后來我只能去做自由職業,去大街上跑業務”。王小鈴給人賣零食,在路邊發傳單,也挨家挨戶推銷過駕校,挨罵變成常有的事,跑三四條街,能看到一個好臉色都算幸運。
最窘迫的時候,她同時欠了5、6個借貸平臺的錢。每個月有1/4的時間在拆東墻補西墻,在一個該交房租的日子,她又被“寶媽刷單”的騙局騙了1000多元錢,身無分文,信用透支,走在路上,人都在搖晃,她說那是自己最崩潰的一刻,“一輩子也忘不掉”。
縣城的回憶對她來說,就是這些窘迫生活的堆疊。
好在,女兒陪著她。到了周末,她帶著女兒一起去發駕校名片,女兒比她更大膽,張口就問,“阿姨考駕照嗎?”晚上,她們一起擺攤,賣之前童裝店的存貨,也賣自制的酸梅湯,孩子主動要推車,邊走邊叫賣。
但由于逃離了痛苦的婚姻,她反而感覺到一種自由。她甚至覺得,只要擺脫縣城,就是擺脫了過去。
同樣希望擺脫過去的還有河北的陳芳鹿。
陳芳鹿有三個遺憾,分別是她錯過了天津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和一次去德國留學的機會,高考的失敗、猶豫的性格、大學的愛情,讓她最終又回到了縣城。開下這個母嬰店,也是為了向所有人“證明自己”——這種證明貫穿于她的記憶。從小她就明白,自己得練鋼琴,練得好,媽媽就高興。別人的暑假上躥下跳,她只能在窗戶底下沒日沒夜練琴。
她至今還留著小學時給媽媽寫的一封信,“媽媽,我沒考好,下次一定改”。31歲了,她再次拿起這封信,雙手還在微微發抖,那是一種無法面對父母失望的害怕。
與這兩位已經有“逃離行動”的縣城媽媽不同,江西的張瑤瑤,則或許能揭示另一群“雖有逃離之心、但已無逃離之力”的縣城媽媽的困境。
她出生在福建的一個山村,母親早逝,父親幾年后再娶,后媽又生下了兩個女孩,張瑤瑤成為了全家最多余的那一個。小時候,她去鄉里上小學,父親一周給她10元生活費,來回路費就要6元,剩下的錢只夠2頓飯。她不敢張口要,后媽冷漠,父親嗜賭,好不容易見到一回,看她的眼神從來都是不耐煩,“怎么又回來要錢了”。
15周歲,父親讓她不要再讀書。她去了福州投奔姑姑,偽造年齡當過服務員,在鞋廠、化妝品廠工作。20歲,她在工廠里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她一度覺得,在這個男人身上找到了過去缺失的“愛”。
現在想來,丈夫娶她只是為了“找個老婆”。
張瑤瑤總是喜歡提起“如果”。她說:“如果我能意識到,這場婚姻的一開始就是不尊重,我會直接把肚里的孩子引產;如果我的媽媽還在,20歲的年紀也許我還在上學;如果我懂一點人情世故,我就知道這個男人根本不可靠。”
但沒有如果。婚禮那天,因為籌備婚禮花了3萬塊錢,丈夫的臉色就沒有好過。在婚車從福建開往江西的路上,丈夫發現忘拿了娘家酒席上的幾條煙,當著婆家人的面,又對她破口大罵,“娶你真花錢”。
而這只是個開始。
婚后,失去了經濟來源的她,不得已用更多的妥協換取安全感,“孩子我一個人帶,家務我做,活也照干”。她的重心開始圍繞著丈夫和兩個兒女——種竹蓀、賣柑橘,抱著襁褓里的孩子在烈日下曬谷子。
隱忍和退讓總在發生。有一回玩耍時,大伯的孩子用鐮刀砍傷了她的女兒,在頭上砍出一條5厘米長、3厘米深的傷口。女兒在她的懷里哭到抽搐,婆婆只是嘟囔了一句,“我也不知道怎么會這樣”,轉頭就帶著大伯哥的孩子離開。
她只是沉默,抱著孩子上藥。
“這是我這輩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張瑤瑤又一次提起了如果,“如果再來一次,我會和他們拼命。”
再后來,孩子長大,為了陪他們上學,張瑤瑤又成了縣城全職媽媽。10年的時間里,因為生活不順,丈夫變得更加冷漠、敏感,兩人爭吵時,丈夫說,“如果不是你們三個,我現在一定不會這么倒霉”。
而張瑤瑤,就同時困在母親、妻子、縣城女人這三重身份中。

▲ 圖 / 《隱秘的角落》截圖
不是逃離的逃離
河南的王小鈴,決定帶著女兒逃離縣城。
3月初,她帶著孩子去了鄭州,前夫承諾給她每個月1500塊撫養費。此前,她已經在縣里找了一個大碼女裝網絡客服的工作,縣城的老板答應她,只要業績達標,這份工作她可以帶去市里。
但城市的生活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簡單。前夫就住在距離她們騎車十幾分鐘的地方,偶爾會過來看孩子,卻絕口不提撫養費的事。女兒上學的事也遙遙無期,按照鄭州當時的政策,王小鈴既沒有當地的房子,也沒交過社保,孩子無法在鄭州入學。
那段時間女兒本應該讀大班,王小鈴只能在鄭州打聽了一個幼小銜接班讓她過渡。它偷偷藏在老式居民樓里,一個月700元。沒有操場,沒有活動室,教室只有一個客廳那么大,全是課桌,擠滿了30來個孩子。他們和王小鈴的女兒一樣,都是外地孩子。
這樣的落差讓她無法接受,“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找前夫要錢,成了王小鈴在鄭州最重要的事。但前夫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少,王小鈴當面要,或是發微信,每次只能得到一句話,“再等等”。
王小鈴在對抗他的前夫,而對河北的陳芳鹿來說,她要反抗的,則是縣城傳統家庭里,難以動搖的觀念。
陳芳鹿總結自己的人生就是缺少了規劃和底氣,所以她早早為兩個孩子想好了出路。“我計劃給孩子送到天津,再不濟也要到張家口市里去。”她準備著,給孩子在天津買一套學區房。
這遭到了公公的強烈反對,“在哪兒念不是念,去了天津念書,又能考上個什么”。公公一家在縣城里做工程出身,陳芳鹿的丈夫當時沒有考上大學,選擇子承父業,照樣過得不錯。
但這在陳芳鹿看來,公公根本不替孩子的未來考慮,“他覺得我們這樣就夠了”。
她的消費觀念也在家里處處碰壁,女兒走路有些內八,她帶著孩子去了北京一家有名的足踝診所,花2600元買了一塊矯正足外翻的定制鞋墊,又去商場買了一雙名牌鞋。
當天,公公也跟著去了北京,在診所、商場替孩子付了錢,后來陳芳鹿才知道,公公向丈夫私下抱怨,“你孩子是啥孩子啊,非得去北京買東西去”。
兩個世界的沖突,在她懷二胎的時候達到了最高點。當時,她和老公有了去廊坊創業開火鍋店的念頭,還沒下定決心,公公直接沖到了她的娘家,指著陳芳鹿的母親說:“這些年,我兒子就聽你這個女兒的,這個家就是你女兒說了算!”爭吵之下,當時差點報警。
相比之下,江西的張瑤瑤的兩個孩子還年幼,她也沒有經濟來源,無法做到直接離去,甚至失去了爭辯的勇氣。
她只能在短視頻平臺上尋找生活的解藥。她關注了許多博主,一半是健身,一半是經典名著講解。有一回,她刷到一條短視頻,里面說,“婚姻我替你們試過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選錯了,往后余生每一步都是錯,你會嘗盡人間苦楚,取舍兩難”。
她覺得這句話仿佛在映照她的命運,“一步錯,步步錯”。在過去的10年里,她多次試圖掙脫,但這種掙扎就像在漩渦里,讓她越陷越深。
而哪怕“外面的世界”下沉到縣城里,但這份下沉的紅利,她也沒享受到。她做過淘寶電商,想賣竹蓀,結果軟件都不會裝,貨也賣不動。還有一次,縣里組織電商培訓,7天的培訓,她來得最早,走得最晚,結果那場培訓只是一場秀。她看到其他寶媽在朋友圈賣書包、短袖和內衣,她又動心了,對方宣稱一單給3-5元提成,結果那些文案她復制了一年,一單都沒有賣出去。直到最后,曾經的同學說要帶她賺錢,把她拉進一個寶媽群,賣美容產品,進了群她才知道,那是傳銷。
她今年已經32歲,初中沒畢業,至今沒有坐過動車、地鐵,就連坐長途車,她也害怕。某種程度上,她已經與社會脫節。
平復這些苦悶的方式,往往是打開一段30秒的短視頻——視頻能刷到她向往的生活。
確實也有看起來“逃離成功”的案例。
30出頭的高婷來自山東濰坊的一個縣城,她選擇的方式,是讓6歲的女兒成為童模。去年,因為手機內存不足,她把女兒的照片傳到了社交平臺上,“意外小爆了一下”。后來源源不斷有人聯系她拍攝,女兒第一次走出縣城,也第一次坐了地鐵、動車和飛機。
身處縣城的她有一個私心,她想讓女兒變得像大城市的孩子那樣,更從容、更大膽——就像她給女兒取的小名“大膽兒”。用高婷的話來說,自己小時候畏畏縮縮,不敢表達,她希望女兒一定要大膽、勇敢。女兒也定下了一個大膽的志愿:將來一定要考上北京大學。
但這樣的“成功逃離”,背后也有相應的代價。
學校里,女兒遭遇激烈的競爭。在這個山東的縣城,女兒一年級剛開學10天,班級就要求抽查《桃花源記》,盡管這是一篇初中文言文課文。幾乎是每天背誦,女兒終于把它磕磕絆絆背了下來,“但意思是一句都不懂”。
而為了讓女兒“多見世面”,她還先后給女兒報了早教、體能、英語、美術、游泳和童模班。但現在,一個令她頭疼的問題是,縣里培訓班的外教老師離職了,僅剩下一個口音較重的本地老師。
她果斷給女兒停了課,“千萬別把口音帶跑偏了”。

▲ 高婷的女兒在拍攝現場。圖 / 受訪者提供
逃離之后
在這個從下沉市場中爭奪流量的時代,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讓縣城媽媽們看到大數據展現出來的“外面的世界”,對她們來說真的好嗎?與此同時,社交媒體里呈現出的片面的世界,又能不能當做理想生活的范本?
對受谷愛凌教育啟發的王小鈴來說,她在這個問題上搖擺不定。
似乎從縣城逃到城市,日子也并沒有好轉多少。今年6月底,女兒馬上要面臨升學,結果前夫再也沒有出現,也不再回復微信。鄭州的花銷就像流水一樣,母女倆租房、吃喝,每個月得花去接近5000元。她突然醒悟,要不到撫養費,“那個地方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她只能被迫離開了鄭州。
現在她回到了娘家所在的地方,搬進了一個新的出租屋。四室一廳一衛,還附帶一個200平方米的閑置陽臺,租金2000元。她在陽臺種了韭菜、青菜、生菜、黃瓜、豆角、大蒜等十幾種蔬菜,之后還準備買個籠子,養幾只土雞。
某種意義上,如今有一個“她”生活在社交媒體中——她現實生活中幾乎沒有朋友,生活圈子也與網絡世界相關,清晨她會在陽臺上,圍著菜園子慢跑,女兒則會在客廳里逗貓。她習慣于把每天的生活制作成vlog,發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很多人說她灑脫,還有人羨慕她的生活。
但只有現實中的她知道,一些傷痛無法隱去。“其實我最大的愿望不是事業好,而是婚姻美滿”,這也成為她最大的遺憾。她的視頻事無巨細,卻刻意隱瞞了一件事,“說出來一定會被罵死”——在離婚后,丈夫依舊向她伸手借錢,她沒有存款,用網貸借給了他。
至于鏡子里那個關于谷愛凌的夢,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了。
與王小鈴一樣,陳芳鹿在自己所在的河北張家口涿鹿縣,也幾乎找不到什么朋友。她的朋友也是,幾乎都在社交媒體上認識,她們一起,在網上分享育兒、家庭以及屬于女人的未來。
自然,她也在上面分享自己開母嬰店的經歷。短短一年過去,她的母嬰店,就虧損了接近60萬。
“外面的世界”,同樣也困住了張瑤瑤和她的孩子。
“如果”,張瑤瑤最后提起了一次如果,“如果我自己夠聰明,我的婚姻就不會走到這一步。”
她不敢離婚,因為她看到,短視頻上的悲慘女人離婚后,往往凈身出戶。對此張瑤瑤并沒有咨詢律師,她只是用生活經驗下了一個判斷,“都是這樣的,都是這樣的”——大數據總會讓人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
等孩子再大一些,她知道自己會更無力。比如,現在的她,應付兒子的數學題已經非常困難,而與此同時,她還要應付其他的同齡人媽媽。前幾天,過去的鄰居給她打了一個電話,這位鄰居比張瑤瑤小一歲,崇尚“精英式育兒”,鄰居會跟她炫耀,說“又報了兩個補習班,周末兒子要學游泳和美術,家里還買了一個架子鼓”之類。這些時候,張瑤瑤只能用沉默回應。
以至于每次接到鄰居的電話,她第一反應是蓋上手機,“她真的讓我壓力很大,真的”。
33歲的她總覺得,作為縣城媽媽,自己早已過了那個重啟鍵。看了太多“獨立女人”的視頻,她迫切想在社交平臺上找到突破的答案,但她怎么也找不到——能在短視頻里找到的答案,能叫答案嗎?
問題還沒解決,但新的擔心的事又出現了。她的女兒膽小懦弱,在外不敢表達,有一回張瑤瑤去幼兒園接孩子,看到她在哭,問了她許久,孩子在外就是不吭聲。回了家,女兒才告訴她,老師今天發棒棒糖漏了她的。張瑤瑤很無奈,問女兒為什么不舉手?
“我不敢。”女兒說。
那一瞬間,她看到了曾經的自己。

▲ 從張瑤瑤的出租屋向下看,是她和幾戶人家的公用廚房。圖 / 受訪者提供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小鈴、陳芳鹿、張瑤瑤、高婷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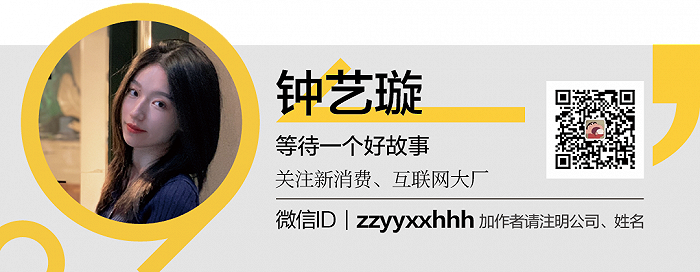
每人互動
你怎么看待這些縣城媽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