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實習記者 劉詩琦 記者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2003年,沈陽“鬼樓”里發(fā)現(xiàn)了一具赤身裸體的尸體,17歲少女黃姝慘遭奸殺并拋尸。十年后,一模一樣的案件再現(xiàn),可十年前的“兇手”早已離世。兩樁案件,讓五個孩子的故事逐漸浮出水面。黃姝的朋友、與她同病相憐的秦理用十年的漫長布局與等待,終于讓罪魁禍首暴露在警方的視野里,正義終得伸張。鄭執(zhí)在小說《生吞》中從兩個視角展開敘事,一是刑警馮國金的破案過程,一是五個孩子的青春回憶。在小說中,除了秦理與黃姝,其他孩子都曾經(jīng)做過錯事,也都是不敢正視面對、逃避現(xiàn)實的“膽小鬼”。
鄭執(zhí)是“新東北作家群”的成員之一,代表作包括《生吞》《仙癥》等,日前《生吞》改編為電視劇《膽小鬼》在網(wǎng)絡(luò)平臺熱播。《膽小鬼》的青春殘酷敘事引發(fā)不少共鳴,也因?qū)?/span>東北上世紀90年代生活場景的還原而廣受討論。
例如,社交平臺上有一些觀眾在討論該劇中學校食堂沒有凳子、大家站著吃飯的細節(jié)。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鄭執(zhí)稱,這還原了他記憶里真實的樣子。“從初中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六年我都是站著吃飯的。后來我才知道這不是南北差異,而是學校差異。”重點中學以學業(yè)為重,學校想要擠壓學生吃飯的時間,如果有座,學生就會一邊吃一邊聊天,但站著吃15分鐘就累了。在電視劇中,類似這樣對生活場景的還原比比皆是,鄭執(zhí)將其歸功于導演、美術(shù)和服化道老師。他稱,自己作為編劇,重點負責的是人物臺詞、性格、命運和劇情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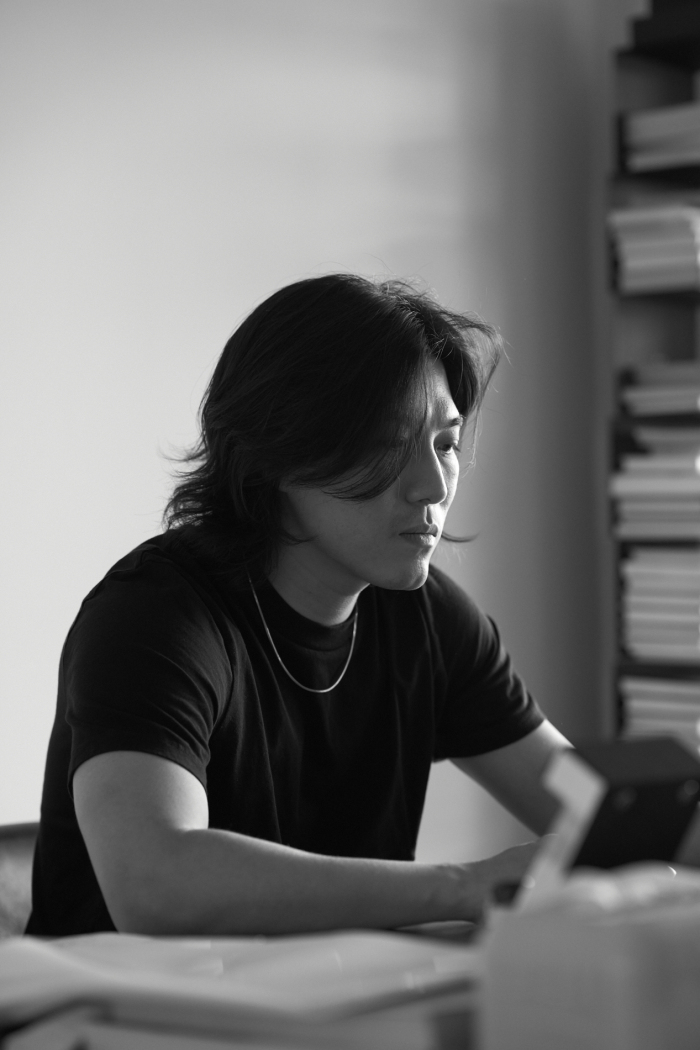
《膽小鬼》是包裹著懸疑外殼的青春敘事,之所以在時空上距離遙遠的東北故事能夠引發(fā)觀眾共鳴,用鄭執(zhí)的話來說,即是“離散、聚合、愛恨、背叛、信任、成長,青春那些最古老的命題始終沒變”。對于孩子們來說,成長的過程是靈魂的“黑白戰(zhàn)爭”,是認識到美好與未來并不等同。
在采訪中,鄭執(zhí)談到了同時作為《生吞》小說作者和《膽小鬼》編劇的體悟。在他看來,作家和編劇兩個工作表面看起來都是寫字,“其實完全是不同的行當”,小說作者“只需要對自己的個人表達和情感訴求負責”,當編劇有很多需要與他人合作的地方。此次擔任《膽小鬼》的編劇,也使他有機會彌補之前在小說中留下的遺憾。

01 談電視劇:一分為二、涇渭分明地創(chuàng)作
界面文化:在小說改編影視劇的過程,《生吞》改名為《膽小鬼》,《仙癥》改成《刺猬》,這兩處名字的變化有什么寓意嗎?
鄭執(zhí):倒沒有。《生吞》跟《仙癥》對小說而言是非常合適的名字,但改編成電影、電視劇,還不夠直白、不夠明確、不夠易于傳播。在改編過程中,敘述方式、故事主題跟小說多少有所不同,會選擇更為契合的名字。
我相信,在經(jīng)歷社會之前,所有青少年的本質(zhì)都更接近孩子,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曾經(jīng)有過一個秦理。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成人世界的壓迫,心里的秦理就慢慢死掉了。王頔(秦理的朋友)更接近我們?nèi)谌肷鐣蟮臉幼印N覄偪吹健赌懶」怼愤@個劇名的時候,第一反應就是,大家曾經(jīng)都是勇敢者,之后在現(xiàn)實中變成了膽小鬼。要是能這么理解的話,我們這個名字就沒白起。
界面文化:比起小說《生吞》,改編成影視劇的《膽小鬼》在加入了很多和友情相關(guān)的內(nèi)容,有人會覺得這部分內(nèi)容已經(jīng)超過了懸疑設(shè)定。你作為原著作者和編劇,會有這樣的感覺嗎?
鄭執(zhí):從題材上,《膽小鬼》的青春部分的確比小說比例更大,這也是我們改編過程中追求的方向。但是因為國內(nèi)市場一定要有一個作品定位,我們才把它定義為懸疑類型。其實劇中最大的懸疑是人物命運的走向。這是我自己寫劇、導演拍劇,甚至演員表演時的興奮點。大言不慚地講,這一點上是比較創(chuàng)新的。
這部劇對觀眾是有選擇性的。傳統(tǒng)上喜歡看國產(chǎn)懸疑劇的觀眾,對懸疑可能有一定的審美認知,會覺得需要多大的篇幅來寫案件、制造多大的懸疑等等。那些不是我的興奮點。起碼在基本文本上,我做出了我想要追求的獨特性,努力地、真誠地、沒有低估觀眾地給大家奉獻上一些新東西。播到今天這個集數(shù),觀眾的接受度明顯要比一開始高得多,就是因為進入了對人物命運的關(guān)注。
界面文化:《生吞》里反復出現(xiàn)的詩歌是狄蘭·托馬斯的《生日感懷》和《死亡也不能一統(tǒng)天下》,《膽小鬼》里反復出現(xiàn)的詩歌是艾米莉·狄金森的《假如我能使一顆心免于破碎》。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動?
鄭執(zhí):其實是一個基調(diào)問題。狄蘭·托馬斯那兩首詩是陰郁的,狄金森這首則充滿力量,干脆直接,具有感染力。如果有人小說和劇都看了,就可以明確感受到,劇里青春的部分比小說里陽光多了。當然這是一種藝術(shù)處理——劇情走向跟小說還是維持了比較高度的統(tǒng)一,也就是說其實這種“陽光”也是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它和最后的藝術(shù)效果和感染力其實形成了對比。所以狄金森的這首更為合適的。
這首詩我也沒有很早讀到,恰恰是在寫劇本的前一年無意中看到的。一開始劇本里還是那首《死亡也不能一統(tǒng)天下》,但是寫到后期,當整個調(diào)性開始變化,我覺得不對,不應該是那首詩,而應該是今天這一首。

鄭執(zhí)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7年
界面文化:你認為作家和編劇最大的區(qū)別是什么?你怎么看看待文字媒介和音畫媒介?
鄭執(zhí):這兩個表面看起來都是寫字,背后其實完全是不同的行當。言簡意賅地說:小說是一個人的單打獨斗,你只需要對自己的個人表達和情感訴求負責;劇本是一項合作的工作,需要兼容并包,兼聽則明,學會跟人交流、配合,以大局為重。
文字為媒介和以音畫為媒介是兩種藝術(shù)形式,各有各的魅力,彼此無法替換。因為兩個工種我都在做,所以要清楚地區(qū)分這兩個工種各自該使用怎樣的技術(shù)和創(chuàng)作邏輯。這是兩道門,每打開一道門就是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當然,你在一道門內(nèi)工作的時候,記得要把另一道門關(guān)上,不要讓不屬于這個門類的表達溜進來,要把自己一分為二來使用。
影視改編的這條路我走了四五年,是以非常警惕、自我警醒的態(tài)度在處理這兩個問題的。未來不確定還會不會寫劇本,但這四五年寫劇本擠占了很多寫小說的時間。所以,在《仙癥》以后,我可能暫時不會碰劇本的工作了。從創(chuàng)作層面來說,當我回來寫小說那天,我可能要階段性地把寫劇本的那扇門關(guān)上,涇渭分明地創(chuàng)作。

界面文化:編劇會對寫小說的工作產(chǎn)生影響嗎?會不會不自覺地去考慮小說的影視改編?
鄭執(zhí):現(xiàn)階段不會,曾經(jīng)我會。這是很現(xiàn)實的原因,因為早幾年我賺不到錢,動過一些小腦筋,覺得要寫點兒能賣版權(quán)、能賺錢的。所以在《生吞》以前,我寫過更貼近市場的東西。經(jīng)歷過那個階段,我有了更大的創(chuàng)作自由,堅持自我表達,寫了《生吞》和《仙癥》,反而被人看到了。我寫了自己想寫的東西,得到了別人的回應,又能養(yǎng)活自己,為什么還要再走那個誤入歧途的回頭路呢?
界面文化:在被更多人熟知后,你的寫作狀態(tài)和此前有什么不同?
鄭執(zhí):這兩年的狀態(tài)比以前好。對自己有要求的創(chuàng)作者,會希望自己保持更健康、更規(guī)律的創(chuàng)作習慣,目的都是能寫得久一點。我這兩年最大的改變是生活規(guī)律多了,早睡早起,鍛煉身體,今年還把酒給戒了。
02 談文學:讓被家庭困住的女性在小說里決絕走掉
界面文化:你的作品里常出現(xiàn)隱喻性的意象。《生吞》里的火炬是五個孩子友誼的象征,是黑暗中的光;《仙癥》里,吃掉己的保護神刺猬的奇人,似乎象征著對迷信與壓迫的反抗;《蒙地卡羅食人記》里的“我”變成了熊,才有出走的能力;《森中有林》中的三代人都像樹一樣,扎根在了沈陽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為什么會用這一類的隱喻意象?
鄭執(zhí):看到一些讀者和評論家的文章之后,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我沒有具體反思過這個創(chuàng)作邏輯,可能這是一種比較直白的隱喻方式。
并不是所有動物的出現(xiàn)都是隱喻,如《仙癥》里的刺猬是一個客觀事件,刺猬代表的是東北民間“五大仙”之一,是融入在東北底層家庭當中的、根深蒂固的生活邏輯。如《蒙地卡羅食人記》里熊的隱喻是對經(jīng)典作品的一種學習,這種處理方式在很多作品中都見過。至于把幾篇放在一起比較,看它們之間是否有關(guān)聯(lián),我不認為這里有一個客觀規(guī)律或是我在潛意識里做出了選擇。
界面文化:《仙癥》里有很多關(guān)于民間信仰的內(nèi)容,但態(tài)度往往是比較模糊曖昧的。比如在《他心通》里的“我”似乎在一開始相信民間信仰,最后卻產(chǎn)生了變化。
鄭執(zhí):我生活在這種環(huán)境里,大家都是工人階級,文化水平都在同一個區(qū)間。那種民俗是融入到他們的生活中的,是他們生活邏輯的一部分。故事一開始對這事兒態(tài)度曖昧,但最后結(jié)局是反諷的,比較接近我生活中對這種事和價值觀的態(tài)度。它影響到了你的生活,甚至影響了人物命運、整個故事的走向,但它并非決定性的因素,也不存在什么因果邏輯關(guān)系,只是你生活中一個縈繞不開的存在。

鄭執(zhí) 著
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0年
界面文化:《生吞》里的黃姝似乎是男性凝視下的“天使”形象,帶有臉譜化、符號化的特點。在王頔與馮雪嬌結(jié)婚后,王頔也開始正經(jīng)工作。好像兩個女性形象都讓“我”完成自我建構(gòu),用女性的犧牲完成男性的成長。你是如何看待這兩個女性形象的呢?
鄭執(zhí):這種評價曾經(jīng)引起過我的思考。不得不說我留下了遺憾,我本可以把女性形象寫得更好。我在29歲到30歲寫《生吞》時,私人情緒主導太重,那段時間表達有些自私,沒有把注意力分散給我筆下本應該更公平對待的人。
《生吞》刪除了一些內(nèi)容才出版,這是我自己的選擇,不怪旁人,但有點后悔。到劇里的時候,我變得更加自由平和,有了更大的空間,像天使一樣的女孩兒一定是存在的,黃姝就是這樣一個像天使一般的女孩兒。但是我要把天使的一面寫出來,不是像小說里那樣一筆帶過,用男性的視角去講述,而沒有真正去深挖她的故事。黃姝為什么會是這樣的一個狀態(tài),為什么她遇到了秦理就像人生遇到了光,為什么兩個人破碎之后,光就好像沒了,她在各種壓迫與殘害下走向了這樣一個結(jié)局。這樣就呈現(xiàn)了一個完整的人物,不管觀眾如何評價,我覺得自己完成了彌補遺憾的訴求。
創(chuàng)作劇本好像在和過去的自己在進行對話。用劇本的方式呈現(xiàn),給予我更大的空間和自由度,讓我去彌補和完善這個故事,而不是把講過的東西又講了一遍。這是我在這次劇本創(chuàng)作中最大的樂趣。
界面文化:在《生吞》和《仙癥》里,母親形象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邊緣化的、缺席的、有隔閡的,比如《蒙地卡羅食人記》中的母親拿著存折從家中消失。相較而言,父親的形象似乎更為主要和正面,帶有子輩為父輩發(fā)聲代言的意味。
鄭執(zhí):有人覺得這是我對母親的憎恨。恰恰不是,正是因為我生活中看到的女性長輩們,被所謂的家庭和母職的枷鎖困住。有時候完全是她們情非所愿,被困了一生,沒有走掉,最后內(nèi)心充滿了埋怨和悔恨。所以,我在很多作品里讓她們決絕地走掉,離開這灘渾水,這樣做當然要斬斷一些東西,這就是代價。我出于善意讓她們逃離那種生活,只是留下了一個所謂的爛攤子給父子。我不覺得父親形象是負責任的,這個留下的父親往往都是沉默寡言、陰郁、沒什么本事、跟孩子之間很難溝通的形象。
劇里面有一個母親的角色是豐滿的,就是王頔的母親,她更接近東北常見的一種母親形象。她操心這個家大小事兒,踏實可依賴,又比較碎嘴;有時又有一點獨斷專行,有一點兒像是母權(quán)社會。

界面文化:提到東北,似乎總是被他者化、奇觀化的,對這一地域的刻板印象從“共和國長子”、重工業(yè)基地到二人傳、趙本山、下崗潮,再到“土潮”、沈陽雞架等等,互聯(lián)網(wǎng)上很多有關(guān)東北的短視頻也在刻意迎合和復制這種“東北想象”,這些內(nèi)容似乎也反向加深了東北對自我的他者化。你是如何看待這種現(xiàn)象的呢?
鄭執(zhí):不僅是東北被他者化,在我眼里,你也被我他者化。作者不需要思考自己被他者化之后的反應,只要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進行真實誠懇的表達就好。我只是狹義地講,一個創(chuàng)作者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寫真正想寫的東西。比如我半輩子都和雪在一起,不可能為了規(guī)避他者化的問題,就不寫雪了,這不真實也不可能。
界面文化:以東北下崗潮為背景的作品,也能引發(fā)非東北讀者與并不熟悉這段歷史的讀者的共鳴。你覺得是什么原因?
鄭執(zhí):是對青春共同的認知。不管時代怎樣變,外部環(huán)境怎樣變,離散、聚合、愛恨、背叛、信任、成長,青春那些最古老的命題始終沒變。故事當中的古老命題,勾起了大家對自己人生過往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