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華商韜略
今年3月,農村農業部發布了一項數據:全國返鄉入鄉創業人數,累計達到1120萬人。
從高校到大型企業,從一線城市到三四五線城市,越來越多年輕人,正走向田間地頭、山林深處。

2021年8月,在武漢江夏區的一個村子,一輛“遙控坦克”開進了村里的玉米田。
這是一輛遙控巡檢機器人,通過攝像頭,田間的作物狀況被實時傳送到手機端,采集到的圖像,用來自動分析作物的長勢和病蟲害情況。
這樣的新鮮玩意,通過改裝,甚至可以在水稻田里進行巡檢。
將“遙控玩具”與農業相結合,是武漢工程大學的志愿者們想出來的“鬼點子”。
武漢工程大學的志愿者到農村去,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2019年3月,共青團宣布力爭組織超過1000萬人次大中專學生,參與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
為了響應“新青年下鄉”,武漢工程大學從師生中選拔了一批志愿者,組成了科技支農團。
這些志愿者的專業雖然看似與農業相隔甚遠,卻為農業帶來了更全面、更新穎的跨界解決方案。
通過大量走訪,實地采集土壤和水樣樣本,進行實驗室檢測和大數據分析,支農團的志愿者們專門開發出一款APP,實時上傳所有的農業相關數據,以幫助農戶和相關企業獲得更為全面的農業信息,建立有針對性的種植方案。
如今,江夏區的農戶們,已經開始根據這些相關數據,來決策化肥的施用亦或是農作物的種植。
比起利用暑假期間短期志愿“下鄉”的科技支農團,在廣東遂城鎮,石家敏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三年志愿者,對于遂城鎮分界小學的學生們來說,他是“無所不知”的“石頭哥哥”。
在石家敏看來,自己只不過做了很多的小事。
石家敏曾在學校中組織過一場趣味運動會,這種城市中很尋常的校園活動,卻是這間鄉村小學的第一次。這些信息閉塞的孩子們,還是第一次知道百米賽跑和跳遠的具體形式。
在中秋節時,石家敏還曾組織孩子們給父母寫信。當地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兒童,對于他們的父母來說,這是多年來第一次看到孩子寫的字、畫的畫。甚至有父母特意從學校要來石家敏的電話,親自表示感謝。
在農村,留守兒童現象只是眾多困難之一,許多地區的貧困,才是最大的痼疾。
廣東省汕頭市的梅徑村,曾因缺乏良好的產業,人均年收入低下,一度被人們稱之為“沒勁”村。
深圳大學畢業的鐘澤鈴是梅徑村扶村工作隊的一員。2021年,鐘澤鈴從實驗室走向田野,協助工作隊將四百箱蜜蜂落戶在梅徑村。
為幫助梅徑村的蜜蜂產業,鐘澤鈴需要時常早起,與養蜂人一起工作。在采蜜期,她跑遍了周圍的山路調研蜜源是否充足,如果恰逢陰雨天,還需要檢查蜜蜂的健康狀況。對于當地剛剛接觸蜜蜂產業的農民們,這些知識既難以快速掌握,又是必需的。
在工作隊的努力下,梅徑村的蜜蜂產業發展迅速,僅僅半年時間400箱蜜蜂就產出蜂蜜超過4000斤,有效提高了當地人的收入。
類似這樣的景象,在廣東農村接連上演。
根據相關數據顯示,今年廣東一省有2萬余人報名“志愿服務鄉村正興行動”,在8月份,4000名大學生被選拔成為志愿者。
放眼全國,自2019年共青團引發《關于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至今,已經有千萬余人次,參與到大中專學生志愿者暑假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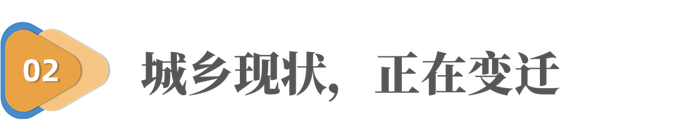
在知乎上,有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不考慮薪水尊嚴面子,你最想從事什么工作?
答案中,“回歸農村”竟然成為高頻詞匯,而排在“回歸農村”前的,僅有“老師”、“學生”。
這個答案的背后,有一個高度共識,年輕人正對城市壓力感到不滿。
在麥可思發布的《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中,本科畢業生選擇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從2015屆的26%下降至2019屆的20%。其中最夸張的當屬鄭州——每4個人去到北上廣深,就有5個人逃離北上廣深。
根據《北京人口藍皮書》顯示,自2015年以來,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持續呈現負增長。
在大城市里,學歷的逐年“貶值”,是重要原因之一。
正常來講,一座城市的人才結構,應該是金字塔式,學歷相對低的占絕大多數,學歷越高占比越少,這樣才最為合理。

但根據2019年的數據顯示,在北京2100多萬常住人口中,有近1100萬人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占比超過50%,其中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口超過35%,高學歷人口密集度全國第一。
高學歷人口密集度第二的位置屬于上海——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超過30%,其中本科及以上學歷占比18%。
和全國水平相比,這是絕對的高比例:全國受過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數,總共才2億多人,大約僅占中國14億人口的14%。
這樣的現狀,使得大城市內卷加劇,高學歷擠占相對低學歷人員的工作機會,既造成了教育和人才的雙重浪費,也使得大城市的年輕人口就業壓力越來越大。
在大城市內卷的另一面,則是農村逐漸“被拋棄”的現狀。
城市的虹吸效應加劇了農村人口、資金、技術等資源的流失,不少農村宅基地已經閑置,農業也變得逐漸邊緣化,而農村的人口結構,也越來越“老齡化”、“空心化”。
過去,以農村的環境和發展程度,難以提供太多需要高學歷、現代化技能的工作崗位,高學歷人口逃離農村不可避免。
然而,日益便捷的高速交通與互聯網,已縮短了城鄉的空間距離,也逐漸打破了城鄉間的信息壁壘。
同時,現代種植業、養殖業、農林產品加工業以及流通、電商的逐漸繁盛,也讓農村,反而出現更多的機遇,成為了就業新藍海。
而這些產業,又往往處在初級階段,需要引入精細化經營、科技賦能、貿易方式等改善。
這樣一來,具備有專業知識,有市場意識,并且接納新鮮事物能力高的年輕人,反倒成了農村新產業里的“對口人才”。
回到農村,更有國家政策層面作為號召。
在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中,將“三農”問題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誓要解決農業農村農民這一關乎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
2018年2月4日,國務院公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2019年3月,在共青團中央的組織下,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正式拉開大幕。
相關政策的下發,不僅向年輕人發出了回鄉、下鄉的號召,也讓回鄉創業的年輕人有了切實的福利。
廣東省為志愿服務鄉村振興行動提供9.7億資金,計劃用4年時間面向全國招募1萬名高校畢業生;成都則為返鄉就業創業大學生提供免費培訓,并為他們設立23個返鄉青年大學生就業創業服務站,專門打造了23個創業孵化空間;自2018年,浙江省為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大學畢業生提供每人每年1萬元補助,目前已補貼大學畢業生近2000人……
可以說,各個省市,要人給人,要錢給錢,正全力為返鄉創業的年輕人鋪平道路。
截至今年3月,根據農業農村部發布的數據:全國返鄉入鄉創業人數累計達到1120多萬,其中創辦項目80%以上是鄉村一二三產融合項目。
越來越多年輕人,已經真正融入到鄉村振興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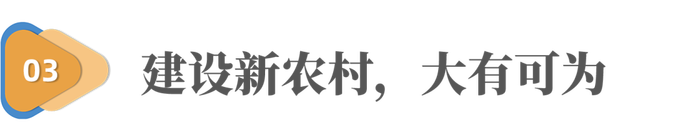
志愿者的到來,是一場鄉村與志愿者的互惠互利。
云南省元陽縣,擁有著舉世聞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哈尼梯田。身處哈尼梯田核心區的阿者科村,由于其獨特的村落景觀,成為第三批國家級傳統村落。這樣的地理優勢,理應產生優秀的旅游產業鏈。
然而由于村落空心化嚴重,傳統生產生活方式難以為繼,村內環境堪憂,旅游接待散漫無序,導致阿者科村一度成為典型的貧困村。
2018年1月,中山大學旅游學院組織團隊到此地進行實地調研,專門為阿者科村編制了《阿者科計劃》,并且每年派一名碩士研究生駐村,以推動計劃的執行。
通過科學的研究介入村莊社會治理,阿者科村本土資源的內在活力被逐漸激活,村民們被組織了起來,居住環境得到改善、傳統村落得到保護、旅游業也得到進一步拓展實現增收。
2019年3月,阿者科村實現了第一次旅游分紅,截至今年5月,阿者科村已經先后進行過6次分紅,共計分紅78.51萬元。再加上平時經營旅游業獲得的工資,阿者科村成功脫離貧困,成為“全球百強旅游減貧案例”。
與此同時,團隊中正在碩博連讀的駐村研究員小楊,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敲定出自己博士論文的框架。
這樣的案例,已經很難去說是誰在幫助誰,而誰有改變了誰。
東北林業大學林學院的教授鄒莉,對此有更深刻的認知。
曾經,很多人認為,一種科技手段只有徹底搞清機理后,才能付諸實踐。
鄒莉通過多年助農扶貧的技術指導后發現,只要確定一種成果能夠幫助實現穩產高產,并且對環境、作物等沒有害處,那么,在研究清楚應用場合、用量、環境條件等前提下,就可以大膽應用、跟進研究。
例如,種植在干旱地區的樟子松會出現衰退病,鄒莉的團隊發現,把血紅鉚釘菇打碎作為肥料,能較好地避免病害。雖然原理暫時還沒搞清楚,但這樣在“田間地頭”的科研項目,同樣使得鄒莉多次獲得科學進步獎。
當研究與實踐越來越契合,農村的潛力也就被發掘出來,新的機遇與藍海也一同出現。
在抖音上形象樸素的石嫣,已經做了多年的有機農場知識分享,鏡頭中看起來一副農民打扮的石嫣,其實有著豐富的學術背景: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后。
曾經的石嫣一度抵觸自己的專業,總認為自己未來的出路只能是去高校任教,可隨著對現代化農場的逐步深入了解,石嫣找到了創業的思路——CSA模式。
所謂CSA模式,簡單理解就是生態有機農場,但因為去除了中間商、產品品質提高、生產風險較小,因此CSA模式的收益更大。
如今,石嫣與團隊已經在北京郊區建成了260余畝的農場,為1500個家庭提供綠色蔬菜配送。同時,她還積極組織CSA聯盟,為全國各地的新農人提供技術支持與銷售平臺。
在石嫣的影響下,有位曾在北京某時尚媒體做化妝師的新農人學員,也放棄了大城市的繁華,回到安徽老家做起了生態蓮子的生意。
在石嫣剛創業時,國內的CSA農場屈指可數,可如今,CSA農場數量已經超過了300家。
與石嫣做法相似的,是一批有實踐經驗的大學畢業生,正逐漸成為規范化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的領頭人。和傳統農民相比,這群被稱為農創客的新農民,具備更強的溝通協調能力、組織指揮能力、創新創造能力,以及品牌意識、市場洞察力。
如今,全國農民合作社已經超220萬家,其中已有10.8萬家農民合作社開始打造品牌。這些合作社已經帶動全國近半農戶的收入提升,比如貴州省畢節市的南方馬鈴薯專業合作社,連續幾年來,已經引領成員收入增長超15倍。
擁有科技和現代經營理念賦能的新型農業合作社,已成為引領農戶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的重要力量。
農村的巨大發展潛力,不僅吸引了年輕創業者,也吸引了企業。2021年3月,華為“養豬”就成為熱議話題,除華為外的大量互聯網、房地產企業也都在進行著跨界“務農”。
很多企業開始協助培養鄉村人才。2021年,騰訊就與農業農村部簽署了“耕耘者”振興計劃戰略合作協議,出資5億元,用來合作培訓鄉村治理骨干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
在各互聯網大廠的技術支持下,“互聯網+現代農業”的新產業模式正在成型,人工智能、云計算、視頻技術、語音等技術,已經被引入農業的各個環節。
在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的湖羊智慧循環產業園中,羊的數量、飼料,羊舍內的濕度、溫度、氨氣、硫化氫氣體都可以進行實時監控,同時通過遙感技術可以進行精準調控。在利用這些手段以后,可以從以前每個人養10頭羊到如今每人能夠輕松管理3000頭羊。
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從來不會自動與農業結合。在各個時代,它都需要有人做先導者,有機制做保障。今天,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一批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承擔了這個角色。
而在城鄉一體化、城鄉人力資源雙向流動機制保障下,在政府、企業、大學的政策、資金、技術、人才支持下,農村正在走出落后與封閉。
在不遠的未來,農村將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詞,而是現代生活的另一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