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人文地理學學者大衛·哈維曾說:“地理太過重要,不能單靠地理學家來研究。”段義孚的學術生涯正印證了這一點。
他是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奠基性學者,在以科學主義為主流的地理學界,他強調不能只以客觀數據理解地理環境,更需引入人類感官與情感來探索空間的意義,并先后提出了“戀地情結”、“空間與地方”等重要術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當地時間8月10日,段義孚于美國逝世,享年92歲。

1930年,段義孚出生于天津,11歲后隨外交官父親(段茂瀾)出國,他曾在悉尼、馬尼拉和倫敦等地生活,并先后在牛津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學位。在西方,華裔社會人文學者往往難以進入學術主流,多以研究中國見長,學界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黑人研究黑人問題,婦女研究婦女問題,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問題)。”段義孚打破了這樣的陳見,投身學科貫通性問題,到20世紀的后20年,Yi-Fu Tuan的名字已經蜚聲于人文地理學界。
多年漂泊的經歷讓段義孚對土地情感問題保持強烈的興趣,不同國家的生活經驗也令他始終重視研究中的文化維度。在學生時期,段義孚最早研究的是自然地理中的沙漠環境、地形地貌,后來,他逐漸意識到了地理學的“重地輕人”特性——人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學科范式中被視作純粹理性的客體,情緒與感官體驗受到忽略,地理學忽視了人的存在、人與空間的關系。70年代,他在以科學實證為主流方法的地理學界,扛起了人文主義的旗幟。
在段義孚看來,人文主義地理學究其根本,探討的核心問題是“人之為人意味著什么”。他在早期著作《戀地情結》中這樣闡釋自己的觀點:“人作為一個個體,他認識世界,就是從調動各個感官去感知環境開始的。通過調動所有感官,人們才形成了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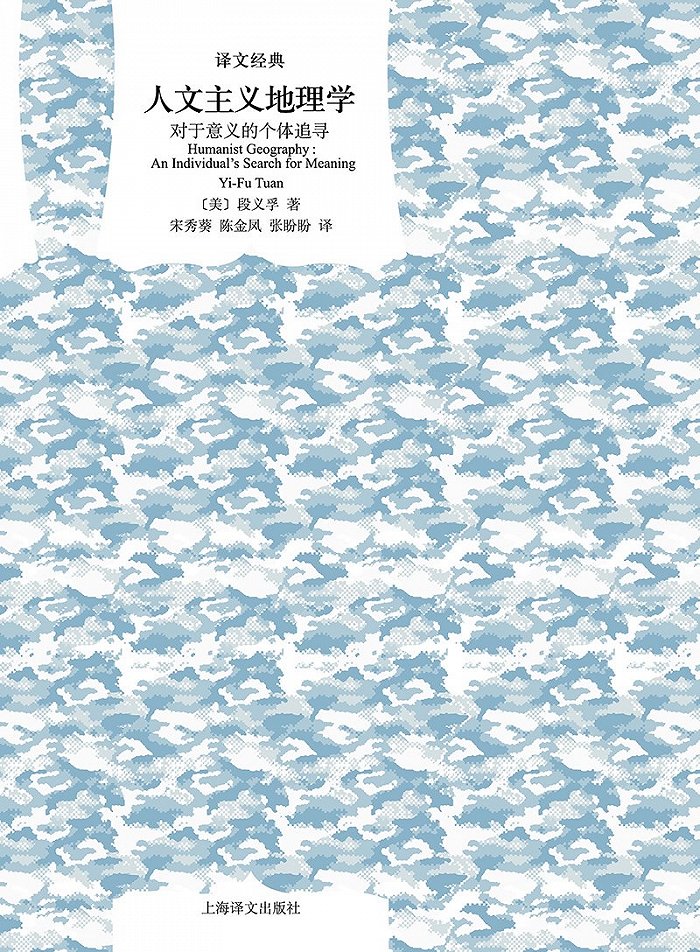
[美] 段義孚 著 宋秀葵 陳金鳳 張盼盼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0-5
除了對人文主義的強調,段義孚也推崇“浪漫的地理學”概念。在大多數人看來,“浪漫”與“地理學”似乎兩相矛盾,地理學更像腳踏實地、為人類生存而創的學科,他卻認為,注重細節的地理學需要與浪漫且先驗性的洞察力為伴——“無論是像威廉·華茲華斯所說的‘仿若那寄寓于落日燦爛余暉之中的、滲入萬物魂靈的虛無縹緲’,還是如愛因斯坦說的‘宇宙的音樂’。”
在他的最后一本學術著作《浪漫地理學:追尋崇高景觀》中,段義孚回溯了早期地理學探索的時代:探險家憑好奇心的驅動深入海洋、冰川與沙漠,挑戰精神與體力的極限;天文學家徹夜面對廣袤無垠的宇宙,觀察看似閃耀但在百萬年前就消失了的繁星。他還在書中從沙漠聯想到阿拉伯的勞倫斯,探討黑暗森林與康拉德小說、《海底兩萬里》與大海的關系,他也從人類對地球地理的探索延伸到對宇宙的好奇:“浪漫的地理學并不是過時之物。……實際上,任何超越了對地球的癡迷并開始欣賞天空、太陽和星星的文化——以及所有完成這一轉變的文明——都默認了我們的家園不僅僅是地球而是整個宇宙。事實上,對于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人來說,地理學也是宇宙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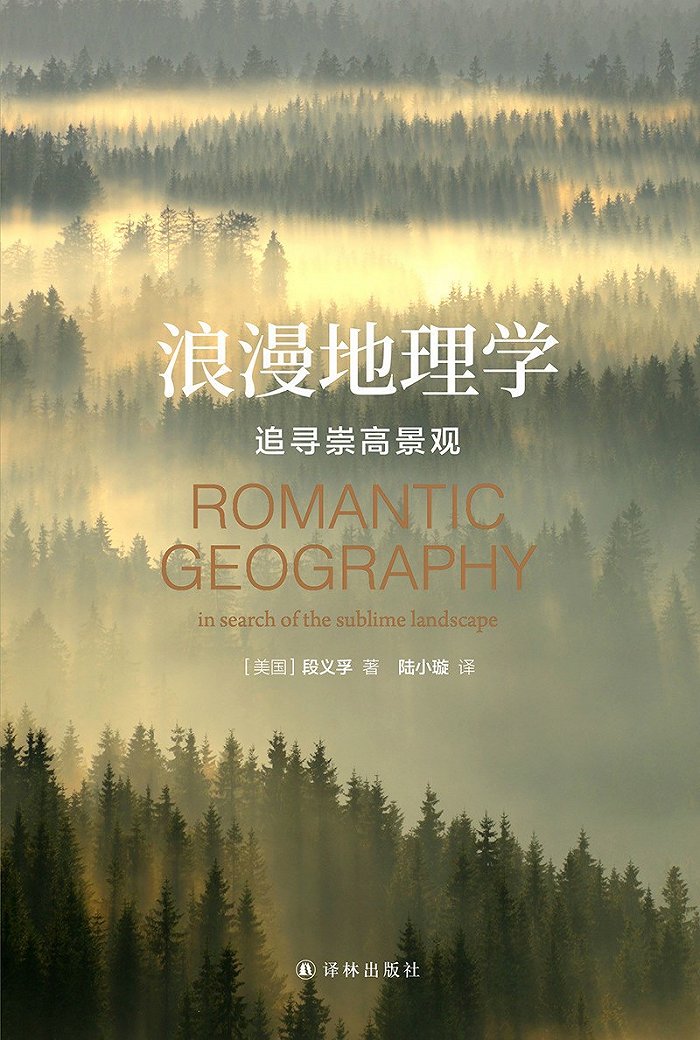
[美]段義孚 著 陸小璇 譯
譯林出版社 2021-7
2012年,段義孚獲得了瓦特林·路德國際地理學獎(Prix Vautrin Lud,此獎被認為是地理學的諾貝爾獎),評委將他比作地理學界中圣·埃克蘇佩里的“小王子”。這同他學術研究中豐沛的想象、娓娓道來的寫作風格有關,也與他在學界出名的溫柔謙遜、如孩童般的天真人格相關。
段義孚在自己最后的作品The Last Launch中寫到了一件小事:一天他在街上步行時,背后有小朋友的聲音響起:“你是學生嗎?你是學生嗎?”他好奇地轉身問那個孩子:“看過來,我看起來像學生嗎?”小朋友說,“是的,你有一個雙肩包。”他聽到后感到很開心,在書中寫:“我仍然有一個雙肩包,這意味著我仍然是一個向生活敞開的學生。”段義孚一生的學術探索,正是向人的生活敞開,書寫地理學的人情與浪漫。
參考文獻:
《浪漫地理學:追尋崇高景觀》[美]段義孚 著 陸小璇 譯 譯林出版社 2021-7
https://mp.weixin.qq.com/s/a3Yi2xVHvTr9tJfZ5l-VTA 段義孚:人文主義地理學之我見
https://mp.weixin.qq.com/s/7laVcAjyw_Hfc9AfehVG1A 讀書與自學 | 唐曉峰:還地理學一份人情
https://mp.weixin.qq.com/s/MshLnII1Zjk0WXfjGJF_Ng 段義孚的最后書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