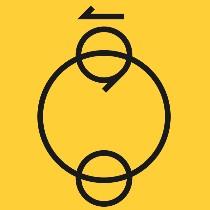文|每日人物社 徐晴
編輯|金匝
運營|月彌
豆瓣的“大學后悔學醫”小組,有2.3萬余人加入,規培是他們討論的高頻詞匯。他們自嘲為“醫療廢物”,在規培中付出瑣碎、重復、高強度的勞動,拿著微薄的薪水,也難以學到真正的技能。
退出
28歲的阿米娜一直在猶豫:要不要退出規培,從此不做醫生了?
這個想法就像偶然跳進她鞋子里的一顆小石子,每走一步,都會磨到腳。
第一次有這種想法是3年前,她讀完臨床醫學本科,去烏魯木齊一家醫院的婦產科規培。規培,即“住院醫師規范培訓制度”,這是所有想要從事臨床醫學的醫學生們的必經之路。畢業后,阿米娜沒有直接參加工作,而是以規培生的身份,在不同科室輪轉,接受系統的臨床訓練,時間是36個月。
原本,阿米娜有畢業后結婚的打算,但實在太忙了,規培生一天要在醫院工作十多個小時,沒有周末,還要值夜班,根本擠不出時間籌備婚禮。實在沒辦法,她想到醫院有個“獻血假”,獻了200ml之后,她獲得了7天寶貴的假期。
第二次是急性闌尾炎發作的時候,同事告訴她,得做個手術切除闌尾。她第一反應是看了一眼銀行卡余額,3000塊的規培工資,還完當月的房貸,只剩下幾百塊錢,最終,是爸爸給她出了手術費。那些天,阿米娜很內疚,“快30歲的人了,還得向父母伸手要錢”。
第三次動念頭,是她意外懷孕了,因為身體虛弱和長期疲憊,胚胎在11周時沒了心跳。她在科室暈倒,帶教老師給她做了流產手術。躺在病房里,她聽到老師們議論:一個規培生,結什么婚?生什么孩子?那一刻,她覺得無比委屈,眼淚流了下來。
和阿米娜一樣,在規培的3年里,學醫的年輕人會從事高強度的工作,拿著不匹配的收入,還需面對不對等的權力關系——退培的理由很多,但對阿米娜來說,又很難最終做出這個決定。因為一旦退培,就代表著一個醫學生要放棄過去長達5-8年的努力,再也做不了醫生,這是巨大的沉沒成本。
在廣西桂林,王凱就真走到了退培這一步。
畢業后,他直接進入當地一家醫院工作,成為住院醫師。3年后,醫院要求他去別的醫院參加規培,36個月的規培時間,他撐到第8個月,決定退培。回來后,大半年沒見的同事疑惑得很:“怎么退培了?”潛臺詞是:學醫的人都能堅持下來,你怎么沒有?他也不知該怎么解釋。
這8個月,王凱在委培醫院的多個科室輪轉,換來一個月2400元、共計19200元的規培薪資,這些錢在退培時全部還給了委培醫院。更深層的損失,是他的職業可能性:原醫院規定,拿到規培證書才可以考中級職稱,這是王凱成為主治醫師的必經之路。
但王凱不后悔。他今年30歲,未婚,房子買在縣城,是父母出的首付。規培的這段時間,他像掉進一個黑洞,社會時鐘徹底停滯,還不起房貸,靠家里的幫助才能維持生活。在親戚眼中,周圍30歲的人早已成家立業,他卻跟沒畢業的學生差不多。
他開始害怕過年,害怕親戚們聚在一起吃飯,討論誰的兒子在南寧買了房,誰的女兒年入數十萬,大家的眼光投向他,他的臉會難以控制地微微發燙,想找個借口逃離,又害怕被看出來,戰戰兢兢地吃完這頓飯。辦完退培手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輕松,走出醫院,覺得外面的天好像都更藍了一些。
退出規培的年輕人不是孤例。豆瓣的“大學后悔學醫”小組,有2.3萬余人加入,規培是他們討論的高頻詞匯。他們自嘲為“醫療廢物”,像阿米娜和王凱一樣,他們在規培中付出瑣碎、重復、高強度的勞動,拿著微薄的薪水,也難以學到真正的技能。
經歷規培之后,他們中有些人,“失去了對醫學的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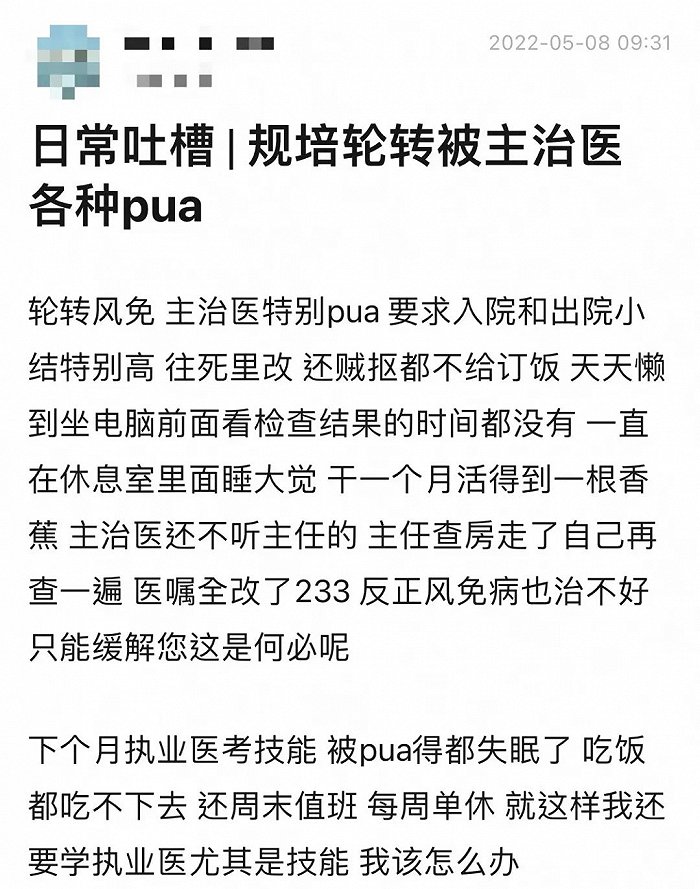
圖 / 大學后悔學醫小組
螞蟻和陀螺
走上學醫這條路,和阿米娜的經歷有關。
高中時,爺爺得了胃癌,當時她們一家人還生活在小縣城,醫療水平有限,每次做手術和復查,都要到烏魯木齊的醫院掛號、排隊,一通折騰,就此,阿米娜體會到一個家庭看病的難處,也認可了醫生這個職業的價值。
臨近畢業時,阿米娜也設想過:通過規培,她能掌握對應科室基礎病和多發病的診療技巧,從學生成長為獨當一面的臨床醫生,但親身經歷后才發現,“并不是這么回事”。
規培的大部分時間里,她做的是一些和診療技巧無關的工作:查新出來的化驗單、主任查房時做匯報、補充醫囑、給病人開新的檢查、與家屬談話簽署手術同意書、做術前準備、交代患者今天的治療……
她覺得自己像一只螞蟻,如果誰開了上帝視角,準能看到她在醫院里來回奔跑的軌跡。這些軌跡太過瑣碎,又十分相似,一天下來,她甚至不記得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規培開始后,柳心也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只陀螺。
他的生活里只剩下一個字:轉。在不同的科室里輪轉,在學術研究和醫院工作之間打轉,在一個又一個考試中輾轉。“轉”成了一個常用詞,走在醫院里跟同學打個照面,“你在哪兒轉呢?”就像北京人問“您吃了嗎”一樣自然。
科室幾乎每天都有手術,他的任務是幫忙扶住工具或是清理雜物。有一次,他早上8點進手術室,第二天凌晨4點才出來。那是一臺涉及多個科室的大手術,幾個主治醫師“你方唱罷我登場”,他作為助手,全程沒怎么休息,走出手術室的時候,他發覺腿全麻了,差點摔跪在地上。
作為一名專碩研究生,他甚至要轉得更快一些,并不富裕的時間,還要擠出來一些留給科研。醫院的下班時間是柳心的研究開始的時間,預約好實驗室,等一個有用的數據,通常要到凌晨。等走出實驗室,天黑透了,燈都熄了,柳心披著夜色回宿舍,簡單洗漱之后睡下,幾個小時后,再開始第二天的“轉”。
醫院也是一個小社會,時間久了,不是真正醫生的規培生,發現了自己在這個小社會中所處的層級:科室里過節發的購物券,沒有規培生的份;醫生們人手一個免費用的儲物柜,規培生得交100塊押金;醫用電梯不給規培生用,電梯阿姨只認本院的住院醫生;晚上值夜班,有病人呼叫醫生,護士先把規培生喊起來,規培生解決不了,再去喊主治醫生;阿米娜所在的醫院,甚至不允許規培生在值班室睡覺,有幾次她太累了,只能穿著手術衣在婦產科的產床上打盹。
幾乎每個規培生都曾有過幫帶教老師取快遞、外賣、跑腿、值夜班的經歷。阿米娜的帶教老師經常塞給她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自家親戚需要的各種藥品名,讓她去買藥的窗口排隊,一排就是半小時。疫情期間,一些醫院的規培生們也會被當作醫生,優先抽調出去做核酸檢測志愿者。
為了盈利,醫院會考核“翻床率”,在更少的時間里接納更多的病人,這些壓力落在了規培生頭上,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規培的于朦朧,常常要去勸說病人提前出院。時間久了,他有一個疑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工作?看起來像醫生,又不像醫生,準確來說,是一個服務員。

圖 / 《善良醫生》劇照
錯位
除去疲憊,規培生常常用來自嘲的還有收入:干著服務員的工作,拿著不如服務員的薪水。
阿米娜有同感。她所在的醫院,一位正式醫生的工資是6000元左右,作為規培生的她,工資只有他們的一半,3000元。
參加規培的第三年,阿米娜第二次懷孕,孩子出生,壓力撲面而來。丈夫在事業單位工作,每個月薪水5000元,兩人的收入得用來還貸,負擔孩子的各類花銷,以及一家三口的衣食住行,勉強夠用,可一旦孩子生病,又得向父母借錢。阿米娜開始學著省錢,甚至在1688上給孩子買衣服。
王凱是在工作三年之后才開始規培的。之前他在桂林的醫院工作,薪水有7000元左右,除去房貸和日常花銷,還能有盈余,賬戶余額每個月都是正增長。規培之后,收入降了三分之二,要靠動用存款才能生活。
規培生張森在一個東部二線城市的三甲醫院,每個月的補貼更少,只有500元,加上研究生補助,一共1100元。他在醫院附近租的房子,租金就超過了1000元,幾乎每個月都要向父母申請支援。
他身邊還有不少家境普通的同學,租不起房,只能住在醫院安排的8人間宿舍。規培的醫院有多個院區,相互之間隔了三十多公里,到另一個院區的科室輪轉時,想要準時上班,乘公交、地鐵是來不及的,只能每天早上6點起來,湊四個人后拼車到醫院,時間長了,大家互相調侃,“貸款來上班”。
規培生收入過低是共識。2020年,丁香園曾對3020名規培醫生進行過一次調查,發現近三成規培醫生(27.5%)表示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其中8%的人表示規培期間“沒有收入”,每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上的占32.3%。
國內自2013年建立起規培制度,就規定了中央財政資金的標準為3萬元/人·年,其余要靠不同省份自己來補助,以及各個醫院不同科室的獎金補充。一些偏遠地區的省份,補助只有0.33萬元,平均到每個月,只有275元。在北京,于朦朧一個月可以拿到共計9000多元的薪資,但在桂林,王凱只能拿到2400元。
即便都是一線城市,補貼也不在一個量級。幾天前,柳心的科室來了一位上海的師姐,剛來就問大家怎么報稅。柳心懵了,報稅?報什么稅?這個詞好像離自己很遙遠。他寬慰師姐,放心,你來了這里就不用報稅了,錢太少,不需要報。
工作之前,醫學生們對這個職業有著共同的想象:穩定、體面、光鮮,工資豐厚,社會地位也高。但現實是,在經歷長達5-8年的學習之后,至少在規培的3年里,他們的收入與教育成本、工作付出常常不成正比。
王凱常常感覺到,收入的尷尬,最直接的是帶來了身份的錯位:已到而立之年的自己,好像既不是學生,也不是醫生。規培之前,他跟關系最好的幾個朋友去了泰國,大家騎摩托車在海邊兜風,風迎面吹來,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有光明的未來。但現在,有的朋友在醫保局工作,有的做建筑工程賺到了第一桶金,還有的組建了家庭,生了小孩,過上安穩的生活,只有他,還得靠父母撿起他丟下的接力棒,替他還房貸。他難以融入朋友們的聊天,大家談起工作、收入、家庭,他能做的只有沉默。
豆豆也對這種錯位感同身受。參加規培這一年,她的社會年齡是25歲,別人對她的期待也是一個成年人,她需要參與社會生活,朋友結婚了要給份子錢,父母生日也該送禮物,但事實上,她的經濟水平還停留在17歲,這些看似理所應當的事情,她根本負擔不起。
“朋友計劃一起去旅游,你拒了,因為沒錢;想換個電腦,只能憋著,因為沒錢;連日常聚餐都不敢去多了,本來就少的補貼,吃兩次沒了,剩下的日子還要活呢,更別說買房、結婚這種大消費。”這份窮,不只是作用于生活,更造成一種人生遺憾:“遺憾在這二十多歲的青春里,能自由支配的時間和金錢是那么的匱乏,能做出的選擇是那么的有限。”

圖 / 《On Call 36小時》
變形
拋開工作強度和微薄收入,阿米娜最在意的,是規培的三年里,沒有收獲多少真的技能。
這三年,醫院幾乎所有的大手術,都由外地來的援疆醫生做。在手術臺上,援疆醫生主刀,阿米娜的帶教老師是第一助手,站在主刀左邊,幫忙縫合傷口,阿米娜是第二助手,站在主刀右面,幫忙扶器械,兩個人面面相覷。別說重大手術,連腹腔鏡這樣的昂貴器械,也是不允許身為規培生的阿米娜使用的。
今年夏天,阿米娜去找工作,一家醫院的主任上來就問,會不會做手術?會不會單獨做人流?剖宮產呢?阿米娜小聲回答,沒有試過。主任意味深長地看了她一眼,讓她把簡歷交給人事處,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更多的帶教老師,只會讓規培生們幫忙縫一下針、打一個結,做最簡單的操作。于朦朧有一次鼓起勇氣,說自己想嘗試深度傷口的縫合,帶教老師皺起了眉頭:“這個出血以后就不好弄了,也沒法跟家屬溝通。”——帶教老師也害怕醫鬧。
規培即將結束,于朦朧心里有一些“不舍”,他覺得自己“有些東西還沒有完全掌握”,唯獨病歷,寫得可熟練了,“但從能力來說的話,其實我沒有完全的把握勝任醫生這個職業,回去(原單位)以后,還得有老大夫來告訴我應該怎么做”。
規培生學不到真正的技能,受傷害最大的還是病人。帶教老師會讓張森給病人開藥,因為剛上手,用量上他常常把握不好。原本以為,帶教老師或是上級大夫會檢查一遍藥方再交給病人,但實際上,他發現沒有這個流程,有時候,他自己都會覺得后怕——開錯藥了怎么辦?他甚至覺得,糟糕的規培經歷,容易把規培生變成最討厭的那一類醫生,再去繼續壓榨下一屆的規培生。
從2013年《關于建立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的指導意見》頒布至今,9年時間里,我國公布的三批規培基地,數量超過了1000個,一些沒有規培資質的醫院也在其中渾水摸魚,開展“規培”。
今年年初,小敏來到在四川某個縣城的一家三乙醫院面試護士崗位,負責人讓她先在醫院“規培”一年。小敏和許多“規培生”一起干著護士的工作,一個月的薪資是1200元,醫院里的正職護士們,每天在科室里刷短視頻,薪水是“規培生”的三倍。幾個月之后她才知道,在這里,根本拿不到國家承認的規培結業證書,也不一定能留下來工作。
一些醫學生,因為規培的變形而離開這個行業。
阿米娜這一屆,一共有6個規培生,有兩個接受不了工作強度,心理壓力大,最終退培。在疲憊又難挨的日子里,幾乎每個規培生的手機里都有個日歷,用來倒數計時:距離規培結束還有XXX天。至于阿米娜本人,用了“解脫”這個詞形容規培結束的那一天,她當時幾乎是逃跑一般離開了醫院,連水杯這樣的日用品都沒拿回來,“再也不想看到那些東西了”。
一天,一位朋友跟阿米娜聊天,說自己在法院做書記員,早上10點上班,下午6:30下班,中午休息兩小時,食堂免費,周末雙休,一年有30天年假,每個月薪水4000多元。阿米娜默默地想:“如果法院還招書記員,我一定會去。”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