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期主持人 | 林子人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作為一場對千萬學子和他們的家庭未來命運有重要影響的考試,高考可以說是吸引全民注意力的年度焦點事件,高考期間,相關話題在社交網絡上層出不窮。比如高考第一日,語文考試作文題又不出所料地引起廣泛討論。眾多離高考其實已經很遙遠的成年人都在躍躍欲試般分析如何破題、立論,而感嘆“幸好自己已經畢業不然大學都沒得上”的人也不在少數。
這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現象:翻翻社交網絡上的高考話題,許多參與者其實都不是考生,都畢業那么久了,為什么我們還是熱衷于討論高考?每次看到別人以過來人的身份給考生分享高考心得、人生經驗,我都會忍不住想說這些話的人以及正在考試的孩子分別是什么感受。
01 我們的高考記憶
潘文捷:高考前夜恰逢鄰居喪事,那位鄰居原本事業上德高望重,業余愛好游泳,六月份在海島游玩時溺水去世,他家也失去了頂梁柱。于是我三天里每天伴著嗩吶和哭聲復習入眠,清晨去往考場時也能看到這家人疲憊的樣子。我想象過很多次高考會什么樣,但這是始料未及也終身難忘的。這件事時不時浮現在我的腦海,讓我想起人生無常,同時也盡量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要面對的難題。
葉青:我最深刻的高考記憶跟考試本身倒是無關。因為鎮上沒有考點,我們得去市里參考,學校統一替我們訂賓館。我去得遲,本來只能和同年級的陌生同學住一間,好在一位深知我社恐屬性的同班男同學居然主動跟我換房間,讓我免受兩日尷尬之苦,自在地備考,可以說能考上大學多虧了他。


尹清露:我來提供一點物種多樣性吧。我們高中是外國語學校,有保送名額不用高考的那種,最后出保送名單的時候我剛好掉出圈外,我媽沒轍,操心勞力地讓我轉學去了當地的A校準備高考,據說能提不少分兒。轉學后的第三天中午,我正在和新同學吃麻辣燙,突然接到班主任電話說某某同學要去德國留學,放棄保送資格啦,你進圈啦!我就這樣稀里糊涂地打車回到母校(當時身上還穿著A校校服),那名慷慨地把名額讓給我的女生拍拍我肩膀說:“尹清露,你可得謝謝我哈,”說完就走了。
我到現在也不懂這件事預示著什么,我到底是逃過一劫,還是錯失了高考這件人生大事?我只知道上帝的確會拋骰子,而那些愛你的人(比如我媽)和無意中影響了你的人(比如那名女生)就是這顆骰子的不同面向。
02 文字長期與大多數人生命相伴,所以我們喜歡討論高考作文而非數學題
潘文捷:大家愛聊高考作文除了因為作文分數最高,還因為文科是文字形式看起來簡單易懂,甭管內行外行都可以插嘴說一兩句。時常在逛公園的時候聽到大爺在侃如何評價女皇武則天,或者制定什么政策可以拿捏美國,卻很少聽到別人討論量子力學或者人體下肢肌群。文科學好學對不走上“逆練”的道路其實并不簡單,但它就是看起來人畜無害,沒門檻接地氣,人人都有指點一二的底氣,如果要聊數學最后一道大題的第三小問如何解答,是不是就有點兒炫學的意味了。
姜妍:高考第一天的時候在朋友圈看到阿子(胡續冬的太太)說,往年這一天總會有媒體打電話過來找胡子,問他愿不愿意寫一寫當年的高考作文。確實如此,以前在報社工作,每年高考語文題一出來,就能看到文娛時評的編輯在忙碌,到處約人寫作文。我覺得是不是可以從文捷的觀點反向思維,恰恰因為語文或者說說文字書寫是會長期與大多數人生命相伴的原因,所以我們更熱衷于討論作文,而不是一道數學題?假如真的在媒體上討論高考數學試卷的最后一道大題的出題和解題思路,會有多少讀者要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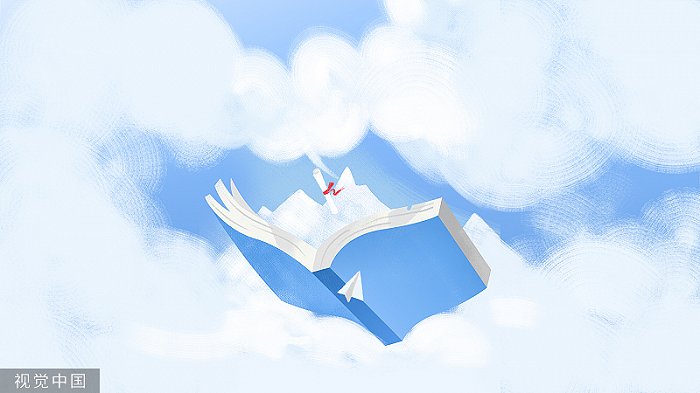
高考作文好和文筆好肯定沒有直接掛鉤關系,事實上在我們一路受到的教育歷程,也是一路被規訓的過程,可能越早進入到體系當中,就越早要接受這種規訓。我有一個朋友的小孩子沒有上過幼兒園,直接上小學的時候,你會發現小朋友很多造句寫得非常妙,但是在老師那里是拿不到分的。比如用“一邊……一邊……”造句,小朋友說“奶牛一邊是黑的一邊是白的”,被否掉以后,小朋友說“我一邊吃豆子一邊放屁”,當然還是通不過,小朋友就很疑惑,不明白自己錯在哪里。隨著年紀慢慢長大,小朋友早晚有一天會學會老師在課堂上教授的高考作文寫作技巧,但也希望他心里還能存有一些兒時的天真童趣。
葉青:語文的閱讀理解和作文是我永遠的痛。閱讀理解為什么會有標準答案,我真的不理解,語文老師上課的時候不是常說“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么,為什么我的哈姆雷特就是錯的呢……作文也同理,題干雖然都寫著“談談你的理解”,但這是個陷阱,但作為一名常年跑題者,我知道這句話的意思是“談談我們預設好的幾種理解中的一種”,你得揣測出題人的意圖,這抹殺了寫作中尤為重要的一點:真誠。盡管詞藻再優美、格式再工整,不誠實的文字除了折磨寫作者,拿到高分外,還有什么意義嗎?
03 議論文考的是邏輯說理能力,但作文教育一直教的是如何炫耀“知識”
徐魯青:高中老師曾分享自己高考閱卷心得,那神態宛如傳授驚天秘籍:“看了幾千份卷子,我發現高考作文高分很重要的一點,”他環顧四周,頓了頓,“字要寫得好看。”這就好比考上公務員的秘訣是身高165,單位升上副主任的關鍵是乒乓球打得好(以上兩個例子都是我媽以前勉勵我用的)。一個題外話,中國人似乎對字寫得好不好有巨大執念,一手好字不單說明是“讀過書的”,還能推出做人不會太差,于是十多個暑假里我總是被要求抱著字帖練個不停。某種意義上我覺得高考作文和這些事都很相似,你知道它想考什么,你不得不努力交出它想要的東西,但你也心知肚明,這套標準并沒有太多道理可言。
我印象里高中大多數作文都是議論文,議論文的意義應該是培養學生的邏輯說理能力,但我的作文教育卻一直在教我們如何炫耀“學識”。老師總是給我們發一大堆材料書,里面集齊了名人名言和人物故事,還會叮囑我們少引用愛迪生或者林清玄,多找找小眾一點的名人,比如小澤征爾這些聽上去很高級的。直到大學寫論文時我還有很多基礎問題沒解決,比如引用論證到底能多大程度增強論點的說服力,比如某處地方是否有必要引用理論,為什么用這個而不是那個,很遺憾高中作文只教了如何騙閱卷老師我讀過很多書。
尹清露:高考作文和文筆的關系在我心中一直是玄學。學生的寫作能力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要在極短時間內、針對特定題目不跑題且結構清晰地撰寫800字,文筆到底能占多大比重呢?似乎考察更多的是臨場反應力、素材遷移能力,還有揣測出題人意圖的能力,而不是(至少不僅僅是)對于題目本身的理解,這讓高考作文成為很多人的噩夢,想起那些快要交卷但還沒湊夠字數的恐懼,發誓這輩子不再寫任何文章。相比之下,在考場外的網友好像反而擁有更多自由空間,去對題目做出有意義的闡釋。
另外就是魯青說的,高中作文不太教邏輯說理,也不強調信息來源的嚴謹性等問題,這挺可惜的,我曾經看到過某本國際高中寫英語作文的教材,他們就會很注重“信息來源-整合-形成自己的論據”的閉環結構,而我到了研究生階段才對這一點產生足夠的意識。我覺得這種能力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發表觀點也很有幫助,可能我們就是因為缺乏相關的教育,以至于許多交流都變成了無謂的扯皮和罵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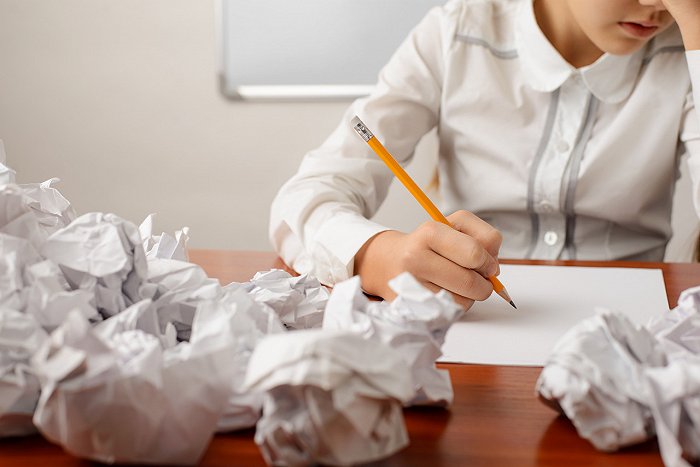
林子人:除了高考作文題以外,我還注意到有歷史博主把高考歷史全國一卷的題目拿出來討論,感嘆說歷史專業的學生恐怕都拿不準選擇題的正確答案。這是因為,你對歷史的了解一旦超過高中教科書的內容,就會發現很多以前你覺得“一錘定音”的結論其實大有商榷空間。正如魯青和清露所說的,等上了大學,真的需要就一個研究課題寫出從自己的研究觀點出發的,邏輯清晰的論述時,才發現高考語文作文的那種“解題”方法作用很有限。
我想這大概是我們畢業那么久依然熱衷于討論高考作文的原因。如果說發表觀點的成年人們真的是出于對后輩的關懷而非蹭熱點或自我夸耀,我相信那背后的動機是一種真誠的擔憂和提醒:要成為一個成熟明理的成年人,我們都需要不斷提升和精進自己。這不止是指不斷積累知識——如果徒有知識卻無分辨和判斷能力,那就和兩腳書櫥無異——更重要的是學習如何講理。我們要考慮任何重要問題的許多不同方面,均衡地尋找各種不同的觀點。我們要努力地拓展自己的知識深度和廣度,讓我們在表達觀點的時候都能有理有據,即使面對質疑也不至于心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