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筷玩思維 趙娜
在黃燜雞米飯、小龍蝦蓋飯之后,料理包對于餐飲業的侵入已經很徹底了,以臺灣鹵肉飯這個單品來說,現今市面上的鹵肉飯門店、鹵肉飯連鎖品牌大多都采用了料理包模式。有第三方指出,目前那些在放加盟的簡餐、快餐有99%以上都是料理包模式。
且不說料理包在C端消費者的大競爭局面和不可持續度(大多是嘗鮮消費,復購極低),單從覆蓋率和穩健增長的綜合角度看,料理包在B端餐飲業的盤子還是在持續增長的。
我們還注意到料理包在餐飲業的尷尬局面:正經餐飲人不屑于用,餐飲小白則用得很普遍,這就讓料理包產品在餐飲端形成了一種消費隔離。
在筷玩思維看來,這種消費隔離的局面,或許是時候被打通了。

料理包產業的分裂:消費C端半死不活、餐飲B端瘋狂發展
由于資本的長期看好,料理包類產品近些年在C端可謂鋪天蓋地,從一線到三四線城市,超市貨架、料理包類專門店、各類小程序電商等正涌現數萬到數幾十萬款(同質化的)料包類產品,可見大競爭是料理包在C端的一個大局面,然而現實卻很骨感,即使資本瘋狂押注,但目前依然沒有在賽道內跑出真正的大玩家。
剛需未起來,大競爭卻先行了,這使得料理包在C端半死不活、前途不定。
而在B端,料理包由來已久,在歐美市場,食品工業化(料理包的原型和土壤)其實就是工業化的衍生產物,從相關價值來看,食品工業化的出現可以解放女性在廚房的時間、降低食品類支出,這使得家庭的資金可以花到其它方面、促進新消費產品,將女性家庭主婦的身份轉為資本主義的新工人。
與此同時,工業化加快了食品的效率、大大縮短了工人在用餐時間上的投入,這些種種布局都偏向了資本主義——人的時間的工業化——把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工業化的機器,以實現對人的機器化管理。
中國餐飲業對于料理包產品的研發、投入及大眾層面的應用晚了歐美近百來年的時間,當代中餐料理包的作用在于讓非餐飲人進入餐飲業以及讓品牌方快速放加盟。非餐飲人入局、無廚師技能、無管理經驗、不想辛苦、產品標準化以及推動加盟發展,上述這些要素全部都重合在料理包這一概率里面了。
在資本的視野下,好不好吃不重要,解決問題、解決需求、帶動經濟才是重要的,這才綜合使得料理包在餐飲業野蠻發展——產品問世比好吃更重要(粉末類代餐比料理包難吃多了,但相應的客群卻吃得很高頻,可見食品在當代已經失去了愉悅味蕾的功能,而這也是資本對食品改革的一個方向)。
不過也先別批判料理包的反餐飲和反人性,如果一個東西確實沒有價值,那么它是不可能發展的。
以薯條為例,要吃薯條,廚師得拿土豆削皮、切配、再沖洗,傳統操作還會產生不少邊角料,更限于產品保質期的問題,而如果用速凍薯條,這些復雜的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
再比如一份鹵肉飯,傳統鹵肉飯極為耗時,如果用的是料包類產品,門店1-5分鐘即可出品,在當前工藝下,如果是優質食材和優質產線,那么做出來的料包產品并不見得比現做的差。再以效率、成本等為核心的商業思維下,部分餐飲產品用料理包做代替確實是一個優質的選擇。
料理包產品的尷尬境地:要么愛之如寶玉、要么棄之如敝屣
但凡是給人用的東西,它都得接受一個評價法則:喜歡的人說好、不喜歡的人說糟。料理包產品也是如此。
從廣度和深度來看,料理包經營模式目前多存于簡餐、快餐、日料、西餐、港餐、面食、燒烤等品類,從高大上的燉湯、鮑魚撈飯、佛跳墻再到平民快餐,如干鍋、炸雞、漢堡、蓋飯、煲仔飯、米粉等品類都被料理包攻下了,且外賣/純外賣品牌通常是料理包的“重災區”。
門店只需要煮米飯,再加上一些水煮蔬菜,其余均通過料理包產品解決,出品就像堆積木一樣,放入A、B、C等多個產品即可出品。
據筷玩思維調研發現,無論是廚師還是非廚師,只要用了料理包類產品,門店對于該產品是沒有勞動成果的,大多料理包產品也通常被歸為零售產品而不是餐飲產品,且老板在經營方面對于此類產品的考慮基本只有一個指標:成本決定價格。
我們可以看到,大多料理包門店通常都會有數款特價產品,其套餐價格通常為9.9元。這也是門店月銷能9999+的一個核心原因。據記者了解,如果整個套餐產品是老板自己親手經歷了買菜、切菜、炒菜做出來的,大多不樂意只賣9.9元。
有餐飲第三方認為,料理包產品的加入不僅方便了門店經營,更解放了餐飲定價的思想,顧客也樂意消費,反正9.9元一個套餐,你還要什么自行車?
一個很明確的痛點是:料理包確實降低了門店的經營成本,甚至是管理成本且研發成本為零(雖然品牌方的研發成本會均攤到具體產品上)。對于一份鹵肉飯來說,料理包無論從食材成本、廚師成本、經營成本都有絕對的優勢。
在成本面前,大多傳統餐飲人對料理包的抗拒是很明顯的(人的認知是便宜沒好貨),更基于沒有產品操作價值,廚師們也不關注料理包,但這并不是仇敵之間的關系,而是廚師們認為料理包不具有餐飲價值(也確實如此),再加上料理包多數是小白群體在用,這更加大了兩方陣營的敵對性。
就好像用半自動咖啡機的咖啡師瞧不上用全自動咖啡機的咖啡師,吉野家、真功夫、必勝客等后廚廚師同樣不被社會廚師、星級飯店廚師認可。而我們還不可否認的是,一些料理包產品確實比現做的要好吃,但需要注意關鍵詞:“一些”,也僅僅是一些料理包產品而已。即使數年、數幾十年過去了,大部分料理包目前還處于開發測試階段,它們遠遠未觸碰到美食的門檻。
PS:歐美資本在19世紀就宣傳營養來反好吃,但要知道,營養不等于新鮮,更不等于好吃,如果只是營養,那么可以通過添加劑來解決,這是資本的小心機,甚至還有用宗教禁欲來批判口舌之欲的追求,大大宣傳難吃才是本質,而這也確實獲得了成功,比如開發了代餐類市場,代餐雖然難吃,但起碼有“營養”,而且也可以表現一個人“自律”。這些都是資本的心機。
我們筷玩思維不贊同上述這類方向,大多美食科學也不贊同這類方向,因為這的確是反人性的。想想如果我們的公眾及后代連識別美食的權力都被資本剝奪了,那就太可悲了。
我們且回歸產品,在筷玩思維看來,料理包和傳統餐飲當前陷入了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尷尬關系,這實則既不利于整個餐飲業發展,更不利于料理包產業的未來,兩端是時候融合了。
料理包的餐飲化還需要傳統餐飲人入局,料理包的產業發展也需要從源頭做模式變革
鄉村基和大米先生屬于同一家公司,但兩個品牌走了兩條不同的路:一個現炒、一個料包。
現炒還是料包化?在行業里的兩方誰也說服不了誰,目前還處于相互鄙夷的狀態。
也有行業評論指出,料理包什么時候能真正發揮作用,還得看傳統餐飲人什么時候愿意入局。這話的意思并不是說傳統餐飲人要把餐飲的技能丟掉,再全部轉型為料理包模式(雖然也確實有這樣提倡的,很明顯是居心不良之輩),而是說傳統餐飲技法可以和料理包產品相結合。
料理包和餐飲大廚是兩個并不沖突的互補工具,而更為首要的是確定料理包的二類工具價值,它可以作為一個中間工具,而不是全部產品。其一,料理包和餐飲廚師可以結合且應該結合;其二,該結合關系要以餐飲廚師作為主導。
我們在餐飲業看到了一些走捷徑的不合理做法,門店把料理包當成了全部產品,認為料理包就是來取代廚師的,這是一個極為錯誤的想法,其一,全料理包式經營在目前還未到時候,料理包產品還未具有相應的成熟度;其二,料理包產品需要篩選,而只有廚師才有篩選優質料包產品的能力,會做產品的才更懂產品;其三,正因為料理包產品的不完備屬性,它更需要會餐飲技術的廚師在門店對之做最終優化,以彌補料包產品的原生缺陷。從上述路徑來看,我們可以大體找出料理包產品和餐飲業的結合方式。
在思維端,餐飲老板和廚師都要擺正思維,明晰料理包產品只是一個補充工具,它還未到成為全部產品的時機,只有廚師技藝+料理包的結合模式才能補齊兩者的缺陷。比如料包產品為廚師提效,廚師為料包產品增色(得保留部分全手工的產品,傳統技法不能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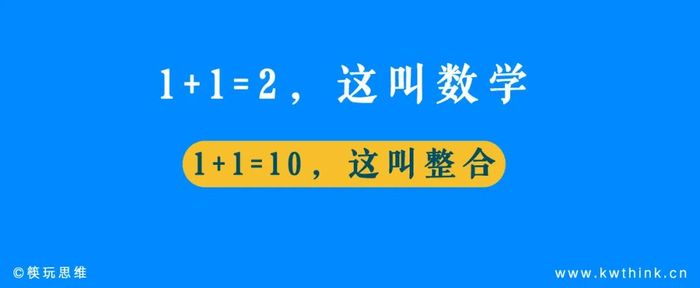
在運營端,老板和廚師要一起深入料包產品,確定哪些產品可以料包化,哪些產品絕對無法料包化(核心產品、招牌產品)以及確定門店料包化/餐飲化的比例,最終找出料包和廚師的共存方式,比如一款鹵肉料包產品應該如何與廚師結合來產生更好的產品方案。
而這也反過來告訴料理包的產業鏈,料理包產品需要做基礎款,比如在即熱產品之外推出半成品款,給門店廚師預留為產品潤色、調味的機會(不要把調味和烹飪在工廠做完了)。因為有了基礎款,一家料理包公司可以為多家餐飲門店供貨,即使拿到同樣的基礎款,經過不同品牌、不同廚師的優化,最終也會讓標準產品擁有品牌的個性化,而不是大家都千篇一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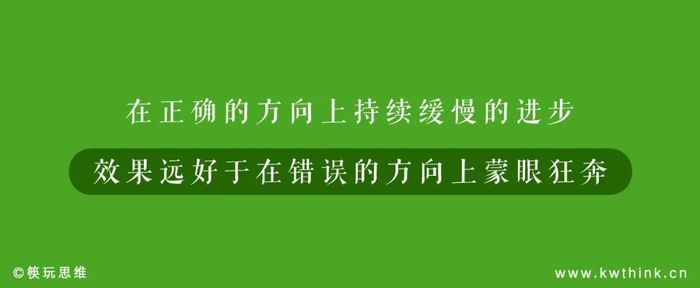
結語
從本篇文章的視角來看,料理包產品在B端依然是重心,但由于料理包企業錯誤的定位,導致了餐飲業對料理包貼了“垃圾食品”的標簽,這同樣導致料理包行業止步不前,只能陷入無規則、無壁壘的同質化競爭局面。
餐飲門店是需要個性化的,如果料理包產品不為門店的餐飲化留出空間,有講究的餐飲人自然難以接受料包產品,畢竟工廠把事兒做完了,門店就淪為工廠的銷售了,這是創業者認知中無法接受的事兒。這才讓愛的人愛之深、恨的人恨之切,而這樣的局面不僅不利于料理包產品的邏輯升級,更不利于傳統餐飲業的再發展。
關于料理包和餐飲廚師如何配合,這是一個具體的課題,需要行業雙方做好協商和方案協同,更需要對目標進行持續優化,這是一條長遠的路,但也是一條新的路。而在老路走不通的情況下,新路或許不妨一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