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般認為荒野(wilderness)是一種對立于人類文化的環境,它是一個龐大的地理生態系統,沒有因人類活動而產生重大變故或受到影響。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人們傾向于在遠處把荒野理想化,津津樂道于某種荒野的理念,而且通常是一談起它就想到某些優美或者崇高的東西。
在《當我高歌,群山起舞》(When I Sing, Mountains Dance)這本書里,我(指本文作者Irene Solà)給自己定下了一項挑戰:以居住在某地區或穿越此地的所有存在者的聲音與視角來呈現這片土地(比利牛斯山的某一區域)。參與故事講述的既有人類,也有非人類的存在者,還包括了一些民間傳說與神話中的角色。敘事以一系列假想的聲音編織而成,涵蓋了狍子、狗、蘑菇、幽靈、水精靈、烏云乃至于當地的某一地質層。
相應地,我想提出一種方法來處理文學中的荒野,使之不局限于被動意義上的“景觀”或引人入勝的美麗“背景板”,而是將其當作某種積極主動的實體來看待。這種方法旨在對荒野概念發起拷問,對其中的矛盾提出質疑,以及探究我們與那些被我們冠以“野性”之名的空間究竟有何關系。或者反過來看,一個對荒野的理解深刻到一定程度的人,也只得尊重其不受拘束、自由自在乃至于危機四伏的本性。
1. 《迷失針葉林》(Lost in the Taig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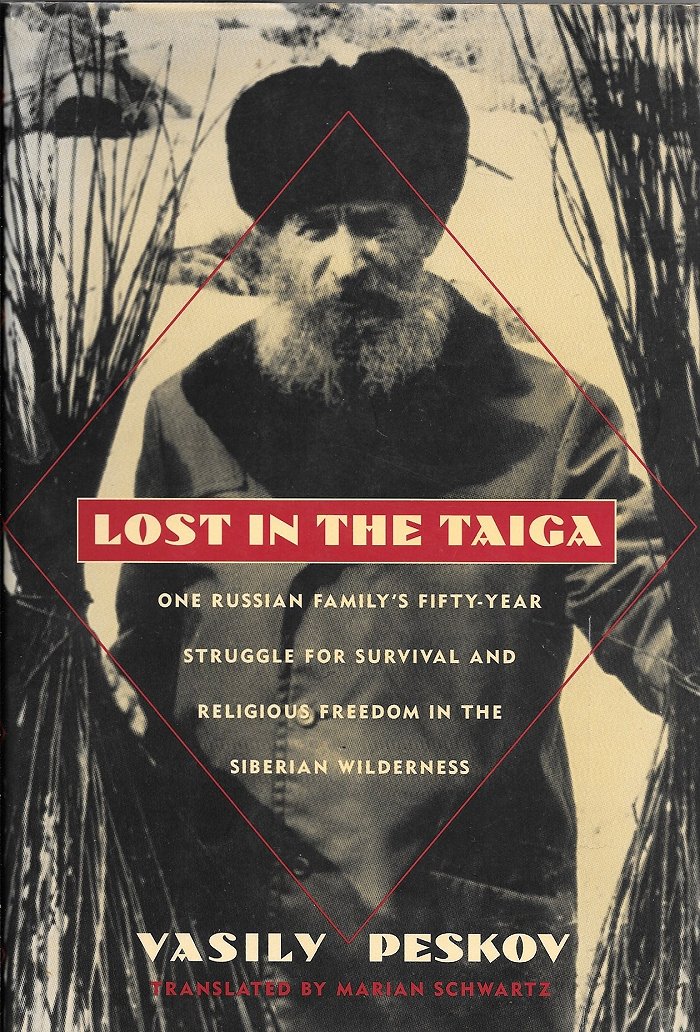
該書記載了作者瓦西里·佩斯科夫(Vasily Peskov)與利科夫一家人相處的經歷,這個家庭在俄國腹地的針葉林中過了四十多年與世隔絕的生活。佩斯科夫敘述了他們在針葉林的極端環境下如何掙扎求生,艱苦的條件常常與這家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那種積極樂觀態度形成鮮明對比,但也難免會有人懷疑,生活選擇與文明方向的不協調可能早晚會對他們構成困擾。
2. 《獨立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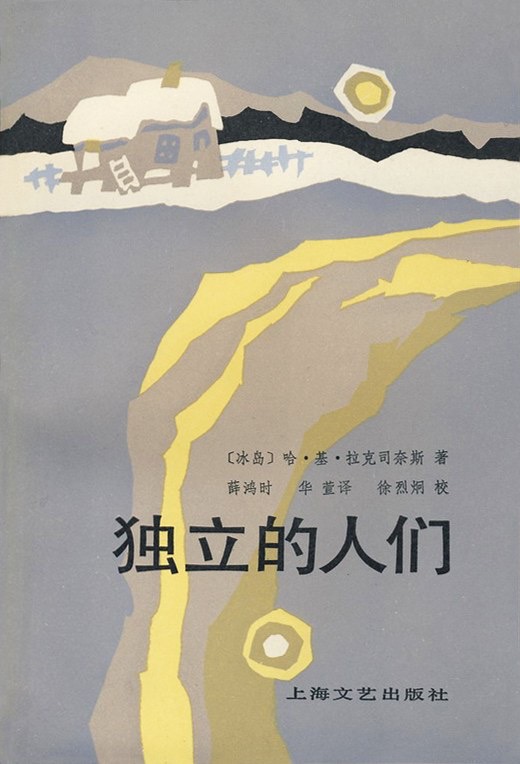
[冰島]哈·基·拉克司奈斯 著 薛鴻時/華萱 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3-1
哈·基·拉克司奈斯的小說聚焦于比亞圖爾(Bjartur of Summerhouses)這位20世紀初的冰島貧農,他在一處僅僅是勉強可以住人的邊緣地帶經營著一座與世隔絕的小農場。這里的荒野成為了比亞圖爾的克星,全書著重呈現了在荒涼而殘酷的環境里為生存而展開的暴力斗爭對人類靈魂所造成的影響。
3. 《死亡在春天》(Death in Spring)

梅塞·羅多雷達(Mercè Rodoreda)這部陰暗的小說沒有明確的時間,背景設在一個交通極為不便的無名山村,周遭危機四伏。“卡拉門”(caramens,一種從未有人見過的生物)或者河流泛濫的沖擊令房屋隨時都有被沖走的危險。村民生活在原始且有如噩夢一般的法律與儀式之下。村莊周圍的環境固然無情,但窮山惡水和人類的殘忍一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4. 《沃爾》(The Vorr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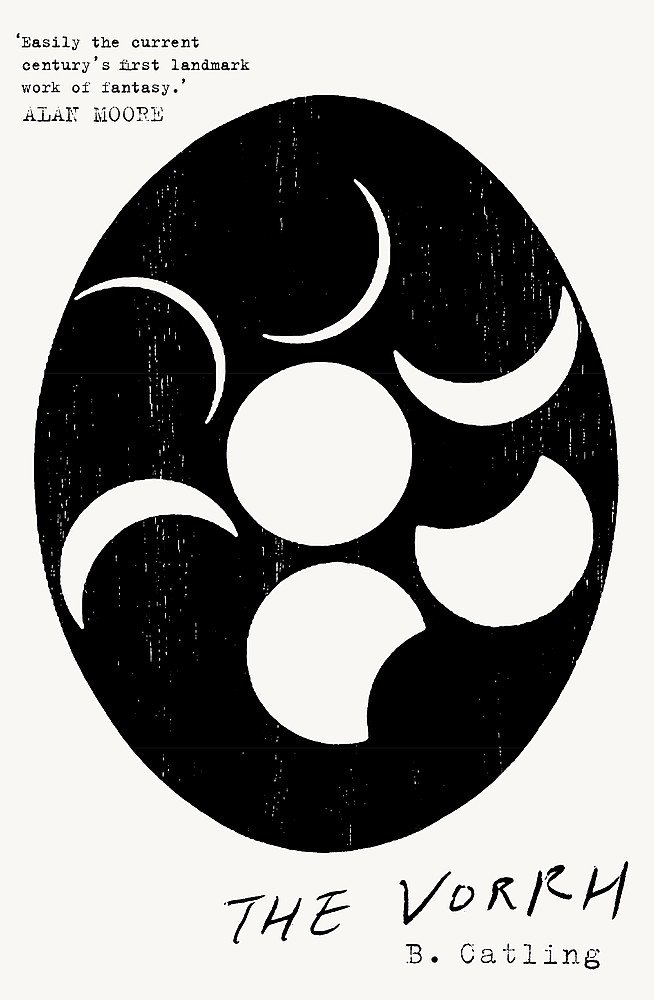
在布萊恩·卡特林(Brian Catling)的“沃爾三部曲”里,“沃爾”(the vorrh)指的是一處非常古老的叢林,它已經老到了被認作是伊甸園的所在地,亞當和夏娃在那里與獨眼巨人和食人族(它們會用一桶桶水和食物誘騙人類深入叢林,然后吃掉他們)一同游蕩。這片叢林本身就是一個具有知覺甚至于意志的實體,它對人類表達拒絕的方式就是驅使他們發瘋。
5. 《皮拉內西》

[英]蘇珊娜·克拉克 著 王爽 譯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1-12
搬進不可能的荒野,這里的荒野是一處建筑。蘇珊娜·克拉克的《皮拉內西》構想了一個沒有盡頭的室內大廳世界,里面滿是雕塑,有開闊的天空以及漲落的洪水。與《沃爾》類似的是,長時間呆在這些大廳里似乎對人類的精神狀況有負面影響。正如書里永遠歡欣鼓舞的主角皮拉內西所寫:“愿你的道路平和安寧,你的地板完好無損,愿房屋讓你的眼中充滿美好。”
6. 《葉子屋》(House of Leaves)

又一部不走尋常路的荒野故事。灰樹巷里有一間屋子,屋里比屋外更加廣大。其內部是無窮無盡的走廊與灰色的樓梯,不斷發出聲響、變換身形,以至于有了一股詭秘意味,這樣安排的最終目的就是誤導你。前來獵奇的人會像探險家一樣,帶上繩索、補給品、火把和相機。這間屋子的變幻無常已經到了違反邏輯學和物理學的程度,從另一層面看,它對于讀者而言也意味著幾乎無法駕馭的海量文本,讀者可能也會跟著迷失其中。
7. 《泰迪熊的父權制》(Teddy Bear Patriarchy)
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這篇文章非常適于快速了解絕大多數圍繞自然與荒野的概念是如何在西方的思想與文化里得到建構的。哈拉維反思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過往及其創始人、贊助人、管理人以及首席研究員,旨在理解自然史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深層聯系,它們并非像看上去那樣是全然無辜、中立而無害的學科,而是與一個歷史悠久的統治階級有著內在的關聯,這一階級又將其偏見與強有力的政治議程銘刻在了博物館的制度根基之上。
8. 《野性》

《野性》匯聚了一系列有關再野化(rewilding)的短論與思考。再野化本質上是一項倡議,它主張修復生態,鼓勵人們撤出某一區域,任其自然發展——從文化的角度看,就是聽憑其自生自滅——而不贊成對自然資源加以積極的照料與管控。面對一系列迫在眉睫的生態災害與同樣泛濫成災的“漂綠”(greenwashing)行為,這本書就像是一股清風,作者喬治·蒙比奧(George Monbiot)不僅在其中分享了自己的理念、案例研究與切身經驗,也提出了一些有助于回歸荒野的做法。
9. 《多少山頭本是金》(How Much of These Hills is Gold)

北美的戶外活動歷史悠久,但這一語境下的荒野卻主要是由白人男性的聲音來詮釋的,通常聚焦于充滿男子氣概的白人角色。其后果就是,與這一時間及地點相關的集體想象經常會否認或抹殺掉闖入這一虛構的、白人中心主義的美國西部的另類視點。在《多少山頭本是金》一書里,C·帕姆·張(C Pam Zhang)借助年輕的華裔女孩露西的視角,講述了加州淘金潮期間的一個堅韌不拔、勉力求生的故事。露西的聲音情感充沛,臨場感亦極強,她邀請讀者反思:在這一時期與背景之下,有哪些人的故事得到了講述?哪些人的故事又被忽視掉了?
10. 《火地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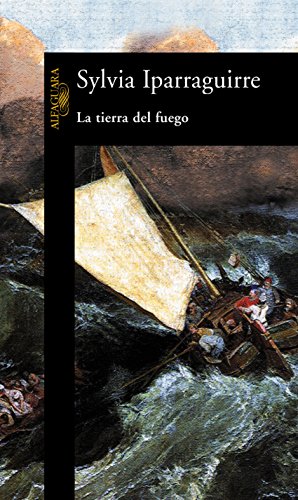
這本書的開端處引用了梅爾維爾《白鯨》里的一句話:“對我而言,我對遙遠的事物總是抱有持久的渴望。”在西爾維亞·伊巴拉吉雷(Sylvia Iparraguirre)這部歷史題材的小說里,英國士兵與克里奧爾母親之子約翰·威廉·格瓦拉(John William Guevara)講述了美洲原住民杰米·布頓(Jemmy Button)的故事,他本是住在合恩角的雅馬納人,兒時與其他一些火地島居民一道被中將羅伯特·菲茨-羅伊強行送到倫敦,試圖以英國文化來同化他們。這個故事令伊巴拉吉雷可以從所謂的偏遠地區居民的視角出發來展開反??思,進而重新審視某些抱有探險“渴望”的人:他們一旦認為誰是野蠻而不開化的,便要試圖馴化之、為其重新取名乃至于摧毀之。
(作者Irene Solà系加泰羅尼亞作家、藝術家)
(翻譯:林達)
來源:衛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