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實習記者 林柳逸
編輯 | 林子人
養顏燕窩、防皺精華液、抗初老葡萄籽、密發黑芝麻丸……在倡導精致生活的小紅書上,一名不到17歲卻自嘲“老少女”的花季女孩分享了她的抗初老秘笈,這篇筆記在被大量點贊與收藏之余,也引發了評論區眾多女性的驚異與焦慮。據《福布斯》數據統計,大眾的抗衰意識正呈現出持續年輕化的趨勢,中國20-24歲的都市女性中,有2/5(39%)在使用抗衰老產品。據2020年京東618數據調查,全網有25%的抗初老產品被00后消費者買走。

在全民抗衰已成大勢所趨的當下,對衰老的焦慮已成為新一輪容貌焦慮的核心,值得玩味的是,哪里有焦慮,哪里就有市場。在“00后老少女”和“95后老阿姨”的抗老秘笈背后、在對“逆齡生長”和“不老女神”的追隨與贊嘆背后,是中國“抗衰市場”的高速增長:Euromonitor相關數據顯示,中國抗衰市場規模自2016年起呈現持續加速趨勢。2018年,抗衰市場規模達到472億元,同比增速高達17%,《福布斯》報道認為中國抗衰市場未來還有1000億的發展空間。
關于抗衰老,市場的需求與導向間相互強化的微妙關系值得進一步探析。在當代,“衰老焦慮”似乎已逐漸從原始的“死亡恐懼”和“時間恐懼”等哲思中剝離,演變為一套以“青春”與“美”為核心的消費話術。在追慕年輕、恐懼衰老的焦慮之余,更值得追問的是,“青春”與“美”的必然聯系是如何產生的?“年輕即資本”這一論調的邏輯、陷阱以及它所掩蓋的結構性的不平等又是什么?在抗衰老的時代大勢中,衰老的真相卻在逐漸遠去,它不斷被懸置、被邊緣化、被逃避。而只有真正辨析消費文化對身體的裹挾,直面“變老”在個人與社會層面的真相,個體才能夠真誠地直面自身的焦慮,不再逃避,而是更有勇氣地接納我們必朽的身軀。
“抗老”中的女性競爭:身體的拜物教與美的情色化
2021年,“沉浸式護膚”等視頻內容成為了廣大女性網友慰藉無聊、舒緩焦慮的新選擇。數十種護膚品在涂抹、按摩、拍打的過程中為肌膚所吸收,這套冗長而精細的動作流程,激起觀者對臉部毛孔、細紋、線條等細微變化的體察,并喚起感知上的刺激、愉悅和舒展。于沉浸式護膚中,當代精致女孩對自身肌體的全方位呵護與關注可見一斑。然而,對身體的沉浸式關注并非當代的造物,早在上世紀,它就頻繁地出現在各大時尚雜志與大眾傳媒中。“我發現了我的身體,感覺純凈地觸到了它”,“就像我的身體和我進行了擁抱,我不由地愛上了它,我想用對自己孩子的那種溫情去照料它”——這些頗含神秘色彩的文字出自上世紀法國時尚雜志ELLE的女性讀者,她們正在對身體的重新發現和全情投入中自我告解。


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觀察到,20世紀的時尚行業和大眾媒體普遍對女性提出“內轉到自己身體中去,并從身體內部對它進行自戀式投入”的建議,它們鼓勵女性“把身體當作一座礦藏進行溫柔地開發”。然而,這樣做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更深刻地了解它,而是根據一種完全拜物教的邏輯,“為了使它向外延伸,變成更加光滑、更加完美、更具功能的物品”,以使它在時尚市場上表現為青春與魅力的可見符號。
自20世紀下半葉,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自戀式投入”就被等同于自愛和自我實現的神話。經過女性主義與性解放運動的洗禮,身體作為“性自由”與“性別平等”的符號被重新發現,并在大眾傳媒的輿論導向中不斷被神圣化。人們從衛生保健學、醫學、時尚等各領域給它附加光環,又建立起無數護理方法、飲食制度、健身實踐和快感神話。鮑德里亞認為,這一切都證明身體變成了一種可以救贖我們自身的物品,它的功能與地位徹底取代了靈魂。
其實無論何種物品都能依據同樣的拜物邏輯來扮演身體的神圣角色,但鮑德里亞認為,在消費文化中,身體是心理所擁有、操縱、消費的那些物品中最美麗的一個。身體不再是宗教視角中的“肉身”,也不再是工業邏輯中的“勞動力”,而是從其年輕、貌美等物質性出發被看作“自戀式崇拜對象”,被神圣化為功用性的身體。身體的一切實用價值(能量的、行動的)向功用性的交換價值轉變,這正是美麗和時尚的邏輯,同時也是“年輕即資本”的邏輯。
值得警惕的是,鮑德里亞注意到,消費文化更多地催促女人通過身體進行“自我取悅”,而要求男人通過身體進行“自我區別”。前者強調的是向內索取、不參與競爭的被動性,是一種自戀式的討好和關切,而后者則強調競爭性、主動性和高要求,近似于以高貴和榮譽為核心的苦行式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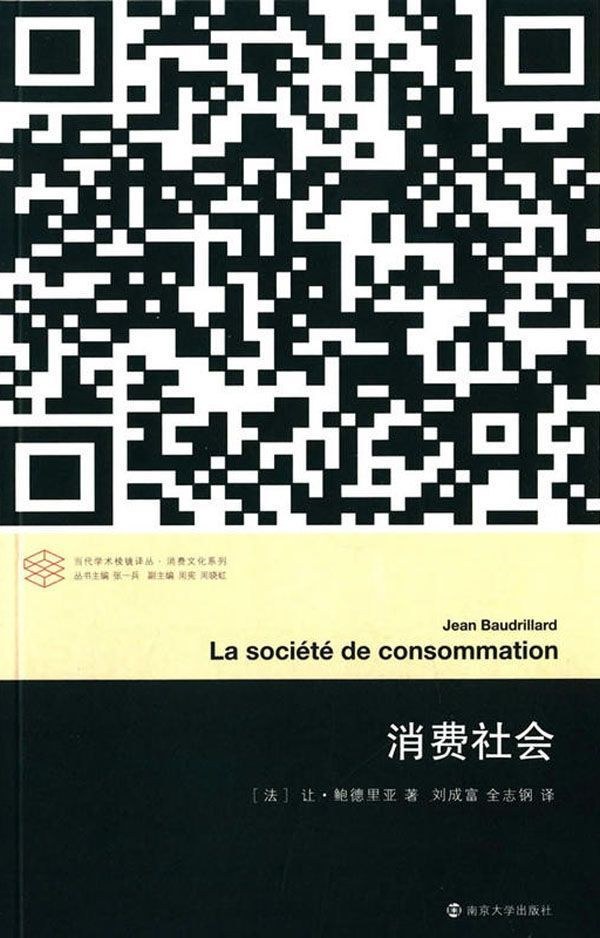
[法]讓·鮑德里亞 著 劉成富 全志鋼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近年來興盛于互聯網的諷刺性語匯“雌競”,揭示的正是女性群體在“投入身體”這一消費文化的誘導下興起的“內部戰爭”。吊詭的是,女性并不能通過參與雌競獲得在社會競爭中的主動性,而只是作為被爭奪的對象卷入到自我裝扮的間接競爭之中。為了破除雌競氛圍,女性之間旋即又興起了另一種論調,即強調“美貌是為了自我取悅”。然而,這兩種論調只是區別了美貌的目的,卻并未轉移對身體外在物質性的強烈關注,女性被鼓勵“與自己的身體戲耍”,而不是投入社會競爭、進行自我區別。鮑德里亞認為,在自愛、自我取悅、自我滿足的旗號下,女性身體的更高價值亦在一套完善的“消費服務”中被間接性地貶低。
在愈演愈烈的抗衰老比拼中,醫美、化妝品和時尚行業正在其中微妙助力,使得抗衰老成為一場基于資本投入的持續嚴苛化的女性競爭。在追求身體之美的拜物教和女性競爭中,美的意涵亦不斷地從內在性與永恒性等精神范疇中剝離,成為與性吸引力直接掛鉤的身體屬性。
正如伊娃·易洛思在《愛,為什么痛?》中所指出的,女性身體以及后來的男性身體的情色化橫跨所有社會階層,是20世紀早期消費主義文化最驚人的成就。19世紀的道德觀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化妝品,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視它為“真實的內在道德美”的“不正當替代品”,社會審美觀念也尚未明確地指向性隱喻。進入20世紀,依照易洛思的觀點,性活動的合法化被高漲的消費文化裹挾后,所誕生的副產品便是“人體的情色化”。時尚、傳媒、健身等多個經濟行業聯手販賣和構建了“情色本位的自我”。在不斷突出性特征的審美觀念里,人體被理解為感官肉體。這種文化將男性,尤其是女性的性別身份轉換為性身份,視性別為性動因。“青春”與“美”這兩個特征符,演變為“情色”與“性”的特征符,易洛思認為,人體的商品化正是通過“青春”與“美”這兩個特征符得以實現。
“初老”的焦慮與自由:重獲身體,在“自我陌異”中自我贏得
在人體情色化的消費文化語境中,肉體的“青春”和“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并隱晦地指向性活動與性隱喻,因而,肉體的衰老也意味著性魅力的喪失,被主流商業市場和時代審美觀念邊緣化。衰老的肉體在欲望故事中被驅逐出場,日漸憔悴的容顏引發自我厭棄與自我陌生,然而這些“喪失”并不全然是苦澀的,它也意味著一種嶄新、純粹的自由。
在《倫敦生活》的第二季中,33歲的女主角Fleabag在酒吧與一位58歲的事業女性進行了一場關于更年期的討論,這位“已經絕經”的女士驕傲地駁斥了“衰老是恐怖的”等焦慮言論,轉而聲稱衰老終究是甜美的、自由的。“該死的更年期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那位女士認為,更年期意味著女性終于得以從痛經、胸部腫脹、生育等肉體痛苦中解脫,與此同時,“是的,你整個骨盆都毫無用處了,你變得富有魅力,但也沒人會撩你,然后,你就自由了。不再是奴隸,不再是生育機器,你只是個單純的處于事業中的人(person)。”在臺詞中,從“female”到“person”的用詞轉變暗示了女性的衰老實際上亦是從“女人”回歸為“人”的身份蛻變過程。當社會賦予的性隱喻、男性凝視、身體的功用性機能等等意義統統從女性身體中被驅逐出去,女性將變得孤獨而又衰敗,但也正是在孤獨老去的過程中,她得以完全擁有自己純粹的身體。
在哲學散文《變老的哲學:反抗與放棄》中,奧地利作家、哲學家讓·埃默里也談到了容顏衰頹所帶來的肉體的新自由:“那陌生的,因為已經從世界中逐出而不再朝向世界的面孔完全成了他的,是自我陌異和自我成就的交合。”與此同時,年輕時他未曾在意過的,他的外表、雙腿、胃,在遲緩和疼痛中也“完全屬于他了”。埃默里因而形容道,“變老的人將在身體中重新擁有時間”——年輕人把自己的身體投入到外部空間中去,而開始變老后,生命存在于他能感知到的、已經度過的時間中,而不是寓于未來的可能性之中,這時他才真正“擁有”時間。
埃默里亦從哲學的視角出發,對正在變老之人的焦灼心境做出了細膩的描繪與闡釋,揭示出我們在開始變老之時感到焦慮的原因所在。依照埃默里的觀點,正在變老的人普遍處于一種十分具象的“自我與非我共存”的哲學境遇之中,這種焦慮心境的第一個層次便是“自我陌異”:
“鏡中的那個自我,那個從青年時期就最親密的人,如今卻作為一個陌生人站在我們面前。”
黃褐斑、下垂的肌肉、溝壑般的皺紋、日漸稀疏的頭發……當變老的人覺察到自己衰老的痕跡后,鏡子里的樣子開始在眼前揮之不去,薄薄的一層“日常自我”便瞬間撕裂,人們將驚恐于“成為自己的陌生人”。埃默里認為,衰老之人的“自我厭惡”最強的組成部分正是這種“自我陌異”,那是“穿過歲月拖帶而來的年輕自我,和鏡中變老的自我之間的抵牾”。變老之際,我們比以往的任何時刻都更深刻地意識到,“我”是“自我”與“非我”的共存,而在年輕時,這種“在自己身上發現非我”的驚悚,盡管是人性基本狀態的一部分,卻被日常生活長期地掩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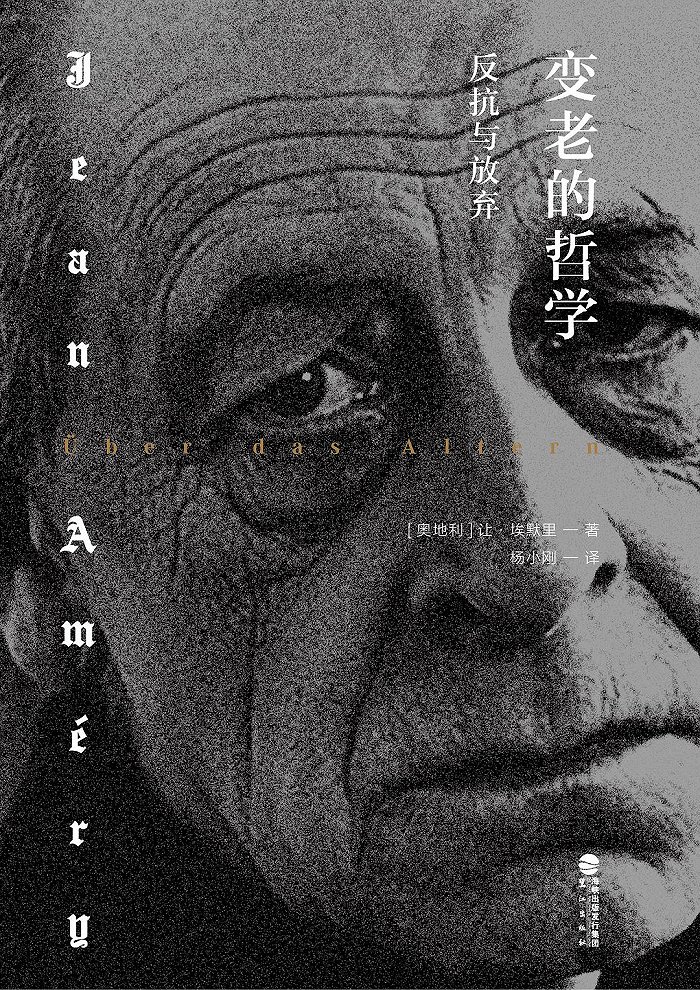
[奧地利]讓·埃默里 著 楊小剛 譯
鷺江出版社 2018??
然而埃默里提醒我們注意,被我們視為“本己”的那個自我,實際上只是一種社會構建,是“按照社會方式定義的自我”。與那個被我們視為本己的“社會自我”相比,那個長了黃斑或牙齒松動的全新自我,似乎必須作為一個陌生的、敵對的自我來加以觀察和感知。這種“自我陌異”便是人們在面對衰老時的焦慮與恐懼所在。
我們不得不在越來越陌生的鏡像前以越來越壓抑的方式變成我們自己,逐漸從我們所熟悉的、視為本己的那個社會自我中分離出來。并且,我們越對自己感到陌生,我們就越接近于軀體中的真實的自己。埃默里認為,變老就是這種“自我陌異”和“自我親熟”的混合。總體而言,變老的人與他身體的關系仍然是一種自戀,只不過,對鏡中形象的熱戀不再是單義的,而是“厭惡與愛的復合”,在這種復合中,厭惡以一種畸形的方式愛著自身,而愛又讓自己深深厭惡。只有在這種復雜的情緒中,人們才得以最終意識到“自我陌異即自我贏得”這一晦暗事實。
抵抗“社會性衰老”:“占有”規定存在,“重啟”如何可能?
那么“自我贏得”之后呢?讓·埃默里悲觀地指出,在當前的社會中,一個正在變老的人即便重新贏得了自我,也無法擁有更多朝向未來的可能性。在埃默里看來,每個人的生命中都勢必有一個變老的節點,在那個節點前后,人突然意識到,“世界不愿再將他看作一個他可能是的人”,意識到自己成了沒有潛能的造物。肯尼迪43歲成為美國總統時,人們覺得他還年輕,而一位43歲的高校教師助理卻不年輕,埃默里進一步追問,如果衰老通常是一種社會判定,那么“社會年齡”又是依據何種標準規定的?它如何判定一個人的老去?
埃默里認為,以“占有”為基礎的世界從本質上規定了我們的社會年齡。在效益經濟中,一個人是什么、處于生命的哪個階段、未來可能是什么,通過他的占有之物被確定。正如青春往往意味著貧窮和“未占有”的狀態,擁有事業、資產和婚約的人常常被社會語境劃入青壯年的范疇。而當擁有之物停止擴張時,社會便又判決一個人老去,因為他作為經濟資源已不再有益,或者說他喪失了某種可兌現為市場價值的確定能力。普遍的秩序要求人們,必須擁有可以被明碼標價的財產或市場價值,“一旦他占有,他就進入社會年齡”,而倘若一個人不是占有者,那么他的社會年齡很可能是模糊的、無法確定的,也一定程度上會成為被社會放逐的人。埃默里進一步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通過占有才能被允許存在”的世界。
以“占有”為依據劃分的社會年齡,對個體而言意味著兩個方面的影響:其一,我們實際上是“經由他人的目光變老”的。“衰老”是市場與效益經濟為個體發放的通知書,“身體的腐朽”這一主觀事實經由“社會經濟效用”的判定而成為社會事實。其二,我們的存在由占有規定,這種被占有決定的存在偷走了個體變化的可能性。自主的個體逐漸被“占有”的要求規范化,這樣的社會剝奪了個體在任意時刻從零點重新開始、按照自身意志重啟生活的可能。
老去的潛臺詞是自我重復與自我鞏固,它意味著被自己已經做出的選擇、已經占有之物淹沒,衰老正是“存在的變化性”不斷被“占有”所侵蝕的過程。美國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在33歲時曾寫道,
“現在,我開始明白,隨著時間不斷推移,我的選擇面將會越來越窄,而(選擇)所承受的代價將會越來越大,直到某刻,我處在生活紛繁復雜的分叉口上,最終只能囿于其中一條道路,并且一路走到頭,從而進入靜止、衰退、腐化的階段,而時間則從我身邊匆匆溜走,直到我淹沒在時間的汪洋里,倍受虛無的煎熬……”
效益社會對于衰老的判決不僅關乎正在變老的人,更關乎所有仍然年輕的人和已經老去的人。埃默里悲觀地指出,“沒有人呼吁反對這個判決”,相反,年輕人對于衰老的恐懼助長了這一判決的合法性。而變老的人也拒絕與有相同命運的人團結一致,他們嘗試與衰老這一否定符號保持距離。但這并非出于對年輕人的熱愛,只是出于一種“荒謬的渴望”和“不愿坦白的嫉妒”將自己歸入年輕人的行列。是否可以設想一種社會秩序,在這個系統里,存在不是擁有,而是保持為變化的存在,個體不再被他人的目光壓制,而是可以從零點重新構建自己的未來?正如讓·埃默里所說,與這種理想相比,“社會經常向變老之人表現出的尊敬很無力,它證明不了任何東西。”
參考資料
《守住年輕?“抗初老”有話》,界面新聞http://www.cfztjj.com/article/6464039.html
【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法】伊娃·易洛思.《愛,為什么痛?》.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奧】讓·埃默里.《變老的哲學:反抗與放棄》.鷺江出版社.2018
【美】大衛·福斯特·華萊士.《所謂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湖南文藝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