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1987年,賈雷德·戴蒙德開始動筆為公眾寫書。這一年他50歲,在醫學生理學、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領域均有所建樹,研究的課題包括膽囊和新幾內亞島的鳥類,而在這個通常意義上職業軌跡已經定型的年紀,他的雙胞胎兒子馬克斯和喬舒亞出生了。“當時人們討論2050年的時候世界會發生什么,其中之一就是熱帶雨林會消失。屆時我已130歲,我肯定不會活著見到那一刻,但我的兒子們才63歲,正處于人生的壯年。我意識到,兒子們的未來不取決于膽囊,不取決于新幾內亞的鳥類,而取決于這個世界的狀況,取決于我們如何理解不同人群的不同經歷。所以,是我兒子的出生激勵了我從膽囊生理學轉向歷史、地理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并開始撰寫面向公眾的作品。”
從1991年至今,戴蒙德陸續出版了《第三種猩猩》(1991)、《槍炮、病菌與鋼鐵》(1997)、《性趣何來?》(1997)、《崩潰》(2005)、《歷史的自然實驗》(2010)、《昨日之前的世界》(2012)、《為什么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2014)和《劇變》(2019)。在被問到如何做到筆耕不輟時,戴蒙德回答稱,是因為自己從未感到書盡有趣之事,在寫作一本書時,對下一本書的主題就已成竹在胸。他說,他正在撰寫一本探討“領袖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的新書——一個被歷史學家和普通人都津津樂道的恒久辯題。“希望這本書能在2027年,也就是我90歲生日的時候面世吧。”這位85歲的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國家科學院院士依然神采奕奕,中氣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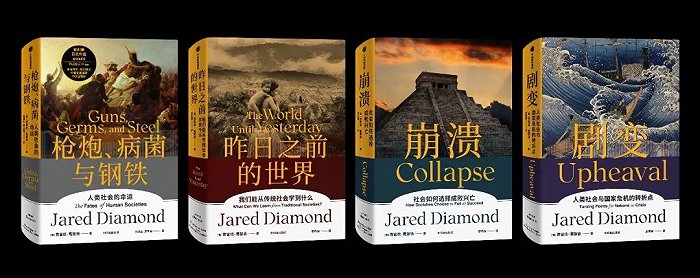
對中國讀者來說,最熟悉的戴蒙德作品應是《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緣起于戴蒙德在新幾內亞島做研究時偶遇的一位當地朋友亞力。亞力向他提出的問題曾長期縈繞在他的心頭,讓他用這本書來回答:“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這么多貨物,再運來這里?為什么我們黑人沒搞出什么名堂?”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戴蒙德駁斥了種族決定論,轉向分析各大洲的自然環境差異如何造成了不同的人類社會軌跡,并最終導致了人類歷史中的“領先者”和“落后者”。自出版以來,這本書對全球史提綱挈領又具有說服力的敘述引發了無數贊美與爭議。日前,戴蒙德與人類學家項飆以“人類社會如何走到今天?又將去向何處?”為題展開聯線對談,從《槍炮、病菌與鋼鐵》一路聊到新冠疫情和人類的未來。
地理環境差異是造成中西歷史軌跡分化的重要推動力
戴蒙德對《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中譯本再版感到開心。他說,這本書在中國首次出版的當年(2000年)僅賣出了4300冊,到了2021年在中國卻售出了近20萬冊,雄踞全球榜首,排名第二的是韓國(10萬冊)。

項飆注意到,戴蒙德在中國聲名鵲起正是始于《槍炮、病菌與鋼鐵》,在他看來,這部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對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歷史提出了重要的問題,他特別好奇的是,當歷史主要是由主宰者或勝利者書寫的時候,像亞力這樣的“歷史輸家”該如何閱讀歷史呢?我們是否能夠從歷史輸家的角度重新審視歷史,重新思考淹沒在歷史長河中的掙扎與消弭?
項飆指出書中提及了鄭和下西洋的案例。對中國讀者而言,一個有趣的話題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鄭和的東非之旅?這段歷史通常被解釋為在權力過于集中、充滿政治內斗的宮廷政治干預下,鄭和錯失了殖民非洲、搶先于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機會。但項飆提出疑問,我們是否應該質疑殖民主義被包裝為歷史驅動力的意識形態,而將之視作歷史進程的越軌?“這將會是一個亟需在智識層面充分辯論的問題,這樣的討論將有非常直接深遠的政治影響。”

戴蒙德坦言,他在那次與亞力的對話后并未與他重逢過,因此自己無從得知亞力對《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反應。對于中國和歐洲的歷史分流,戴蒙德主要是從地理環境差異的角度理解的。他指出,中國的海岸線平滑,歐洲的海岸線曲折且有多座大型島嶼,各個半島和島嶼逐漸形成擁有不同語言、社會和文化的國家,如意大利、希臘、西班牙、丹麥、英國和愛爾蘭。從河流走向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兩大河流長江與黃河呈平行東西走向,南北則由大運河貫通,幫助中國實現統一;但萊茵河、易北河等歐洲境內主要河流則像自行車的輻條般成放射狀。這兩方面差異造成了中國自古以來長期大一統,但歐洲則長期分裂的局面。
農業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西差異。戴蒙德稱,歐洲農業以小麥為主,中國農業以水稻、小米為主,小麥是后期引進的。小麥的種植高度獨立化,農民可以僅憑個人播種和收割。水稻種植則需要社群合作共同建設灌溉系統。在他看來,農業差異造成了中國文化更強調集體主義,歐洲文化更個人主義的傾向。在中國內部,農業種植的差異也能從不同地區人群的性格差異中看出來。戴蒙德表示,自己曾讀過相關文章指出,小麥產區的中國人比水稻產區的中國人更個人主義。
關于島嶼的重要性,戴蒙德補充道,距離適中的、“可見”的島嶼能刺激人們遷徙的欲望。因此無論是遠古時期的中國南方農民還是歐洲人,都積極地離開大陸,前往陌生的島嶼定居,而在非洲和美洲大陸原住民的移居與遷徙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相當罕見。
流動(mobilty)是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永恒的主題之一。在項飆看來,流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既是掌權者強加支配的手段,也是弱勢者爭取自由的途徑。從歷史上看,流動的重要動機是逃離支配,前往一個新的地點實踐自由。雖然說殖民主義的本質并不是“逃離”,但它確實引發了大量被處決的歐洲人動身前往“新世界”。而項飆指出,在新冠大流行時期,流動呈現出了一種與以往時代截然不同的特性,這具體體現在它被技術手段嚴密控制,項飆稱這些技術手段為“電子流動性基礎設施”(e-mobility infrastructure),它能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分配流動——在大部分公民被要求居家隔離以阻斷病毒傳播的同時,一小部分人(比如快遞人員、醫療人員等維持社會運轉必不可少的工作者)則能夠快速流動。他說,21世紀,電子流動性基礎設施的重要性甚至已經超過了流動本身,我們有理由認為,我們正在進入文明的一個全新階段。
全球化已經改變了世界的規則
在最新一部著作《劇變》的結尾,戴蒙德將視野投向全球,指出當下我們面臨的四大全球挑戰分別是核武器、氣候變化、資源衰竭和社會不平等。在此次對談中,他屢屢提及解決全球問題的緊迫性。在他看來,全球化在某些方面已經改變了世界的規則,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意識到,有一些問題是整個世界共同面臨的,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以新冠肺炎為例:一戰后西班牙大流感雖然在全球蔓延,但其速度和波及地區遠遠不及新冠肺炎。
“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新冠肺炎將奪走全球2%人口——相當于1.5億人——的生命,但我們還有比新冠肺炎更嚴重的問題,特別是氣候變化。”戴蒙德指出,正如中國無法獨自消滅新冠病毒一樣,中國也無法將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驅逐出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做到。要解決氣候變暖問題,各個國家必須齊心協力加強合作。

戴蒙德談到的另一個重要全球問題是資源衰竭,他認為歐美國家消耗水、電、金屬資源和食物的速度是不可持續的,當今世界已沒有足夠多的資源來供發達國家繼續消費,然而在以歐美為發展模板的全球化愿景中,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卻被告知,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過上美國人的生活,事實上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印度和非洲人民達到同樣的消耗率,相當于要以當前的消耗率養活900億的人口,今天的世界連養活75億人都勉強,又將如何養活900億人?要想在2050年擁有一個穩定的世界,就不得不降低美國、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的消耗率。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想在50年后擁有幸福的未來,就要打造一個歐洲、中國、印度、非洲和美國之間生活水平和消耗水平更平等的世界。”
“如果我們只專注于競爭,我們都將毀滅。世界的未來取決于中國、美國、歐洲、印度和日本通力合作,共同解決全球氣候變化、資源枯竭和不平等問題。”他強調。
項飆觀察到,當今的全球化影響力已呈無遠弗屆之勢,然而它也呈現出一種非常奇特的狀態:第一,在技術層面,全球互聯程度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第二,在意識形態或情感層面,不同地區對全球化都已萌發懷疑;第三,我們對全球合作的需求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看起來,當下的全球化似乎正在陷入“理智與情感”的矛盾。項飆認為,從16世紀歐洲對外殖民開始形成的全球化格局基于競爭、移民和自我利益驅動,二戰后聯合國成立,終于在制度層面為全球社會保證了一定的秩序感。值得注意的是,如今這一套全球化意識形態已陷入了死胡同,“很多生產和貿易活動很可能會出于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的考量回歸本地。”與此同時,全球協作變得更重要,卻又缺乏基礎。在項飆看來,除非我們能夠在未來幾年內對聯合國等現有國際機構進行深入改革,否則全球合作無從談起,但從目前來看,他不知道具體該如何實現這一點。
關于戴蒙德提出的消耗率問題,項飆的看法是,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全球南方的主體性及其提出的替代性方案。“現代化的敘事確實給我們呈現了一個相當扭曲的畫面,即每個人都應該渴望擁有歐洲人或美國人那樣的生活方式。但我們知道,從歷史上看,這種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槍炮和病菌殖民之上的。它在道德上是大有問題的,在生態上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全球南方的任務是提供一個全球性的答案。”
項飆指出,甘地、章太炎、竹內好都曾對西方工業文明提出過深刻的批評,試圖以另一種方式來想象如何組織個人與公共生活。當代全球南方的知識分子應該重新承擔起這一任務,發動一場觀念革命,宣布“你們擁有的物質財富我們并不感興趣,我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和你們不同”。他認為,大國停止干涉全球南方國家的內部事物或許是變革的起點,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在巨大挑戰面前保持冷靜的頭腦,“我認為未來幾年并不容易,我們需要進行一些深刻的批判性思考、宣傳以及辯論。”
新冠疫情會促進人類在其他全球問題上加強合作嗎?戴蒙德對此持謹慎樂觀態度。從表面上看,氣候變化的惡果不如新冠肺炎那般直接迅速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它以饑荒、海嘯和疾病傳播等間接方式奪走人類的生命,且作用是緩慢漸進的。但新冠肺炎或許會是一個比氣候變化更好的“老師”,提醒我們全球問題亟需全球性的解決方案。“我認為我們有51%的可能取得全球解決方案,49%的可能走向一個不圓滿的結局,機會就在我們的一念之間。”
歷史是道德故事還是科學?
對談的最后一部分圍繞歷史寫作展開。項飆認為,歷史不是一門科學,因為從根本上說,歷史事關人類的活動,它需要被定義歸屬——征服者和勝利者的歷史與受害者和失敗者的歷史是不同的。他相信歷史是一個道德故事,賦權人們去理解他們所處的位置,并指導他們如何行動:
“根據目前的歷史敘述,鄭和的遠航錯失了機會,因為殖民擴張、發達的工業以及采掘原材料等才被認為是歷史的推動力,但這只是歷史的一個版本。如果你從拉丁美洲、非洲,特別是像夏威夷或瑪雅帝國幾乎被滅絕的土著人和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歷史就是規則的歷史、野蠻的歷史。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擁有多樣的敘事呢?我想,我們可以給予那些不在歷史中心的人一種力量感和目的感。然后他們可以站出來說:這是我的理解,這就是我選擇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再次強調,賈雷德的書是如此重要,他提出所有這些問題可能會引發其他敘事方式出現,并豐富我們對人類的理解。”
戴蒙德表示,自己一直試圖使歷史變得更科學,因為他看到了歷史的教訓是有可能具有普世意義的。以新幾內亞人為例,新幾內亞的社會形態仍然非常原始,人們使用石質工具,沒有政府和文字,爭斗不斷,甚至食人,但戴蒙德注意到了在新幾內亞人和美國人之間仍然具有共同的基本人性特征,這對他來說意味著歷史的普遍性。他舉的另外一個例子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揭示了帝國戰爭背后的普遍邏輯——如果你不發出信號,對方就會對你的行為感到驚訝。“所以我謹慎樂觀地認為,是的,我們可以把歷史發展成科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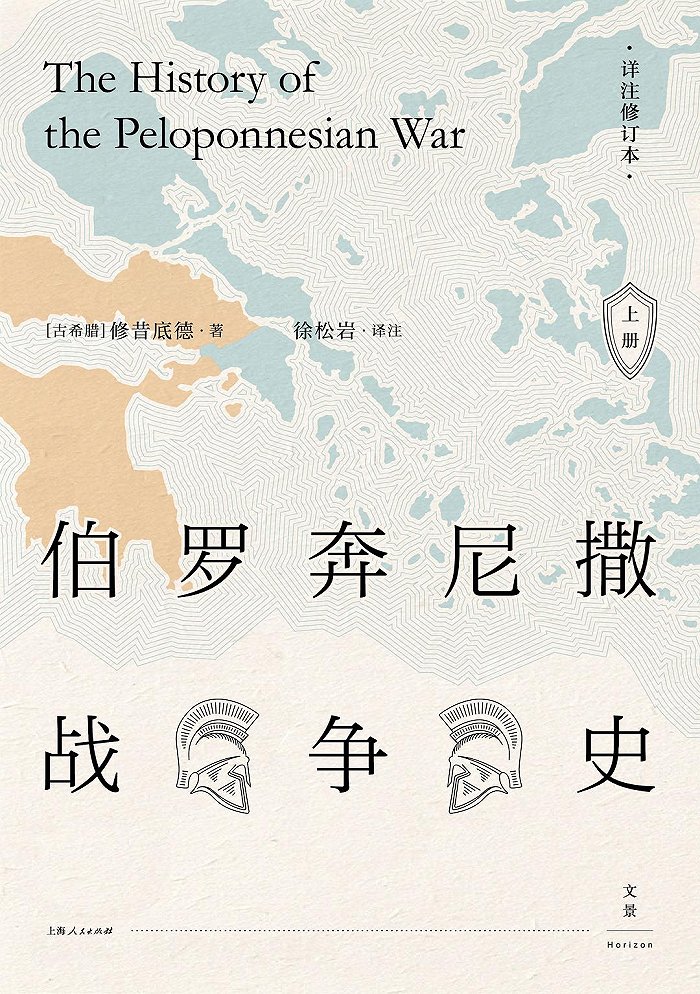
在對談最后,兩位學者給致力于寫作的年輕人提供一些建議。項飆認為,對于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長大的年輕人來說,寫作的起點應當是自己有溝通的欲望,“因為我們往往特別看重寫作,認為寫作是一場表演。你必須遵循一定的框架、一定的體裁、一定的公式,以證明你有能力駕馭某種寫作風格,那么你是在為幽靈寫作、為權威寫作,而權威會批準你獲得任何你想要的獎勵。如果你這樣寫,就是沒有目的的寫作,那就不要再寫了。”他提醒我們在當今的社交媒體時代對矯揉造作的同理心和虛張聲勢的寫作保持警惕。
雖然社交媒體時代導致人們的注意力下降,對長文章和書籍喪失了耐心,但項飆同樣認為一個巨大的、歷史性的機會正擺在寫作者的面前:“年輕人的教育水平已有了如此戲劇性的提高,特別是在亞洲和全球南方,年輕人渴望新的想法、新的分析、新的語言,以便他們可以使用來對自己的存在進行批判性思辨。因此,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的機會,可以讓我們進行有深度的、與公眾相關的寫作,從而影響公眾的思想,促進社會變革。”
戴蒙德提醒我們,在寫作時保持不恥下問的態度將使人受益匪淺。就他本人而言,他一直在寫作中保持合作交流的開放態度,從其他領域的專家那里學習,并將他們的見解消化吸收,融入自己的寫作中。另外,他分享了一個他從前英國皇家學會主席羅伯特·梅(Sir Robert May)那里學到的寫作技巧:將寫作分成兩個階段,先將想法記錄下來,編號,待組織好順序后再根據草稿一行行重寫,把它變成文筆優美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