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實習記者 林柳逸
編輯 | 林子人
我們的理性失落了嗎?哲學家陳嘉映在新書《感知·理知·自我認知》中提出了一個重要判斷,人類理性的工具化發展招致了“理知時代的終結”。他寫道:“理知走得越遠,感知的切身性或豐富性就越稀薄,乃至最后完全失去感性內容,變成了純粹理知、無感的理知。”陳嘉映對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時代抱以憂思,并提出當理知脫離了感知,當“智能”取代了“智人”,當“數理”取代了“道理”,當理性淪為了赤裸裸的工具理性時,理知時代便迎來了終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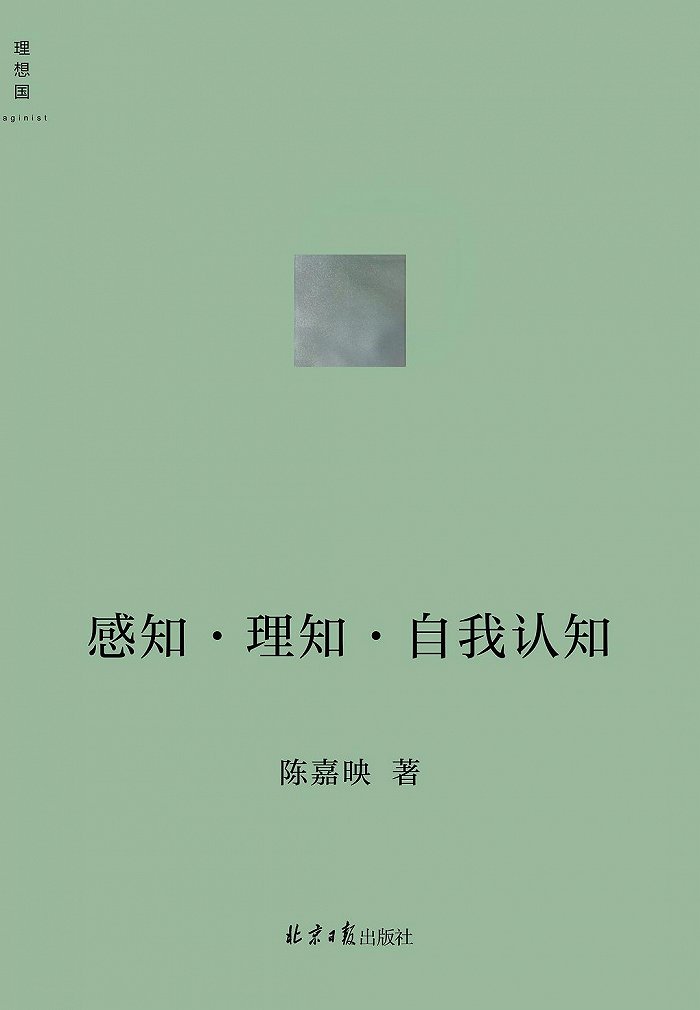
陳嘉映 著
理想國 | 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2-1
與理知時代的落幕相伴而來的,是“智人”(或曰哲人)的落寞與當代“智識結構”的轉變。2017年,在第二季的《十三邀》中,許知遠與馬東曾就“我們是否處于文化的粗鄙階段”進行了爭鋒相對的探討,引發公眾關注與持續熱議:當代的知識話語果真衰落了嗎?以智識為核心的精英文化被邊緣化了嗎?這些設問的背后是知識分子的“杞人憂天”與懷舊情緒,還是當前時代的真實處境?日前,在由“理想國”發起的以“文化-智識結構的當代轉變”為主題的直播對談中,陳嘉映與學者劉擎再度觸及這些懸而未決的當代議題,并圍繞“智識”于時代變革中的處境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追問與探析。
文字時代:“智識人”與“文人共和國”
在談論當代“智識結構”的轉變之前,陳嘉映首先細化了他的論述對象,并提出了“智識人”這一概念,以強調它與傳統“哲學家”以及當代“知識分子”等意涵的區別。“智識人”是自中世紀以來,近代民族語言形成之后,隨著文字閱讀的普及而崛起的智者群體,包括達·芬奇、米開朗基羅、但丁等追慕古典人本主義的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法國啟蒙時期以伏爾泰、盧梭等思想者為代表的哲人(philosophe),英國的休謨、德國的萊布尼茨等跨學科文人(man of letters),以及當代“不直接參與政治活動”的思考者與知識人(intellectuals)。“智識人”最本質的共同特點是,他們是“思想者”而非“行動者”,以“話語”(discourse)而非“行為”參與社會生產。
陳嘉映指出,在文藝復興以前,絕大多數人都被排除在智識話語之外。文藝復興之后,權貴階層沒落,近代民族語言進一步生成,拉丁文的壟斷性地位被打破,能夠閱讀文字的人越來越多,總體而言,文字閱讀條件的改變促成了智識結構的轉變與“智識人”的形成。


在識字率與文化普及率極高的19世紀,文字作品曾經是智性結構中最核心的形式,在人人都閱讀報紙的紙媒時代,寫作者曾經是智識結構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陳嘉映認為,“對智識人的追慕在19世紀下半葉達到了頂峰”:在當時社會開辟出的崇尚智識的文化場域中,智識人與智識人之間可以忽略種族、國別、階級、立場的差異,赤裸而真誠地交鋒,進行系統的、理性的說理與探討,形成蔚為壯觀的“文人的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man of letters)。劉擎亦贊同類似“共和國”的提法,他補充認為,在曾經的歐洲知識分子共同體中,“道德與政治立場的不同并不構成對話與交流的障礙。”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亦對二戰前的歐洲文化與文人的昔日榮光加以追思與緬懷,依照劉擎的說法,中國在80年代也曾贏來過與之類似的文人榮光和“文人共同體”。
圖像時代:“數字”驅逐“智識”,“話語”淪為“表達”
陳嘉映認為,以線性邏輯、結構性思維為基礎的“文字”,已不再是當代智識結構中最核心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圖像”的泛濫。“在以前,圖像是昂貴的,而如今,圖像卻是最最便宜的東西,比文字便宜很多。”陳嘉映提醒大眾注意,在疫情的常態化過程中,數字對人的驚人的掌控力,以及俄烏戰爭中短視頻作為重要媒介的歷史性參與,這些現象皆為“數字時代”權力的新型表征。
進入20世紀,尤其是二戰之后,西方社會的智識結構發生了重要轉變,“我們進入了所謂的后現代,或者說圖像時代、數字時代。”在陳嘉映看來,數字時代憑借“技術門檻”將人群割裂為了兩個部分:其中一半是掌握數字技術的人,以硅谷、中關村的技術精英為代表。他們通過“數字”理解世界,于他們而言,世界不是感知的,而是數字的,因而是可復制、可衡量的。另一半的人則無法通過數字理解與掌控世界,而是通過接收“圖像”理解世界,而圖像恰恰是與數字距離最遠的一種形式。于是,在當代,掌握數字的人炮制圖像,不懂數字的人接收圖像,形成無法互通的技術鴻溝,唯有“商業”能夠將相互隔絕的兩端聯系到一起。在此種態勢中,技術一定程度上壟斷了對世界的詮釋,進而將“智識話語”從社會結構中驅逐了出去。
然而,智識話語的衰落在當代究竟意味著什么?陳嘉映在界定“智識話語”(discourse)時,將其解釋為一種“系統說理”,以此區別于智性含量更低的“自我表達”。“智識話語”實際上意味著一個能夠熏染、教化大眾,容納不同意見的文化場域和對話空間。然而,知識平民化之后,公眾“表達”的愿望似乎遠遠超過了“獲知”(being informed)的愿望:人人都想要表達,這種表達的需求在陳嘉映看來,并不盡然是從人的內在自行生發的,而是很大程度上被技術塑造與引導的。數字讓圖像變得“更便宜”,更廉價的表達成本催生了更豐沛的表達欲。我們因而進入了昆德拉所謂的,人人都是作者卻沒有聽眾的時代。

陳嘉映指出,理論上看,在智識話語的衰落之后,勢必會有其他的智性力量涌入,以填充這一真空,但事實卻是,智性含量更低的“表達”填充了“系統說理”的真空。陳嘉映進一步總結稱,在圖像時代與數字時代,“智識話語”淪為了“個人表達”:用以交換、修正、調和不同意見的“智識話語”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化、情緒化和政治化的“立場表達”。
“平民化”的悖謬與出路:讓行動者與思想者各司其職
誠然,對知識的平民化、表達的民主化加以反思,并不是為了回歸一個哲人理知專斷的傳統。“知識人有過屬于他們的時代,正如武士、僧侶有過他們的時代,只不過如今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劉擎立足于不可抵擋的民主化趨勢,進一步指出,“民主比明君更難”,當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公共生活,我們應當思索的是如何走向更好的民主,而非抱以知識分子對自身昔日榮光的懷戀與感傷。
劉擎進一步闡釋了知識平民化的多面性:一方面,后中世紀“文人共和國”的興起,與市場對大眾的教化作用有直接的關系,正如大眾音樂鑒賞力的提升是貝多芬備受推崇的時代基礎;而另一方面,當代知識人聲音漸趨微弱的態勢,從表面上看似乎也是民主自身演化過程中自然衰落的結果。在《童年的消逝》中,尼爾·波茲曼亦從大眾傳媒的角度闡釋了知識平民化的雙重作用:一方面,正是印刷術的普及使得人們可以自由地閱讀文字,對文字的閱讀豎立起了橫亙在“成年”與“童年”之間的智識界限,導致了“深刻與淺薄”的文化分野;另一方面,電視市場的興起又彌合了這種智識的界限,導致了成年世界的持續低齡化與淺薄化。基于這種由市場帶來的知識平民化的悖謬性,劉擎誠摯地表明了自己的困惑:“究竟什么樣的市場是好的、高雅的,什么樣的需求是低級的、粗鄙的,今天的知識人還能夠給出確切的答案嗎?”

而在陳嘉映看來,文化平民化的兩面性需要以更多維的智識結構去解決:簡言之,問題不在于如何讓更多的普通人成為智識人,而是讓“行動者”與“思想者”各司其職。依照陳嘉映對于“智識人”的定義,智識人是不參與社會物質生產的“思想者”,這意味著他們不需要“行動”,且擁有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處理浩瀚的信息系統。因而,“要求一個行動者,一個討生活的人,在生活之余維持高強度的思考,在表達之余還得‘好好說理’,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因為‘說理’并非他的本職工作”。相較于歷史上的其他時代,當代的智識人在數量與質量上也許都并未衰落,如劉擎所言,他們只是“比例被稀釋”了、“聲音被淹沒”了。而陳嘉映似乎更為悲觀,在他看來,“淹沒”與“缺席”并無二致,“被淹沒只不過是另一種不在場的方式”,在當前,讓思想者與行動者能夠各司其職的多維對話空間尚未被重建起來。
重建“知識話語”:放棄對“政治正確”的極端追求
在追溯當前大眾與精英關系緊張化的原因時,劉擎聲稱“智識的邊緣化一定程度上是知識人的‘內戰’造成的”。他援引德里達與福柯等人的后現代理論作為例證:在哲學的后現代轉向中,德里達對“羅格斯中心主義”的批判極大程度上摧毀了語言的權威地位,并向大眾闡明了語言說理系統自身的危險與欺騙性。而福柯對“知識話語”中所蘊含的權力結構的反思與披露,則進一步加劇了公眾對于“話語”本身的不信任。在60、7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內部論戰中,同樣有知識人站在了反精英的大眾立場上,認為“貝多芬的音樂和街頭巷尾的口哨并無區別”。劉擎進一步得出結論,認為“對知識共同體的破壞有時也是知識人自我招致的”。
然而,在福柯原語境的論述中,話語和權力的關系實則要復雜得多,陳嘉映指出,“話語和權力的視角,雖然能幫助我們看到某種真相,但這并不意味著話語就全然依靠權力,它所創造的就只有權力。”陳嘉映指出,這些武斷的判斷皆是政治立場的表達,而非政治立場的交流。
在美國當前的公共生活中,此類非此即彼的“立場表達”則更為普遍,“不管什么樣的表達最后都會演變成‘yes or no’的立場站隊。”卡爾·斯密特曾聲稱,“政治的本質就是區分敵我”,然而陳嘉映認為,“施密特的確是處理危機時刻的專家,但我們并不總是處于一個必須區分敵我的危機時刻。”陳嘉映坦言,自己對于當前輿論中普遍存在的極端的“政治正確”傾向并不認同,亦對當前“表達”的高度政治化與高度緊張倍感憂慮:“彷佛我們每一時、每一刻都處在一個生死攸關的當下”,然而,“過度的政治化將使政治失去其原初的意義。”
在對談的尾聲,陳嘉映試圖從古希臘先賢埃斯庫羅斯的早期劇作中探尋出路,并提出,我們應當從雅典城邦的民主進程中汲取經驗,嘗試從一個追求“原始正義”的時代,進入“擺脫原始正義”的時期,從而成為一個“話語的城邦”。陳嘉映認為,在非此即彼的立場之外,還應當留有一些中立的空間,讓智識的“話語”于松弛之中重新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