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互聯網指北
可能王濛自己也很難判斷,自己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到底是當年溫哥華冬奧會成為史無前例“三冠王”的那一刻,還是坐上咪咕體育解說席的十二年后。畢竟榮譽感雖然是競技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事業的價值總是需要真金白銀來打底。很顯然“解說員王濛”比“運動員王濛”更容易實現這一切。
在北京冬奧會期間,王濛依靠解說冬奧會期間犀利的點評風格連續登上7次熱搜,成為2022年最受矚目的“流量大戶”之一,其中她的金句“我的眼睛就是尺”更是獲得了“商業化價值”,咪咕將其打造為IP推出了“標尺系列手辦”,定價99元起。

而且從“解說員”的職業角度出發,王濛顯得天賦異稟:
她擁有鮮明的運動荷爾蒙,情緒飽滿且鮮明,能夠輕易擊穿社交網絡時代的注意力壁壘,冰雪運動骨子里的高門檻又讓她“直言不諱”“不假思索”的語言風格,在距離感的保護下成為觀眾眼中的優點。
比如2000米混合接力決賽中武大靖以毫厘優勢取勝,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結果的時候,只有王濛斬釘截鐵地說,“歡呼吧朋友們!就算只有微弱的優勢,那也是我們贏了”。她的搭檔的黃健翔就沒太看明白,一度試圖在旁邊留“中國隊沒贏”的余地“啊……那個意大利選手好像……”
要知道黃健翔才是真正的“解說圈屠龍少年”。當年那句著名的“意大利萬歲”不僅把2006年世界杯喊出了圈,讓格羅索毫無疑問地成為了“偉大的左后衛”,更是一嗓子把自己的工作“喊出了體制外”,從此央視少了一個解說名嘴,娛樂圈多了一位“跨圈紅人”。
于是有網友感嘆,這真是第一次聽到黃健翔也有“唯唯諾諾輕聲細語沒地兒插嘴的時候”。
據說還有相當一部分冬奧觀眾,養成了“追著解說看比賽”的習慣。他們開始研究咪咕的轉播安排,按照排班表來決定自己的觀看時間,然后形成整齊劃一的熱度,幫助王濛和黃健翔的“拍案組合”周期性地登上熱搜——這可是連“解說文化”最悠久的足籃球項目,都很難做到的這一點——楊毅和詹俊帶給比賽的額外關注度,說不定還沒有美娜和馬凡舒多。
所以可以想象的是,有了王濛和咪咕打樣在前,在2022這個擁有奧運、亞運、大運、世界杯的公認“體育大年”里,“解說”一定會被中文互聯網世界分配更到的關注度權重,解說員們也將頻繁地從“體育圈”里走出來,在其他領域兌現著自己的“經濟學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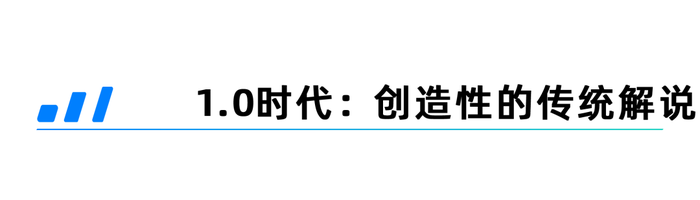
中國體育解說的開端顯得有些倉促,一方面是因為中國體育形成“產業”的時間非常晚,另一方面是因為“解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不是一門基于興趣自由選擇的“職業”。
時間回到1950年,蘇聯男子籃球隊到上海訪問,準備與中國隊進行一場友誼賽,比賽地點確定在當時最大的、能夠容納4000余人的盧灣體育館。
但這還是太小了。無論是對于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支來訪的外國球隊,對于中國龐大的體育愛好者群體,盧灣體育場能夠帶來的“影響力”顯得非常有限。于是就有觀眾給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打電話提出建議,“播音員看著比賽也可以廣播介紹嘛!”
而這個提議就成為了“新中國體育解說事業”的開端,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決定轉播這場比賽,并找到了在1949年國慶大游行中進行實況解說的播音員張之和電影演員陳述搭檔進行賽事解說。
按照現在的說法,那場比賽的解說形式,應該會被定義為1.0版本的“場景式描述”。
解說中,陳述負責描繪場上的氣氛,張之則運用評書的語言,把突破上籃說成“單槍匹馬殺入重圍”,勾手上籃是“回頭望月”,比分的焦灼獲得的形容則是“犬牙交錯”。這場臨時安排的解說,打開了中國體育解說的大門,而“兼職跨行”的張之,則成為了中國體育解說的“開山鼻祖”。
1953年,張之加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專門從事體育新聞報道和體育比賽實況轉播的解說工作。由于當時缺乏對于“解說”職業技能的系統性總結,張之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試著總結出一套“自己的辦法”來更好地完成工作。比如大量借鑒古典文學名著,去定義體育賽場上那些不好形容的局面——“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這是形容足球門將的嚴密防守;“黑云壓城城欲摧”,這是形容一方圍攻另一方危急場面。
同時,他還會借鑒古典小說的描述手法,比如對中國第一代足球運動員在比賽中的場面這樣形容——“中鋒史萬春用越過對方頭頂的妙傳,把球送到禁區空擋,左邊鋒叢者余單刀直入飛步趕上抬腿猛射,球像炮彈出膛,對方守門員來不及補救,球已經飛進網窩。”
這些詞語,我們現在仍然能夠在NBA每日五佳球或者《天下足球》每周最佳進球的解說詞中聽見。
到1961年北京舉行第26屆世乒賽時,張之的解說達到了他的生涯巔峰:他一共解說了八場,在徐寅生著名的“二十八板”時,張之每數一板,現場觀眾就尖叫一次,收音機前的聽眾也總會跟著把心揪緊。
就是帶著這種“既富有傳統色彩又富有創造性”的解說經驗,張之培養出了一位“中國體育解說總統山”。
1961年,和張之一起解說世乒賽的,還有剛加入央視不久的宋世雄,后者見證了中國電視體育史的所有經典記憶。1978年,央視第一次轉播世界杯,宋世雄的解說、肯佩斯的長發以及糖果盒球場漫天飛舞的紙片,成為了中國球迷對于世界杯的最初印象;1981年女排世界杯,中國女排首奪冠軍,宋世雄負責了中國女排五連冠賽事的全部解說;他的巔峰之作,則是在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時,一個人承擔了全部26場比賽的實況轉播解說。

其實用今天的標準回看當年的體育解說風格,宋世雄一定是拿不了高分的。“A傳給B,B傳給C,C打門,球高出了橫梁”這種白描式的語言信息增量太少,一旦遇到場面平淡的比賽很容易讓人昏昏欲睡。
但考慮到當時的轉播條件限制,以及體育賽事規則的普及程度,很顯然“準確、讓人聽得明白”比“情緒飽滿”更重要,只有這種平淡無聊的“連珠炮派解說”才能跨越農村與城市、學校與工廠之間的界限,讓體育比賽成為了國民的底層社交語言。
1989年春晚小品《懶漢相親》里,雷恪生扮演的“農村窮光蛋”就幻想著依靠一臺能看“宋世雄轉播”的電視討媳婦。

等到人們鼓起勇氣,嘗試“打破”這種解說方式,時間都已經來到了1990年。意大利之夏,央視開始直播所有場次的世界杯比賽,六年前剛剛入職的韓喬生開始嶄露頭角,成為了下一個伴隨比賽的標志性聲音。
韓喬生身上仍然能看見張之、宋世雄的老派,但他肯定有更向往“自由發揮”的一面,并隱藏在他“一本正經胡說八道式”的解說風格中。有網友親切地將其總結為“有煽情、有故事、有沖突,但就是沒有技術”“韓老師本不想成為可笑的人,沒想到在解說界有心栽花,在搞笑界無意插柳”。
比如他會擔心“可能有的觀眾剛剛打開電梯,我們再把比分播報一下……”,也會在中秋節給觀眾朋友們拜個晚年,也會說那是“30公里外一腳遠射”,或是 "中國隊一腳射門,被區楚良奮勇撲出"。
有球迷總結了一條韓喬生定律:眼睛看著球員A,腦子里想起球員B,嘴里說著球員C,實際指的是球員D,觀眾還以為是球員E。

(“全員夏普”)
當然直到此時,人們還沒有太多“誰才是中國最好的足球解說員”或是“你怎么評價昨晚XXX的解說”的概念。畢竟“解說員”這個職業逐漸走入“前臺”,需要的不僅僅是電視轉播技術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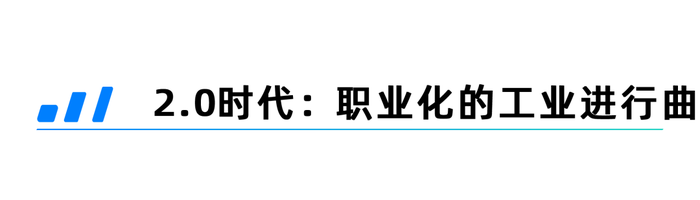
套用一句俗話,中國體育解說的第一個三十年,是“野蠻生長”的。在這個階段,解說員多是播音、新聞、語言文學專業的人來客串,所以無論是張之、宋世雄還是韓喬生,都只是致力于將他們看到的比賽實況說出來,區別可能僅在于:精確和更精確,生動和更生動。
宋世雄在多年后和媒體的交談中也絲毫未避諱那個時代的局限性,“拿我自己來說,過去觀眾給我提意見,說轉播有時啰唆,廢話多,我覺得他們講的有道理,因為我們當時手頭沒有足夠的信息,就那么可憐的一點,而時間又很長,你也總不能‘空白’太多,或車轱轆話來回說,所以翻來覆去得只有炒冷飯,觀眾不煩才怪呢。”
帶動國內解說事業升級的,實際上是賽事包裝的率先升級,從國外傳來的“解說+專業選手”的雙解說模式開始影響中國體育解說領域。這種解說模式的特點是對比賽的規則、策略、技術、參賽隊員等都很熟悉,能夠從專業角度對比賽的精彩之處做出點評,從而更好地將普通觀眾轉化為“核心觀眾”,使其更有動力全面地參與到賽事經濟當中。
1991年,央視轉播意甲聯賽,同時開始嘗試AB角(解說主持+解說嘉賓)的搭配。在這場解說革新中,畢業于北京體育大學運動系足球班,曾經短暫擔任北京隊門將的張路出現了,作為評球嘉賓,張路開啟了自己的解說生涯。他延續著上一代解說員“隨意發揮”的特色,但依靠專業知識,他能夠迅速洞悉比賽中陣型、戰術的變化,然后轉化為帶著濃厚京腔的大白話,直接點出球員的問題,這種專業解說模式,讓球迷的足球素養得到了快速提升。
張路粗略估算過從“球盲”到“懂球帝”的過程,大概需要觀看三千場比賽,“到三千場的時候,可以有一些預判了,一場比賽打了十分鐘,要點在什么地方,我就大概能知道了,有什么發展,我也大概能預計到了。”
在知乎一條關于張路的提問下,有網友的回答是:張指導當年說意甲的時候演示了一遍下底傳中是怎么回事,愣是把我那個球盲母上給講明白了。
同樣是運動員出身的前男籃國手張衛平,也走了“張路”相同的路——專業且通俗,又從不避諱自己的喜好,因此被球迷冠以”衛平·布萊恩特“的外號,認定他是湖人的鐵桿球迷,是科比頭號鐵粉,在推崇中立的解說界里硬是走出了一條別樣的路子。
在他的解說中,不管評論誰最后都會用“科比”來總結升華:當費舍爾拿球——“嚯,這球不合理,應該傳給科比·····嚯,費舍爾還真敢投,還真不進,嘿嘿。”當科比拿球——“科比投了!好球啊!哎呀,沒進。雖然沒進,但是戰術打出來了,這種球很合理,湖人就得這么打下去。”
之后,游泳世界冠軍周雅菲、羅雪娟,前體操國手楊云,國足唯一世界足球先生候選人宮磊,能夠接連成為了央視固定的體育解說嘉賓,可以說吃到的都是張路、張衛平二位張指導的紅利。
市場經濟的逐漸開放貢獻了國內體育解說改革的另一個浪潮。1994年,ESPN進軍亞洲市場,依托華南地區悠久的“說波文化”(粵語里的說球)開展英超聯賽轉播業務,廣東體育等地方頻道紛紛購買版權,帶動了丁偉杰、何輝、江忠德、蘇東、詹俊等一批職業解說員全面崛起。
ESPN把國外體育解說經驗移植到國內解說員身上,為解說員定制了一系列量化的KPI,比如“轉播畫面不能出現超過10秒的解說空白期”“當電視鏡頭對準一個人30秒,你卻不能告訴觀眾為什么攝像機會如此關注他,那就算重大失誤”,蘇東對當時的回憶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整體來說,可能也就是我們幾個人這些年下來,組合起來形成了一種所謂的ESPN解說風格”。再配合上英超冠絕全球的賽事包裝水平,中國觀眾也第一次感受到“體育娛樂化”的魅力。
直到現在,英超轉播還有普粵英三語選項,很多香港足球解說的“俚語”,比如世界波,窩利射球,插花腳,已經成為了球迷群體的日常用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稱為“人腦數據庫”的詹俊。他能很快告訴你禁區混戰中是哪個球員先碰到了球,甚至那個球員僅僅露出了半個背影,也幾乎不會說錯他的名字和球衣號碼,接著他還會告訴你這是這個球員本賽季進的第幾個球、第幾個左腳進球、連續第幾個賽季在這個球場取得進球等等。
這是非常被EPSN需要的能力,在英超比賽直播中,導播經常把鏡頭定格到場外的某個細節,那可能是球隊老板、英格蘭主帥或者綠洲樂隊的主唱。很多人稱贊詹俊的解說中有很多典故,能夠一眼認出場外的人物,最經典的橋段是“坐在溫格旁邊的是奧克斯,他是阿森納隊的隊衣管理員,同時也是阿森納女隊的主教練,而且兼任阿森納隊的大巴司機。”
但隨著詹俊認可度越來越高,觀眾心中“解說員”的基本功課也越來越多:普通話標準、傳達準確、不能有明顯的主隊傾向、要做充足的賽前工作(包括且不限于球隊數據、球隊歷史、球員數據、球隊歷史)、能做到同期同聲翻譯……
用比較流行的話來說,這個能力有些“太卷了”,能卷到同行也能卷到自己。就像當年“ctmd本特克”事件,逐漸從“解說員”向“明星解說員”進化的詹俊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質疑論據毫無例外地都來自于所謂的“解說員基本功”。

開頭提到的黃健翔也一度給人們帶來過這種疑問:到底什么才是解說員應該具備的基本功?
作為央視體育解說風格轉變的代表人物,黃健翔有著當時最受歡迎的風格,富有激情、語言感染力強、內容功底深厚。但在解說2006年德國世界杯時,黃健翔失控了,在那場意大利對陣澳大利亞的八分之一決賽的末尾,黃健翔把一個球迷的激情體現得淋漓盡致,并且給整個體育界,或者說整個中國,留下了一段著名的咆哮——
“……格羅索立功了,格羅索立功了!不給澳大利亞隊任何的機會。偉大的意大利的左后衛!他繼承了意大利的光榮的傳統。法切蒂、卡布里尼、馬爾蒂尼在這一刻靈魂附體,格羅索一個人他代表了意大利足球悠久的歷史和傳統,這一刻他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不是一個人……”
那場解說掀起了公眾輿論層面,第一次關于圍繞著體育解說展開的大討論,報紙、電視臺、網站、論壇圍繞著“體育解說的專業素養”進行了無數次的辯論,各大媒體多次深入田間地頭進行輿情統計,結果顯示“保黃派”和“倒黃派”數量不相上下。但無論如何,黃健翔因為解說門事件匆匆結束了自己在央視的解說生涯,接下來的劉建宏和段暄卻似乎都沒有足夠的實力去扮演主角。

直到從《挑戰主持人》出道,將黃健翔視作老師的賀煒出現,這個爭論似乎還有了新的答案。
與黃健翔的外放不同的是,賀煒含蓄而深沉的解說風格似乎更加有觀眾緣。韓喬生曾經評價他,“賀煒讓體育解說進入到全新的境界,這是種靠實力和內涵功底的解說,賀煒稱得上同年齡最優秀的解說員。”
在賀煒的百度詞條介紹中,他的別名是“足球詩人”,他也確實給許多球迷留下了可以反復回味的解說詞——南非世界杯1/8決賽,德國對英格蘭的大戰結束后,他說,“勝負既分,結局也已經確定了,英格蘭和德國永恒的對抗在世界杯歷史上繼續延續下去······在今天晚上,電視機前的億萬球迷能夠一起來經歷、共同分享,這是我的幸福,也是大家的幸福。”
有觀眾這樣總結過賀煒的解說:除了在比賽中某一個節點上評價戰術、成績、球員,每一個球員的足球人生,每一種戰術的發展脈絡,每一個球隊的興衰沉浮都是一部故事·······賀煒喜歡把這些賽場內外的故事,投射為人生的隱喻,足球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僅豐富你的生活,足球一樣教會你如何生活。

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體育解說基本已經完成了從1.0到2.0的躍升。完整的賽事轉播培養了一批批風格各異的解說員,無論是單口解說還是主持搭配嘉賓的雙人模式,無論是專業主持人還是運動員轉型,無論是央視的盡量客觀中立還是地方臺明顯的地域袒護,體育解說走到那時,已經沒有了絕對的風格與規矩,觀眾們各取所需,在遙控器里調換著自己的時代記憶。
等到移動互聯網內容載體的崛起,PPTV、騰訊、新浪等大內容平臺開始搶占賽事版權,天生具有移動優勢的網絡平臺漸漸取代電視,成為體育賽事轉播的主流平臺,也隨之帶來了更加龐大的解說員隊伍。
幾乎包攬了國內外各級足球聯賽的PP體育招徠了曾經供職于傳統媒體的張路、黃健翔、詹俊、蘇東等一批老資歷名嘴,買斷NBA版權的騰訊則聚攏了籃球媒體人出身的蘇群、楊毅、王猛,以及近兩年異軍突起的咪咕視頻,更是憑借東京奧運會和北京冬奧會的解說搭配強勢刷屏。除此之外,各家平臺也在致力于搭建自己的解說員團隊,并且開發了相應的IP節目,比如騰訊的《有球并應》和PP體育的《足球解說大會》。
相比電視媒體,網絡平臺的解說會顯得更加隨性一些。王猛會在一顆超遠三分進網之后狂呼“厲害炸了”,也能聽見“道歉之王”于嘉在直播中經常“啊對不起,剛才犯規的是XX而不是XX”,以及讓裁判把錄像再看十遍的王濛由于激動在解說間站著講完了整場比賽。

隨著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體育解說已經逐漸成為了各自領域內的KOL,走出虎撲、懂球帝這些垂直社區,也在B站、快手、抖音成為流量擔當,關于哪個解說更好的討論永遠有新的更貼,像“徐靜雨”這樣深諳互聯網思維的體育解說開始走紅,得到和楊毅同處一個直播間的機會,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革新。
而他們獨特的口頭禪就像鬼畜視頻一樣,幾乎被每一個球迷熟知,“聽說他今年夏天特意加練了罰球?”一開口就是老NBA2K了。
被互聯網語境重新定義了的觀眾們,則開始經常詬病以央視為代表的傳統體育解說:黃子忠喜歡四字四字地蹦成語、童可欣的解說總讓你懷疑她支持的是中國隊的對手、洪鋼居然會夸贊王夢潔這樣的自由人是中國女排第一個現代自由人、陳瀅亂用詩句點評花滑……
當去年咪咕視頻打破轉播壟斷,獲得奧運會轉播權并且設置了多條解說線路,大家好像終于可以實現“解說員自由”,而不是不得不看的“我們知道你不是在炫技,而是在為平衡付出巨大努力”這種劣質雙押的尷尬煽情解說了。
很大程度上,直到此時“體育解說”才終于找到了它最科學的定位:作為賽事包裝中的重要一環,“體育解說”本質上是一個系數,它無法決定賽事本身,只能放大賽事本身的特點——而解說員決定了這個系數的大小,決定了去乘以賽事的哪一部分。
換句話說,大視頻平臺的賽事解說開啟了一種新的解說形式,更適合那些平時并不關注聯賽、錦標賽、單項賽,只想在四年一次的人類大狂歡中湊個熱鬧的觀眾,或者本身就不具備商業化運營可能的冷門項目。
當然最近紅火的電競解說除外。
作為一項沿著競技體育邏輯實現正規化的產業,電競產業用了十幾年就走到了傳統體育產業半個多世紀的高度,這一方面可以意味著電競產業擁有足夠的成本去幫助人才成長,也意味著產業發展規模與產業實際基礎并不匹配,大量市場空缺是通過“趕鴨子”上架來完成的。而“電競解說”就是所謂的“產業基礎”之一。
于是現狀就是,現在的電競解說員主要還是來自退役選手或者網紅來“兼職”,比如中國電競解說元老之一的Alone就曾是SVS戰隊的職業選手,虎妞的更常見身份是LGD的教練。高校、職高雖然也在近年來陸續開設了“電競專業”,其中就包括“電競解說過程”,但從目前看來似乎并沒有現有的賽事運營方建立起人才通道。
在大版權時代,電競產業蓬勃的表達欲,基本只剩下了兩條路,要么成為解說獨立游戲視頻的UP主,要么在那些“你知我知以為別人都不知”的平臺“偷偷解說”。但隨著大版權時代的來臨,高聳的制作成本,讓前者越來越富有PUGC色彩,開始成為媒體團隊的專屬;而后者太容易帶有灰產色彩——就像因為烏克蘭因素而停播的英超聯賽,國內觀眾只有通過“菠菜網站”提供的資源進行觀看,還得面臨每次分鐘一次的“購彩推銷”。
電競解說沒有新鮮事,實際上走的是“傳統體育解說”的老路,上面發生的那些故事大概率會在電競產業的路上再發生一遍,只不過在互聯網的包裝下來得更快、更裂變。
而對于日趨龐大的體育消費者群體來說,“解說”是體育消費場景中最重要的一環已經成為了共識,僅僅只有畫面的比賽不一定是一場完整的比賽。而對于日趨正規化的“解說員”職業來說,“解說”的使命也不再是簡單地“傳達”場面信息,而是作為渠道幫助觀眾真正地進入“項目”內讓他們成為“核心用戶”。
很多年之后,你或許不記得自己曾經看過哪些比賽,但在那些”大心臟“時刻,一定有一些聲音會幫自己找到共鳴。無論是宋世雄的嚴肅、張衛平的“京味兒”,詹俊的妙語連珠還是賀煒詩意的陳述,都曾經成為那個重要的瞬間,而許多賽事也因此被更多人銘記,就像在克萊·湯普森因傷休賽了接近三年再次復出時,咪咕視頻的解說連睿說了這樣一段話——
“941天,這世界發生了很多的改變,有的人從高中走進了大學校園,有的人從大學步入了成人世界……但這個世界,在這941天沒有變。不變的是執著,不變的是信念……克萊·湯普森,歡迎你回來。這個世界沒有改變,你還是你,我們還是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