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仙人們和精靈中更純潔的那些就住在那里,用風中搖擺的蘆葦的嘆息,用鳥兒的歌唱,波浪的呻吟,用小提琴柔情的泣聲,哀悼我們隕落的世界。
葉芝在代表作《凱爾特的薄暮》里塑造了飄渺有靈、自然脫俗的愛爾蘭美學,至今仍影響著大眾文化對愛爾蘭的想象——在游戲《魔獸世界》中,角色“德魯伊”能運用自然力量來維護平衡、保護生命;托爾金筆下的《魔戒》借愛爾蘭傳說構造了精靈族的形象,優雅輕盈,棲居森林。
除了葉芝,經典文學的書架上還有其他許多愛爾蘭作家的身影,喬伊斯、貝克特、科爾姆·托賓……頗受市場青睞的新生代作家薩莉·魯尼也來自愛爾蘭,她的書寫關乎城市、物欲、階級地位,與葉芝筆下樹蔭郁郁、精靈游走的舊世界相隔甚遠。“我討厭葉芝!” 她曾向媒體這樣說道。從愛爾蘭文學里探尋出一條連貫的線索,是否只是一廂情愿的妄圖?畢竟托爾金在牛津大學就職典禮上談到愛爾蘭文化時說過:“凱爾特這個詞就像是一個有魔法的袋子,你什么都能往里面塞,可是它自己什么也不會提供。”
在日前舉行的《雪嶺逐鹿:愛爾蘭傳奇》新書發布會上,本書作者、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助理教授邱方哲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戴從容、復旦大學英文系副教授包慧怡從愛爾蘭傳說出發,探討了“凱爾特文化”與“愛爾蘭性”是如何被民間故事文集塑造的,以及我們能否在從喬伊斯到薩莉·魯尼的愛爾蘭作家中尋到延續的母題。

邱方哲 著
胭+硯|漓江出版社 2022-1
在純粹的“愛爾蘭性”之外看到多種文化的碰撞

在代表作《凱爾特的薄暮》里,葉芝采集和整理了愛爾蘭民間神話傳說。這本書的野心不只是文學的,也是政治的,葉芝是“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的領袖人物,這場發軔于19世紀末、綿延至20世紀20年代的文化運動,與愛爾蘭政治上的民族獨立運動相呼應,力求證明愛爾蘭文化根植于威爾士、高盧同源的凱爾特文化,與希臘羅馬文明以及當時的英國、法國文化截然不同,為塑造“愛爾蘭民族”提供依據。作家們在這一時期致力創作去英國化的,符合愛爾蘭文化精神的作品。
葉芝認為,古代與民間故事可以作為文化資源,用文學“為愛爾蘭這塊軟蠟來塑形”。邱方哲指出,當前國內出版的大多數愛爾蘭傳奇,選材多受“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影響,往往刻意拋去基督教與拉丁語文化的因素,追求純粹的“愛爾蘭性”,但這些被選編的故事集“對愛爾蘭的呈現不夠全面,愛爾蘭并不僅僅意味著凱爾特薄暮式的精靈文化”。他說,“很難總結愛爾蘭古代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樣的文化,這像中國文化一樣。你讀到他們的傳奇故事會發現都是多種文化碰撞的結果,本土信仰、基督教的線性歷史觀、歐洲大陸和遠東的故事模版,也包括了英國入侵者帶來的影響,所有這些文化因素兼容并收才形成愛爾蘭的本土文化。”
邱方哲提到,“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中的作家試圖將愛爾蘭文化打造成同陽光與微風相關,“如同金發長袍女子緩緩走過林間的美感”。實際上,愛爾蘭民間傳說里有許多血腥粗俗的故事,比如古代愛爾蘭諸神的原野之戰描繪了殘暴戰爭場景、婚外情、野合以及血腥的大屠殺。比如《雪嶺逐鹿》收錄的《麥克達索之豬的故事》一篇里,主人公與人分食豬肉起了爭端,大開殺戒,直到“尸體堆成山,血從七道大門汨汨流出”;《伊娃獨子的隕落》描寫愛爾蘭最有名的英雄庫呼蘭為了獲得國王贊嘆,殺死親生兒子康勒的經過,“康勒身上流出的鮮血,在我手上一會兒就蒸發殆盡”、“他從水中一擊得手,腹矛沒入康勒肚中,再一扯,他的腸子流得滿地都是。”

隔絕的孤島與偏遠的鄉間也是對愛爾蘭的刻板印象之一。然而在許多傳奇故事中,愛爾蘭與城鎮和物質關聯密切,也是歐洲甚至遠東各國頻繁溝通往來之地。比如《蒙甘的身世》提到了國王與不列顛島上盟友的密切交往,《卡里爾之子圖安的故事》是不列顛的修士帶著福音書來愛爾蘭傳道的經過。邱方哲指出,中世紀愛爾蘭和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國家交集頻繁,愛爾蘭僧侶在歐洲很多地方辦了學校,也有很多國外學者前來進行學術交流。
愛爾蘭傳說也不只有輕盈飄渺、關注宇宙和精神的空靈文本,還包含許多批判時政、諷刺現實的故事。在嘲諷主教殘暴、國王無能的故事《麥康格林的畫像》里,一個窮書生諷刺主教施舍食物太少,主教以抹黑教會的名義抽打他,并與僧侶合計將他吊死,后來他來到被饕餮魔折磨的國王身邊,這位國王因胃口巨大使得王國生靈涂炭。
從喬伊斯到薩莉·魯尼,愛爾蘭式的文學母題存在嗎?
在中文世界,愛爾蘭文學最初是受到忽視的。戴從容回憶道,在20世紀90年代,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愛爾蘭文學與英國文學有什么不同,她博士答辯時還被質疑為何要將葉芝、王爾德等久在英國文學之列的作家特意劃到愛爾蘭作家的范疇。如今,愛爾蘭文學作為一個獨立門類已經被學界正視與尊重。
作為翻譯喬伊斯作品《芬尼根的守靈夜》的學者,戴從容認為,喬伊斯的寫作經歷了從愛爾蘭文化的出走到年老后的回歸。他年輕時恥于愛爾蘭落后的經濟、混亂的政治制度與矇昧的文化,在巴黎生活的二十年中,僅有兩次回鄉小住。在最早期的作品《都柏林人》里,喬伊斯寫下愛爾蘭精神的遲緩和麻木,《尤利西斯》全方面表現了都柏林的貧窮和枯燥,到了《芬尼根的守靈夜》,他回到了愛爾蘭文化傳統,收集了愛爾蘭傳奇里“特里絲丹和伊瑟的故事”、奧康納與圣帕特里克等人物的傳奇。戴從容推斷,喬伊斯一開始可能想寫愛爾蘭的史詩,后期決定把《芬尼根的守靈夜》發展成一部“世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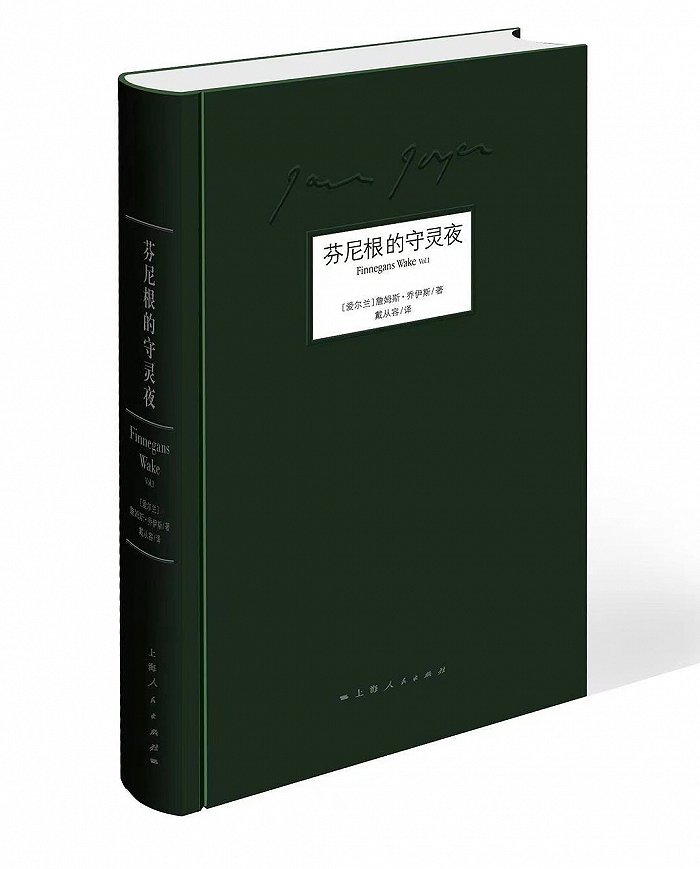
詹姆斯·喬伊斯 著 戴從容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
對包慧怡來說,島嶼經驗和世界經驗的雙向反芻是愛爾蘭文學的母題。許多愛爾蘭作家對故土島嶼愛恨交加,書寫之中鄉愁與鄉痛并在。喬伊斯面對愛爾蘭始終有一種被放逐感,然而他到哪里都隨身帶著愛爾蘭的民族之書《凱爾經》。他曾說,“這是我唯一不變的行李,《凱爾經》里繁復的動物圖像、被吞噬的藤蔓,就如同我《尤利西斯》里的一個章節。”托賓也在很多作品中處理了家園經驗,比如在《黑水燈塔船》以及《空蕩蕩的家》中大篇幅描寫故鄉恩尼斯科西的海灘與海浪,以及離開家鄉后看到的海同家鄉之海如何不一樣。在《空蕩蕩的家里》里,角色在陰暗的家鄉與空虛的他鄉之間游走:
“也許這正是我此刻身在此地的原因,離開愛爾蘭的黑暗,離開無情降臨在我出生地的漫漫嚴冬,離開東風。我處在一個到處空蕩蕩的地方,因為這里從來沒有被填滿過……”
故土情結放在薩莉·魯尼身上并不適用,包慧怡認為,魯尼對政治議題的關注、激進新潮的語言風格以及作品的影視改編,都讓她獲得了很多關注和曝光,試圖從她身上尋找愛爾蘭文學的脈絡和歷史卻找錯了地方。“薩莉·魯尼只是愛爾蘭文學很小的一塊拼圖,并且我相信她在未來要走得更遠更廣,一定會處理城市經驗、校園生活與愛情生活之外的東西。我也很警惕讓一個年輕作家去背負愛爾蘭文學傳統這樣過于沉重的負擔,”包慧怡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