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后廠青年
在「互聯網+傳統曲藝」這個行當里,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德云社。當傳統劇場還在禁止錄影時,德云社的劇場視頻已經在互聯網傳開,大家都知道有一個”黑胖子“叫郭德綱,他的搭檔叫于謙,愛好“抽煙喝酒燙頭”。
德云社雖然走紅,不過絕大多數傳統曲藝演員,因為對于互聯網不了解或不信任,依舊只靠極不穩定的線下演出的收入過活。
從小就癡迷相聲的馮喆,因為天賦欠佳沒能成為相聲演員,但他畢業后進了一家互聯網公司,做相聲評書頻道運營。他讓傳統曲藝演員試著和互聯網做朋友,并讓他們看到——憑借優質的內容,相聲評書演員真的能在互聯網賺到更多的錢。
而他推廣傳統曲藝的努力也得到了行業的認可,成為全國曲藝協會2018年入會年紀最小、以及唯一一位不從事表演的會員。
橫跳青年第二期,后廠青年帶你看看一個年輕人,如何曲線擁抱自己的夢想。
放學路上,打快板的高中生
遼寧鞍山,除了是鋼鐵之城,還是“ 曲藝評書之鄉”,走出過被譽為“評書三芳”的單田芳、劉蘭芳和張賀芳。整座城市的上空飄蕩著評書的聲音。
鞍山小伙馮喆對評書的喜愛源于一檔名為《空中書場》的節目。在還沒到上小學的年紀,他便纏著父親要買快板,舅舅糊弄著給他做了一根“簡易快板”,長板翻不上去,但能刮起響聲,馮喆就呱嗒著這根“快板”,成了“業余”相聲人。

馮喆兒時的照片,圖源/受訪者供圖
高一的元旦晚會,馮喆和另一個從小喜歡曲藝的同班同學搭檔,改編了一段郭德綱的文本,上臺演了一出相聲節目,在全校出了名。
高二開學,馮喆主動找到音樂老師,說想學快板,音樂老師就給他介紹了著名相聲演員蘇文茂的再傳弟子王安良。馮喆的父母都是和文藝不沾邊的工程師,他擔心父母覺得自己不務正業,就瞞著父母,跟王老師學打快板。
“一有空就約那個在晚會同臺表演的同學去實驗樓打快板”,因為怕被父母發現,馮喆抓緊一切時間練習,放學路上如果沒什么人,他就邊打快板邊練嘴皮,寒來暑往,每天如此,兩只手現在還有那時冬天打快板的凍傷印記。到了家門口,又會躲在樓下練半個鐘頭。
不過,即便滿腔熱情地刻苦練習,馮喆并沒能拜王安良為師。在傳統曲藝行業,拜師之前,學生要先達到一定的水平,然而用老師的話說,馮喆“不靈”——唱大鼓永遠找不到鼓點,唱太平歌詞也會變味,連入門的水平都達不到。
回憶起來那段時光,馮喆開玩笑說,“這錢白交了”。雖然吃不了表演這碗飯,但下課之后,馮喆吃了不少王老師的飯。飯局上,馮喆聽懂了相聲界的各種行話:春點、正的、清的、使扁家伙的······這在日后的工作派上了用場。

部分行話列示,資料源自/百度
大學畢業后,馮喆去喜馬拉雅做相聲戲曲編輯,在公司20個音頻品類中,相聲評書頻道收聽量倒數第四。
相聲評書演員,為何不敢擁抱互聯網?
傳統曲藝不是沒有擁抱過新的傳播形式。上世紀初,電臺開始放送戲曲。1949年之前,國民識字率低,有些電臺會請說書先生讀報紙、讀書,有了“有聲書”的雛形。
進入互聯網時代,電臺在音頻視頻的浪潮前稍顯式微,如何讓傳統曲藝擁抱互聯網成為了馮喆思考的問題。
在相聲行業,德云社較早實踐了“互聯網+”。當傳統劇場還在禁止錄影的時候,德云社的劇場視頻已經在互聯網傳開,大家都知道德云社有一個黑胖子叫郭德綱,他的搭檔叫于謙,愛好“抽煙喝酒燙頭”。
早在2009年, 德云社封箱演出便出現在了優酷上。2010年,讀高三的馮喆還偷偷溜去網吧,看完了整場直播。

德云社在優酷視頻的專區,圖源/德云社官方微博
看到德云社在互聯網中大放異彩,一些相聲評書演員紛紛效仿, 但很多人“因為不熟悉互聯網的商業規則,又缺乏版權意識,揣著平臺眼里的金子,卻把自己賣了個白菜價兒”。
馮喆遇到過一位相聲演員,以極低的價格和一家公司簽約了長達20年的協議,那家公司卻以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價格出售他的作品。
在和演員簽約的過程中,馮喆聽很多演員都說過類似的情況。“說白了就是遇到‘版權流氓’了”,馮喆說,這類公司里,法務是主要的營收部門,日常工作就是起訴各個平臺,讓平臺賠錢或花高價買他們低價簽來的作品,但不給獨家版權,只從中牟取暴利。更有甚者,會雇人把演員的作品偷偷上傳至平臺,然后起訴平臺侵權。
很多相聲評書演員礙于協議,并不敢起訴這些公司,怕得罪這幫人,波及到自己的作品。
除了被簽約的公司挖坑,很多觀眾也會在現場偷偷錄制音頻視頻,然后上傳到平臺,盜版現象猖獗。
入職后的第一個春節,馮喆在公司值班,遇到一個前后換了三十多個賬號的用戶,不斷改名上傳盜版內容。“下架了又上傳,再下架再上傳,像打游擊戰似的”。

馮喆珍藏的曲藝作品,圖源/受訪者供圖
時間一長,演員對互聯網平臺形成了不好的印象,自然不會接受其提出的合作邀請。
另一方面,即便是已經答應合作的演員,對馮喆提出的內容分成模式也持懷疑態度。2016年,內容付費模式剛剛在國內興起,演員們并不相信會有很多人為相聲評書付費。
但在馮喆看來,相聲評書的觀眾可以不通過演員外在的表達,單純通過聲音就能知道演員想要傳達什么意思,天然適合音頻平臺。帶著對“互聯網+相聲評書”的憧憬,馮喆試圖破除一個傳統行業對另一個新興行業的誤解,并讓它們成為朋友。
被拒多次,用誠意打動王玥波
為了讓頻道的影響力更大,需要簽下一個“角兒”。馮喆和同事列了一份清單,上面是幾十位有錄音資料流傳的四十歲左右的評書演員,同事們把錄音資料完整聽下來之后,一致認為王玥波的作品質量最高。
除了公司內部評估,馮喆同時讓其他評書演員推薦值得合作的大腕,他們也都提到了王玥波。
想要聯系到王玥波并不容易。王玥波很少用手機,也不輕易給別人聯系方式。馮喆前后找了幾十位演員當中間人,有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的、有全國曲協、北京曲協的,有合作的演員、甚至還有演出場館的經理......馮喆托他們帶話,表達想跟王玥波合作的意愿。
然而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馮喆得到的回復都是“不同意”、“不會合作”、“再等等”。
2017年3月,馮喆從上海調到了北京。在同年5月,一個溫度還不高的傍晚,馮喆接到一個演員的電話——“現在有個機會能見到玥波老師,你要不要過來?”馮喆立即拋下手里的事,打車到民族文化宮,因為堵車,等他趕到的時候,王玥波已經快要上臺表演了。
趁著幾分鐘間隙,在中間人的引薦下,馮喆和王玥波見上了第一面。他自我介紹后,“合作”二字剛說出口,王玥波就轉身上場繼續表演,并丟下一句,“我從來不跟你們這些平臺合作”。
王玥波表演期間,馮喆在后臺“忙活了起來”——和已經談成合作的演員聊未來內容規劃,并看后臺里還有誰能合作。演出結束后,王玥波迅速被其他評書演員圍住,馮喆沒能找到機會上前插話。
等所有演員都走了,王玥波的搭檔應寧招呼馮喆拍了一張合照。當時馮喆體型較胖,王玥波開玩笑地說了一句,“跟你比,我顯得很瘦哦”。馮喆回道,“那我常來見您”。合完照,王玥波沒有給馮喆攀談的機會,徑直離開了后臺。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馮喆工作外的時間,基本都用來“跟”王玥波。他自費看了十幾場王玥波的演出,散場后,在中間人的引見下,進后臺繼續“磨”王玥波。
馮喆了解到王玥波對盜版深惡痛絕,便告訴王玥波清空各個平臺盜版內容的方法,包括該給哪個賬號發郵件、郵件該怎么寫。他還主動提出,如果想告侵權,可以幫王玥波找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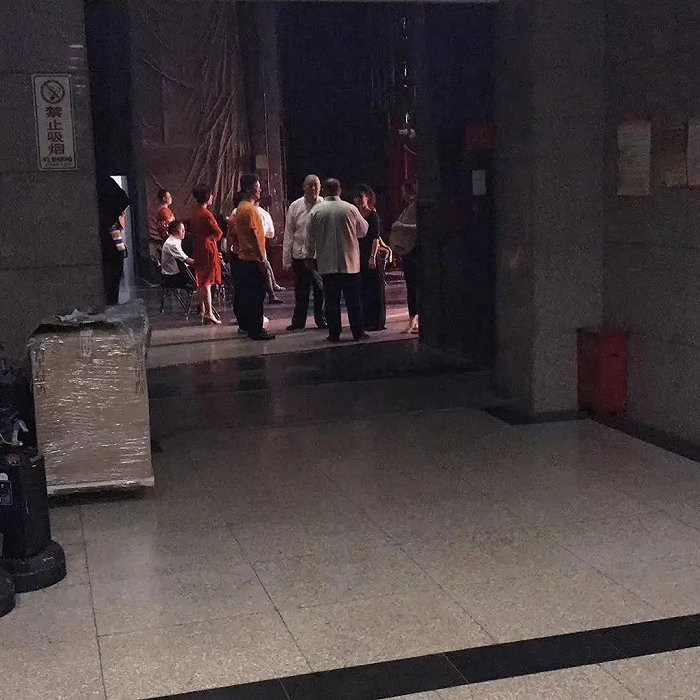
2017年5月30日,馮喆又一次來到后臺,圖源/受訪者供圖
不久之后的一天,凌晨兩點,馮喆接到了王玥波的微信電話:
“小馮,我這個內容誰都沒給過,我信任你,你要把這東西用好”。
掛完電話,馮喆松了一口氣,來不及興奮,立即將王玥波表示同意合作的微信消息截圖發給了領導。第二天一早,他就給法務總監打電話,“以最快的速度擬出合同”。
馮喆原本想把合同郵寄給王玥波,但王玥波執意要來公司現場簽。簽合同時,馮喆準備給王玥波詳細解釋合同條款,王玥波說,“不用解釋,我相信你,直接簽吧”。

簽約當天,王玥波來到喜馬拉雅,圖源/受訪者供圖
后來馮喆和別的演員聊合作時,別人讓他列幾個已經簽約的例子,聽到王玥波的名字,他們都會驚訝——他都跟你們合作了?繼而合作、簽約便順利了很多。
幫忙賺到錢,破格進曲協
跟演員談成合作只是第一步,傳統藝術和新渠道的磨合并不容易。為了拉近和相聲評書演員們的心理距離,92年的馮喆日常穿中山裝上班,偶爾也穿一身中式對開襟的褂子,右手揉兩個核桃,左手盤個串,桌上沏著一壺茶,把自己打扮成“業內人”的樣子。
然而因為思維方式的差異,運營和演員時常會有分歧。
比如運營為了讓用戶更有點擊的欲望,通常會幫演員上傳的作品重新取標題。但有的演員無法接受,認為講什么事就得是什么事,不能用別的話包裝。馮喆曾經幫一位評書演員取標題到凌晨四點,因為不符合對仗的句式,被訓「文學素養不夠」。
讓馮喆印象深刻的一個合作例子是陜西的相聲社團青曲社。為了更好地了解互聯網思維,青曲社主動提出派兩個人,從西安到北京,跟著馮喆學習如何運營頻道。不僅如此,馮喆還讓青曲社的演員在平臺上開通自己的賬號,建立個人IP。
在相互學習、磨合的過程中,一些相聲評書演員及社團確實在互聯網賺到了錢。
馮喆了解到,在和互聯網平臺合作之前,相聲評書行業的收入基本來自線下演出。“這場能賣出40張票,下一場可能一張都賣不出去”,整個行業的收入普遍不穩定。
而有了互聯網的加持之后,相聲評書演員的收入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有位S級演員,經過三年的時間,稅后總體收入達到七位數,年均增長五倍,這個數字還在往上漲”,馮喆說,腰部演員單月的線上收入也從幾十塊漲到了幾千塊,一兩萬的也有不少。
線上的作品受歡迎,線下的演出也會跟著火起來。“有些演員,以前專程來看他線下演出的粉絲很少,現在票都不夠賣,上座率提升了兩三倍。“馮喆舉例道,之前合作的一個演員,每個月線下演出的收益只有兩三千塊,現在月收入接近原來的十倍。
而尾部演員的作品雖然不如頭部、腰部演員受歡迎,一年也能有穩定的幾萬塊線上流水。

嘻哈包袱鋪深圳專場,圖源/高曉攀微博
馮喆推廣傳統曲藝的努力也得到了行業的認可。2018年,遼寧省曲藝家協會破格吸納他為會員,并保薦他進入全國曲藝家協會,成為當年入會年紀最小、以及唯一一位不從事表演的會員。
那個當初被相聲啟蒙老師認為“不靈”的小伙,用他自己的方式發揮了對相聲行業的熱愛。

馮喆在脈脈上記錄自己的工作感想,圖源/脈脈APP
2019年6月,馮喆想把職業道路走寬一點,離開了喜馬拉雅,彼時相聲評書板塊的日活躍用戶數已經從倒數第四升至第二。不過馮喆和相聲評書的緣分并未就此變淡,很多相聲評書演員在和互聯網平臺合作前,都會習慣性地給馮喆打電話——
“小馮,你幫我看看靠譜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