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期主持人 | 林子人
春節假期的時候我讀完了《女孩們的地下戰爭》。這本書講述的是一個廣泛存在但在很長一段時間缺乏關注的問題:女孩之間的霸凌。首先要澄清一點:女孩的霸凌行為和男孩的霸凌行為存在很大的不同,后者通常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打架斗毆、言語沖突(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所了解的霸凌形式),但前者往往是“隱性”的,表面上看女孩之間風平浪靜,但背地里會展開“隱性攻擊”,具體表現包括說閑話、傳謠言、排斥、辱罵、冷暴力、操控等方式,引發受害者的心理痛苦。《女孩們的地下戰爭》作者蕾切爾·西蒙斯在美國中小學展開長期調研后發現,霸凌行為在10-14歲的女孩中最盛行,與通常欺負泛泛之交或陌生人的男孩不同,女孩攻擊的對象往往來自親密的朋友圈:
“在女性友誼親密無間的背后,隱藏著一片彌漫著憤怒的秘密土地,而滋養這片土地的,正是沉默。”
西蒙斯認為,“女孩們的地下戰爭”有其深層次的社會原因。長久以來,女性都是依靠與他人的社交關系來加強社會地位的,強加在她們身上的是“與人為善”“以他人為中心”的性別范式。所謂的女性之間的敵對與惡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女性不被鼓勵直接表達負面情緒、正面應對沖突,于是在潛移默化間習得上述性別范式的部分女孩,轉向了以摧毀對方社交關系為目的的另類攻擊方式。在西蒙斯看來,“如果競爭和渴望不能通過健康的途徑表達,如果要求女孩將照顧他人擺在首位,怨恨、困惑和報復就會緊隨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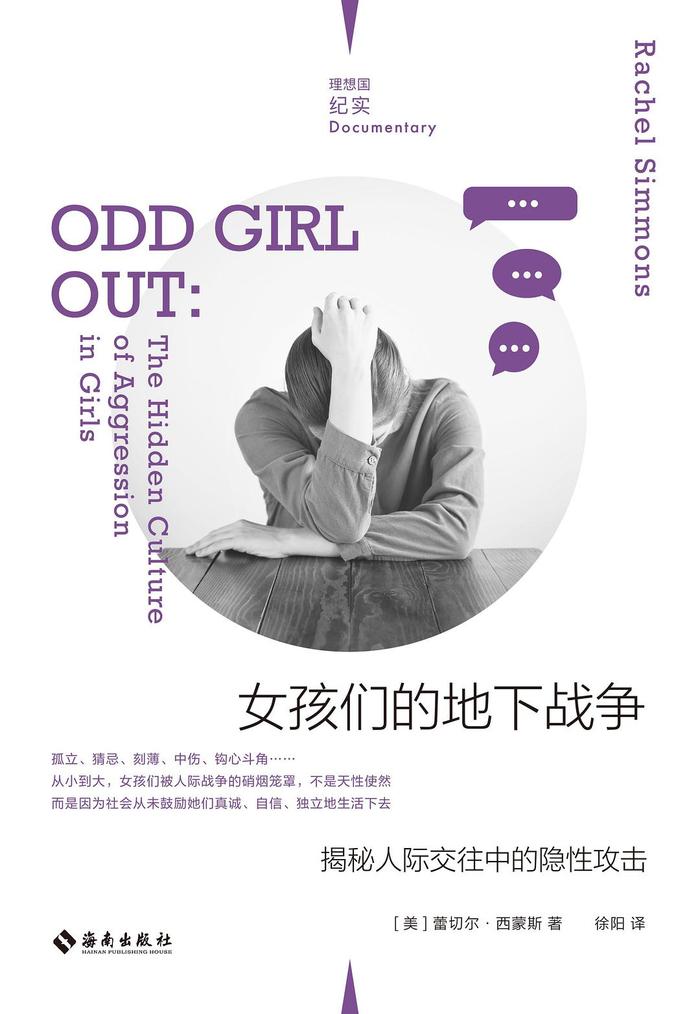
[美]蕾切爾·西蒙斯 著 徐陽 譯
理想國 | 海南出版社 2021-11
女性之間的刻薄行為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女生本就如此”或“塑料姐妹情實錘”,但這本書提醒我們,我們對女性精神世界狀況的了解和公開討論是多么不足。這些年我們也陸陸續續在反思流行文化為何熱衷于呈現女性之間的“扯頭花”,為文學和影視作品中開始出現真摯的女性情誼而歡欣鼓舞,為越來越多強大自信的女性榜樣歡呼雀躍。但我們或許還需要看到,在社會和文化意義上的性別平等仍未完全實現的當下,扭曲女性自我和同性友誼的土壤依然深厚——即使是在強調個人主義、獨立自主的美國,女孩子們依然要在“甜美友善合群”的性別規范下壓抑自我。
01 成長過程中那些讓我們不適、痛苦的同性友誼

林子人:《女孩們的地下戰爭》勾起了很多我的回憶。我首先想到的是小學時班里有兩位成績最好、人氣最高的女生,其中一位女生的媽媽剛好是我們班的班主任,在許多女同學看來,這給了她許多“特權”(比如評獎評優)和“打壓”另外一位女生的手段。于是幾乎全班女同學都圍繞著她們倆劃分成了兩大陣營,暗自較勁別苗頭。我雖然不在那兩位酷女孩的社交核心圈里,但相比之下和那位“被打壓”的女生關系更好一些。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班主任女兒陣營”的一位核心成員在課間沖過來譏諷我長相奇怪,說罷揚長而去,留下我和我的朋友面面相覷。
這樣的社交攻擊尚且可以一笑置之,真正讓我感到痛苦的是初中和大學我都有過被女同學單方面斷交的經歷。那是一種現在回想起來都錐心的痛苦——你曾經以為是親密好友的人突然不再和你說話,在社交網絡上把你拉黑,但你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仿佛你的身邊突然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吸走積極、快樂等所有正面的情感。正如西蒙斯所描述的,被社交攻擊的女孩在一無所知又不敢去當面對峙的情況下,只會一遍又一遍地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做錯了什么?那完完全全就是我當時的經歷。雖然后來我和那兩個女孩的關系都緩和了,但我一直沒敢去問我們之間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因為我害怕這會讓事情變得更糟——而且我也明白,我和她們的關系再也不會和從前一樣了。《女孩們的地下戰爭》在某種程度上寬慰了我,遭遇到這種事情的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葉青:在成長的過程中,我發現想形成和維持一些同性友誼,我常常得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像是小時候會害怕地跟著玩伴做壞事(偷地瓜、把鄰居阿姨曬的魚干丟進池塘等等),讀書時會反感地附和同學開的下流玩笑。通過破壞、侮辱他人來彰顯男子氣概,是這些情誼得以維系的核心,而如果我稍微流露出一絲不配合與反抗,就會被迅速孤立,踢出這個兄弟會。現在我只慶幸自己被踢得夠早。
潘文捷:如果一個人讓我不適和痛苦,對方就已經不是我朋友了。不過未嘗沒有過心酸時刻。比如說初中的時候,以為A和B都是我的好朋友,結果某天赫然發現原來她倆之間才更鐵一些,那就是我應該在車底而不該在車里的時候了。
02 男人打架都能打出兄弟情,女人一次惡語相向就“友盡”?
潘文捷:不知道為啥友誼中的矛盾也要怪罪到性別頭上來。曹操和關羽的關系不復雜嗎?好了,要是尼采和瓦格納是女性,那么大家大概會說她們最后反目,就是因為女孩的關系很復雜。但因為他們是男人,大家就會說是理念不合啦之類的,所以說人和人關系復雜跟性別又有什么瓜葛呢?
姜妍:如果從整體性上看,我覺得女性友誼和男性友誼是有一些差別的,但是不是本質區別我不知道。比如看《乘風破浪的姐姐》和《披荊斬棘的哥哥》,在同樣面對離別的時候,女性的表現和男性確實是不同的。雖然里面的情感內核可能類似,都包含著不舍、傷心、難過。
徐魯青: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厭女》里討論過現實里的女性友誼為何困難重重。她認為在女性被客體化的社會,能否贏得男性歡心是女性成功的重要標準,因此女性間會產生以男性為中心的競爭關系,女性共同體的關系也更動蕩。但在我看來,上野千鶴子沒有關注到女性友誼的全部面向,“扯頭花”之事難說哪個性別概率更高,男性間并不少有為權為名關系破裂之事。
另外,我也常慶幸自己身為女性,到現在仍可以和親密的女友擁抱、牽手、同睡一張床,這對大多數男性友誼來說不太可能。我還記得第一次聽到兩個男性朋友出門旅行時會開兩間房的驚訝,觀察身邊的直男,“哥們兒”之間在生活與情感里似乎離得更遠,傾訴太多心緒波動是肉麻的,親密的身體接觸也被恐同文化抹殺,想和同性朋友靠得近一點,就得擔心旁人或打趣或狐疑的揣度。在歐洲時會驚訝荷蘭室友和“哥們兒”緊緊挽著手走路,告訴國內的男性友人時,他沉默了一會,說小時候也常和發小抱著同睡一張床。看來厭女文化既令女孩發生“地下戰爭”,也讓男孩失去與朋友的親密擁抱。
葉青:魯青提到直男因為怕被誤會不敢與同性好友有親密舉動太好笑了,干嘛此地無銀三百兩,我以為扮直(straight acting)是只有怕被發現身份的同性戀才會做的事。這樣來看,怕被誤解而約束自己這種帶有恐同性質的行為,反而是在實踐同性戀性質(practice gayness)。
陳佳靖:想起之前看到一個短視頻,拍的是兩個男車主在開車時發生了剮蹭,二人都很氣憤地摔門下車,想要找對方理論一番。沒說兩句他們就推搡起來,這時候雙方都不甘示弱,擺起拳法陣腳,實實在在跟對方過了幾招。好笑的是,挨了幾拳之后,這倆人反而佩服起對方的格斗技能,很默契地放下了車的事,在大街上開始了第二輪“切磋”。事后他們拍拍身上的灰,再拍拍對方的肩膀,車的事就這么了結了,還萌生了一種不打不相識的兄弟情。我不知道這條視頻是不是完全真實的記錄,但在現實中以及影視劇里類似的情節也很常見。發生沖突的時候,男人們好像打一架就能解決(大不了再喝頓酒),事后還可以做朋友,女人們卻從不會輕易出手,只要有一次惡語相向,她們的關系從此就多了一個死結。

這是不是說明女性之間的情誼就比男性更復雜呢?也許是,但這不是女性天生更敏感或更記仇導致的。正如《女孩們的地下戰爭》所描述的,女性之間的戰爭之所以要隱匿到“地下”,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塑造了女性交往的規則。她們在成長過程中就被教育要克制攻擊性的一面,至少要在表面上成為友善懂事的“好女孩”。相反,男性則被鼓勵去展現剛強、有力量的一面。長期以往,不僅女性的憤怒被壓抑了,而且大部分女性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正常地表達憤怒和正面地處理人際沖突。她們可以委婉、刻薄、愛猜忌、“婊”且“mean”,唯獨不能與人公開對立,因為一個“好女孩”應該有能力不和任何人發生沖突。換言之,她們的復雜不過是因為缺乏對人際交往的安全感罷了。
03 無論性別,友誼事關超越自己的局限去愛另一個人之所是
董子琪:對《簡·愛》最深刻的印象不是簡·愛和羅切斯特的愛情,而是她小時候在洛伍德學校跟海倫的友情,讀那一段時我正好也是十二三歲,跟她們差不多大,也在半寄宿學校里,很能理解在孤寒的寄宿學校里遭受的嚴苛待遇——好像寄宿學校更放大了友誼的重要性,因為吃完飯的一段時間就是social around的時間。書里兩個女孩互相給予支持,性情也互補,簡·愛倔強而海倫堅忍,簡·愛能勇敢地幫助海倫走出屈辱,海倫也能以慈悲幫簡·愛化解憤怒,這是青春期里很難得的感情了。但可惜的是,海倫早早地離去了,仿佛簡·愛的一部分慈悲也跟著死去了。在之前或者之后,我好像都沒有看到過像這樣的友誼描寫了。
給女性友誼“抹黑”的例子來自簡·奧斯丁。簡·奧斯丁在《傲慢與偏見》里寫伊麗莎白與夏洛特交好,可是實際上兩人在人生選擇上大相徑庭,夏洛特選擇了伊麗莎白完全理解不了的柯林斯先生,從此過上了蒸蒸日上的好日子,她對婚姻的安排“充滿頭腦而沒有愛”,連伊麗莎白也得贊賞其理性。對人生伴侶審美的分歧會讓她們走上友誼的岔路嗎,可能這也是寫實之處。至于《諾桑覺寺》里的同性友誼,是多么糟糕啊,凱瑟琳與伊莎貝拉開始得熱烈,進展得迅速,一起交流看書的心得,伊莎貝拉還嚷嚷,男人總以為我們女人之間沒有真正的友誼,她可要讓他們看看事實并非如此!可是呢,不知不覺,凱瑟琳就覺得伊莎貝拉有哪里不對又不能確認,而正是“不知道哪里不對”透露了那位好友的真實本性。這段友誼最終也被證明沒有繼續的必要了。奧斯丁參透了這種少女情誼熱烈里的虛榮之處,這位作家對分辨情誼的真假、品性的高低確實在行。
黃月:認為女性友誼只是“扯頭花”無疑出自一種頑固的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橫亙古今、不分東西,這或許也是今天許多關于女性友誼的作品被重新發掘或新鮮創作的原因,比如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比如薩莉·魯尼的《聊天記錄》,作者和讀者都有意識去糾正這一偏見,去書寫其中無數的層次,去發現和照亮女性友誼的復雜與立體、愛與競爭。
很遺憾我無法身處一段男性友誼之中,去看到不同的友誼的狀態,但我既見過街頭兄弟酒肉朋友,也有幸在《此時此地》中體會到了庫切和奧斯特的情誼、在《歌德席勒文學書簡》中見證了兩位文學巨匠的惺惺相惜,在《三人書簡》中感受高爾基、羅曼·羅蘭與茨威格的思念和熱情。那些都是友情這種事物中無分性別的最珍貴的核心——它是人去努力建造和維持的結果,不是什么與生俱來或理所應得的果實,是超越自己的局限去愛另一個人之所是,是時時生長去創造一段關系之所是。
姜妍:昆德拉在小說《身份》中借著女主角和丈夫的對話曾經討論過一部分男性情誼和女性情誼的區別。對話中他們提到友誼的產生,最初為了對抗敵人而彼此結盟,所以起先是男性間的產物,因為他們外出打獵要互相援助。到了現代,集體打獵的記憶則變成了看球賽、喝酒等等,從結盟衍生出了新的契約關系。男性相對來說會更早接受這樣的“馴化”,甚至也內化成了男人的一部分,而女人這部分的“馴化”程度則要更淺。
隨著年紀漸長,我更向往的情誼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種看似不那么綿密的相處,是“朋友十年不見,聞流言不信”的友情,因為這背后其實需要強大的價值信念做基礎。
林子人:前段時間讀了《形影不離》,這是《第二性》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生前從未公開發表的一部小說,以她少女時代的摯友扎扎為原型,悼念她生命中最刻骨銘心的友誼。讀完我發現,早在費蘭特之前,波伏瓦就寫過“我的天才女友”了,連兩個女孩的生命軌跡都幾乎一樣:一個早早地就顯現出驚艷卓絕的才華,但被家庭環境所限無處施展;一個看似本分乖順,卻在天才女友的激勵下力爭上游,闖出了一片天地。20世紀初的法國女性所面臨的禮教束縛之嚴苛,不輸同時代的中國。這是否是一個女性生命經驗中永恒的命題——因榜樣缺失,女孩們只有從身邊的“叛逆者”身上汲取精神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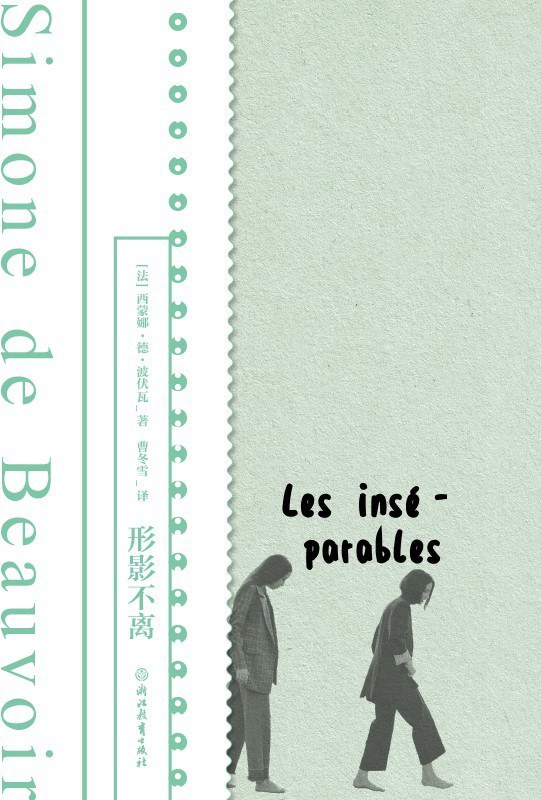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曹冬雪 譯
磨鐵 |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2-2
“那不勒斯四部曲”最觸動我的一點其實是它展示了女性友誼的復雜性,我完全能夠理解埃萊娜在深愛著聰明、漂亮且大膽的莉拉的同時,心懷羨慕、憧憬,又帶有一點點妒忌(反過來講埃萊娜身上也有莉拉妒羨交加的東西)——捫心自問,哪個女孩沒有過這樣的感受呢?俗氣的女性故事可能就止步于此了,但杰出的故事和真實的生命經驗告訴我們:女性能夠正視這種同性友誼的復雜性,坦率地承認心中的確存在某個陰暗角落,發現女性之間的共同點和聯結的可能性,并把這種張力釋放到更廣闊的天地去創造屬于自己的意義和價值。如今女性研究的發展則向我們揭示了,所謂的“女性友誼的復雜性”是性別維度的結構性傾軋所導致的。
愿天才女友的故事代代流傳,成為過去、現在和未來女性的警示與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