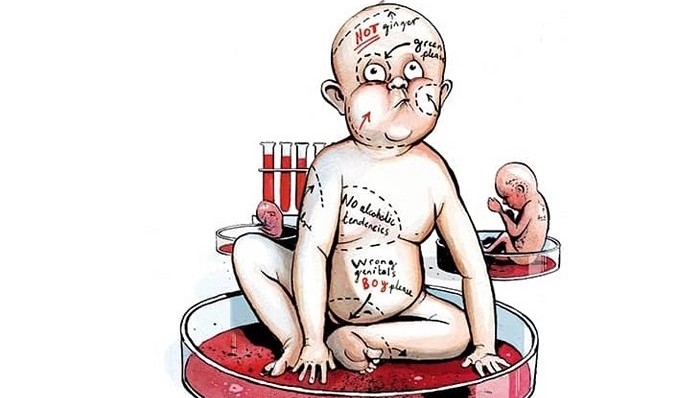在《如何與種族主義者辯論》(How to Argue With a Racist)一書里,遺傳學家亞當·盧瑟福(Adam Rutherford)清楚明白地解釋了為何許多廣為接受、具有顯而易見的常識性的有關種族的觀念其實是偽科學,他還在論證過程中稍微勾勒了一下相關的歷史背景以及助長了此類觀念的一系列意識形態(tài)偏見。對于進化的具體運作機制,我們的觀點可能還不夠成熟——并且在未經(jīng)思考的情況下就接受了一些18世紀帝國主義者發(fā)明的種族范疇,但他也企圖借這本書的主體部分向我們表明,這一切背后的遺傳學可能“高度復雜”。
《控制》(Control)是《如何與種族主義者辯論》的姊妹作。它依舊著眼于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觀念對科學的招攬與利用,或者說對此一關系的淺薄認識。如今拜納粹所賜,“優(yōu)生學”這個詞已經(jīng)臭名昭著了,以至于它往往會腐蝕它所觸及的任何東西。鑒于此,報紙上的恐怖故事經(jīng)常會拉它做大旗來抨擊廣義上的種種干預措施與觀念。任何胚胎或干細胞實驗有關的事都會“引來優(yōu)生學的陰影”,令讀者生出一陣夾雜著愉悅的小小恐懼。
情況并非總是如此。在20世紀早期,許多杰出人士無論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為何,都認為優(yōu)生學肯定是個好東西,有人甚至認為它的好是不證自明的。選擇性的育種(selective breeding)——其推進手段或可包括設法讓那些被認定具有不可欲特征的人少生孩子——必定能增進普羅大眾的智力、健康與繁榮。這一觀念并不新穎。柏拉圖在《理想國》里就設想過讓一個由兼具聰慧與美貌者構(gòu)成的特權(quán)階級來創(chuàng)造聰慧而美貌的嬰孩;而斯巴達人——起碼就杜撰的內(nèi)容而言——則傾向于把瘦弱的嬰兒扔下山崖。 在孟德爾與達爾文有關遺傳與遺傳機制的一系列思想問世后,這種古老的沖動又獲得了新的尊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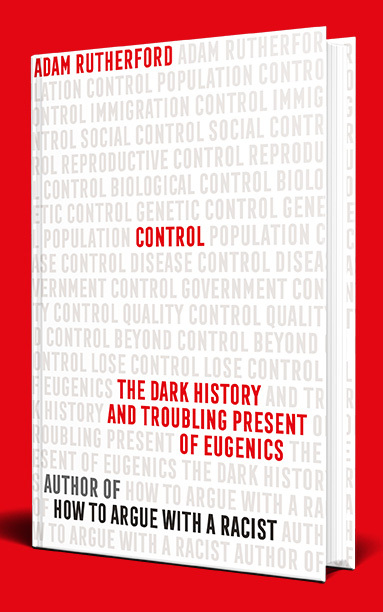
在英國,遺傳學的創(chuàng)始人是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他不僅首次提出遺傳學這個術語,還是孿生研究和許多統(tǒng)計學技術的開創(chuàng)者,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后來都成了詆毀其成就的口實。盧瑟福并沒有妖魔化各個優(yōu)生學的現(xiàn)代先行者,但他還是不介意稱這些人為種族主義者。高爾頓是個才華橫溢的人,但他的遺傳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一說乃是“證實性偏見的最高級表現(xiàn)”。他的弟子卡爾·皮爾遜(Karl Pearson)“對科學史的影響是巨大的”, 羅納德·費希爾(Ronald Ayler Fisher)則“穩(wěn)居有史以來最頂尖科學家的行列”,然而這三個人都跌進了優(yōu)生學的“兔子洞”。
定義——尤其是這種內(nèi)涵極其龐雜的術語——會惹出麻煩。優(yōu)生學可否被有效地界定為一本書的主題?為了部落的利益而對瘸腿、無法行動以及精神上處于不利狀態(tài)者實行安樂死等做法——如今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都不會同意這樣做,與表面看來是良性的干預措施之間究竟有什么區(qū)別? 又如,我們會在妊娠早期進行唐氏綜合癥的篩查,許多父母正是據(jù)此來決定是否繼續(xù)妊娠。至少在理論上來講,在體外選擇一個遺傳性疾病幾率最低的胚胎進行植入是有其可行性的。隨著科學的進步,我們已經(jīng)在探討于受孕后立即編輯胚胎基因組,以防其罹患遺傳性疾病這一可能。基因編輯技術還為我們帶來了新冠疫苗。這一切難道都是“優(yōu)生學”嗎?
盧瑟福在“減輕個人、父母和孩童的痛苦……而非國家強令的全面提高人口素質(zhì)”之間做出了區(qū)分,我(指本文作者Sam Leith,《旁觀者》雜志文學編輯)認為這大體上能成立。換言之,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的話,盧瑟福的意思就是:在人口層面實行干預不好;至于個體層面的干預……行吧,至少還可以討論一下。

這本書最有力之處就在于它就上述論調(diào)提出的解釋。如盧瑟福所指出的,在人口層面,有關什么能夠“提高”一整個社群的素質(zhì)的決策,通常都有意識形態(tài)性,和科學關系不大。它們暗示了一種人類價值的等級制——哪怕其并不以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波蘭東部村莊,納粹滅絕營所在地——譯注)為歸宿,也容易把人忽悠到種族主義、殘障歧視以及階級歧視這一方向上。

從歷史上看,潛藏在這些理論背后的恐懼,是病患、殘障、低劣的窮人或種族上的他者將會“吞沒”、污染或壓倒光明與善良。盧瑟福認為,這種恐懼——他的論述偏簡練但說服力尚可,與維多利亞時代面對新興的工業(yè)化世界里數(shù)目不斷增長且頗為刺眼的下層階級以及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滋生的焦慮有關。許多人相信羅馬滅亡的原因是下層階級淹沒了統(tǒng)治者,這暴露出了他們的文化偏見。高爾頓認為,教父讓自己最優(yōu)秀的神學家們保持單身乃是愚蠢透頂?shù)摹?/p>
的確有觀點認為,優(yōu)生學支持者與那些聲稱相信資本主義崩潰的歷史必然性并鼓動武裝革命的人有著同樣的毛病。如果你真的相信北歐人種的血統(tǒng)更優(yōu)秀、更具活力(乃至于相信進化的壓力青睞更高的智力),那你還用得著走這么多過場嗎?你難道不希望高等種族在適者生存的法則下自動勝出嗎?
話說回來,優(yōu)生學支持者總的來看并沒有這么優(yōu)哉游哉。相反,就像我們成功為肯德基培育出了肥美的雞仔一樣,我們能夠并且應當為智人(Hom sap)做類似的事情。他們基于意識形態(tài)的胡言亂語來制定政策規(guī)劃,其中一些出于善意,另一些則遠非如此。正如程序員所言,垃圾進,垃圾出。諸如“低能兒”“白癡”與“蠢貨”等操場上的羞辱之語一度還被歸為了診斷意義上的范疇——包括智力遲鈍或心理疾病與其他形式的殘疾再到刑事累犯在內(nèi)的多種情況,均被籠統(tǒng)地視作遺傳退化的標志,被判監(jiān)禁或絕育。而這只楔子的大頭正是所謂的“種族衛(wèi)生(racial hygiene)”與納粹對所謂Lebensunwerten Lebens的滅絕行徑——這個德語詞的意思是“沒有再活下去的價值的生命”。
但這本書并不滿足于做這種志在必得的事,即論證我們都明白某不好的東西是不好的。盧瑟福的公允態(tài)度,或者至少是運用科學思維的程度,足以讓他關心一些更尖銳的問題,例如:即便我們認定“積極的優(yōu)生學”是個好東西,它又真的能起效嗎?
截至目前,答案都是一個響亮的“不”字。回到以前是沒戲的——科學家們基于一些對遺傳運作機制的想當然的猜測來構(gòu)思政策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放到今天也還是不行。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了解基因是如何塑造我們的,而這也讓我們更加明白我們的所知之稀少。例如,一般智力或精神分裂癥易感性的可遺傳成分涉及到我們已知的數(shù)十或數(shù)百個基因,還關系到更多我們一無所知的基因,它們的影響是多元的,呈現(xiàn)為高度復雜的相互依存。這段論述可謂是盧瑟福在自家地盤上作戰(zhàn)(“當科學家扮演歷史學家時,”他略帶挖苦地說道,“存在極大的風險”)的一大高光時刻。

有關遺傳的絕大部分流行觀點,都源自他所稱的“單基因決定論(monogenetic determinism)”:這種觀念特別適合于放在頭版頭條上吸引眼球,即“存在某個導致X的基因”,如果有導致藍眼睛的“基因”,那么你似乎就可以刻意選擇藍眼睛了。但即便是眼珠的顏色以及發(fā)色這種例子——英國中學生學到的則是其簡化版——也未必有表面上那么可靠。“這一謬誤有三個維度,”盧瑟福寫道:
復雜的性狀很少有單一的遺傳學起因,它們總會涉及到非遺傳環(huán)境,而遺傳也是概率性的而非決定論的。這是優(yōu)生學計劃始終缺乏堅實根據(jù)的一個關鍵原因:我們在意的弱智、癲癇與酗酒等狀況,確實都有遺傳成分——人類的生物學與心理學當中的幾乎所有元素都概莫能外——盡管它們從來就不是單基因的,且這些遺傳學起因也很少是決定論的。
盧瑟福認為,那些迷戀技術的未來主義者似乎最熱衷于在21世紀復興某種“美好”版優(yōu)生學(托比·楊在書中被敲打了一番,多米尼克·卡明斯也被點了名),但他們不過是因為不夠了解科學而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在說些什么。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設計嬰兒”在科學上仍屬異想天開。CRISPR基因編輯遠非某些人炒作的所謂絕對可靠的“DNA打字機”,那些讓我們在通往《變種異煞》(Gattaca)的路上走得更遠的實驗不僅不切實際和不可靠,而且在各方面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此外,盧瑟福還表示,企圖在試管中就開始為廣大普通人群“施肥”并不可行,傳統(tǒng)的方法更簡單也更有意思。如果你想提高人們的一般智力,那么投資教育、營養(yǎng)與潔凈的空氣和水,讓進化順其自然地進行下去,其實是更便宜、更有效以及更人道的——當然也更枯燥。如果我們忽然有能力一舉消滅唐氏綜合癥或亨廷頓病了,我們是否應該立馬開干? 盧瑟福在這些問題上持觀望態(tài)度,你也不好責怪他,我們也尚未碰見過那樣的情形。
有趣的論點、歷史奇聞、細致的案例研究以及平易近人的笑話在盧瑟福的書里匯聚一堂,你讀完它之后想必會再次對真正的科學家的所作所為產(chǎn)生敬重與興趣。我想這本書可能很難用一兩句話來概括,畢竟它的復雜程度非同一般。
(翻譯:林達)
來源:旁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