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家長在生日蛋糕上插滿課本讓孩子大哭、“985碩士媽媽”嫌棄孩子是學渣,這類視頻屢屢登上熱搜,更不要提“雙減”前被奇觀化的海淀媽媽(總是媽媽,沒有爸爸)和“雙減”后周末脫不開身的家長。城市很多中產家庭里的父母和子女,似乎都在為教育焦慮和痛苦,而一些民間家庭的教育實踐要么很少被主流話語關注,要么成為被凝視和同情的他者。
北京師范大學研究員安超在《拉扯大的孩子:民間養育學的文化家譜》一書中指出了民間教育實踐被輕視的現狀。在學院內部,大量教育學研究被布迪厄的階層研究理論統領,強調家庭文化資本決定個體社會地位。階層理論可以有力地解析和批判結構弊病,但單一的視角也可能帶來對民間民眾教育實踐的貶低——民間教育既提供不了經濟資本也沒有文化資本,成為了需要被彌補、被解放的對象。同時,對民間教育的研究也缺乏主體性,民間父母在傳統養育中的實踐性知識被忽略了。

安超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1年
安超從小在山東農村長大,后來讀書升學并進入城市工作生活。在博士期間,她回到山東鄉下老家生產,感受到早已體認的現代城市精細化育兒與鄉村養育經驗的巨大沖突,這也讓她決心重新回望個人家族教育史,審視被現代科學育兒話語所輕視的“庶民教育”。庶民是區別于貴族的群體,除了養育孩子,還要為生計奔波,他們也不同于掌握了精細化育兒標準的城市中產階級,而更多憑借直覺與經驗進行養育實踐。
反思當下結構性教育焦慮,擁有話語霸權的“科學育兒”和“精細育兒”是唯一“正確”的養育方式嗎?我們是能否在缺少“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加持的庶民教育里看到更多溫度與能量,并打開對城市養育方式的想象?在教育成為“家庭資源投入的無底洞”(社會學家渠敬東語),越來越多的女性退出職場、代際矛盾加劇之時,城市育兒是否可以借鑒庶民共養經驗,超越原子化家庭,構建互助的養育共同體?
焦慮的母親,疲憊的兒童
在《給無價的孩子定價》一書中,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社會學教授維維安娜·澤利澤(Viviana A. Zelizer)探討了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兒童的社會價值觀念轉變:兒童從家庭中的勞動力轉變為“經濟上無用,情感上無價”的存在。這一針對美國社會的描述也極其契合中國幾十年來兒童角色的巨大變遷,如今的孩子幾乎不參與任何生產性勞動、成為家中所有人的情感寄托,同時也被期待在道德上無暇,家長嚴格地篩查動畫片是否有陰暗的畫面、不準孩子和成績不好的“壞孩子”做朋友,不允許任何玷污孩子純潔性的風險存在。安超認為,教育焦慮最根本的危機是兒童對成人的經濟依附和成人對兒童的情感依附,“結果就是我們一邊無微不至地照顧孩子,一邊把他們禁錮在家庭、游樂場、電子產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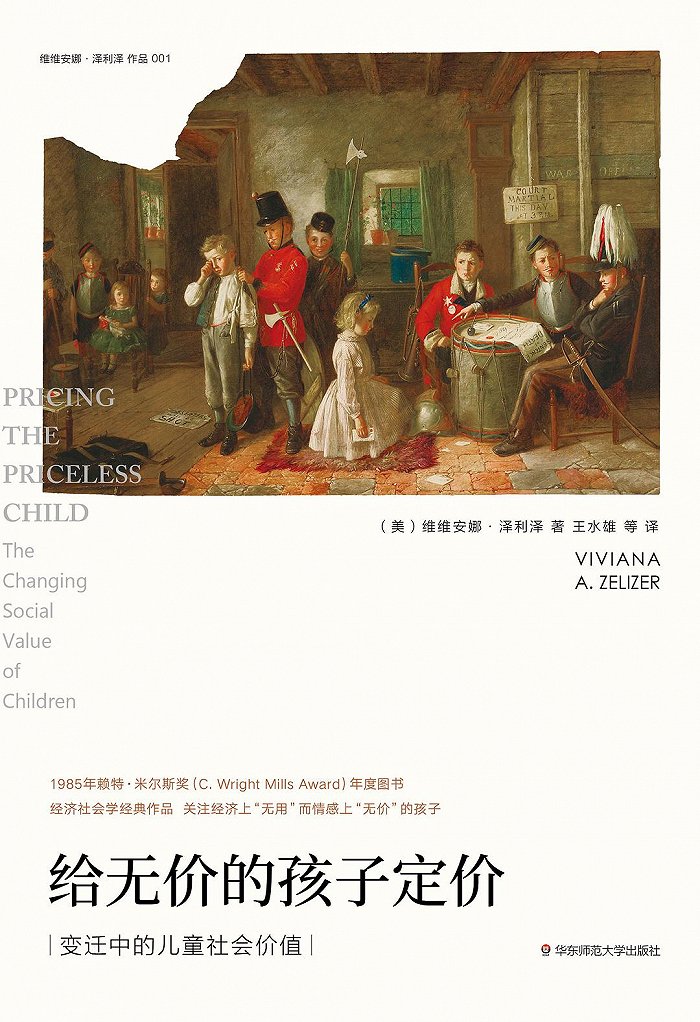
[美]維維安娜·澤利澤 著 王水雄 譯 ????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年
對兒童的精細化養育要求也進一步加劇了性別不平等。在美國,“母愛至上”、“依附理論”、“童年決定論”等觀念長期流行,日本占主流的觀點是教育學者中內敏夫提出的以兒童和母親為核心的“教育家族”。而在中國,母親所承擔的角色壓力在近幾十年里急劇增大。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教授金一虹指出,自1990年代起,中國掀起了“母教”潮流,宣揚好母親應該勇于承擔責任,為了孩子犧牲自我發展,這也讓許多母親在工作和育兒沖突時產生一種罪惡感,全職母親的現象越來越多。蘇州科技大學社會學副教授陶艷蘭也分析了中國育兒雜志中的“母職”話語,她總結出這些話語建構的理想母親形象:愿意花費高昂的教育經費、遵循育兒專家指導、一切以家庭和孩子為重等。安超在田野中觀察到,如今,中國城市家庭中“嚴母、玩父、慈祖”代替了傳統社會的“嚴父慈母”角色分工,母親成為教育的總舵手和指揮者。安氏家族中有越來越多的母親為了敦促孩子的學習,又不放心上一輩的教育方式,選擇放棄自己的職業發展專門在家陪讀。這也給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壓力,焦慮的母親與疲憊的兒童共同構成了城市中產的教育困局。
教育焦慮中還充斥著大量“科學育兒”話語,例如“家庭教育要專業化”、“父母要培訓上崗”。弗吉尼亞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莎朗·海斯(Sharon Hays)指出,科學育兒提倡的是一種以“兒童為中心、信賴專家指導、高情緒投入、勞力密集、高消費的育兒方式”。安超在對自己家族做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也發現,城市新一代年輕父母往往不相信自然成就式養育,對于“專業機構”和“專業書籍”的熱情非常高,家族中第一個女博士安德婧是科學育兒的代表,她花費了十萬余元報了很多家庭教育班、父母課堂、家長學校等,還抽出自己幾乎所有閑暇時間學習育兒知識。
然而,科學育兒并不總是正確,在界面文化此前關于中產育兒焦慮的采訪中,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助理教授張聰指出,許多公共話語中的“育兒科學”其實更多是對某一理論的斷章取義,學界本身就對如何正確育兒沒有唯一的答案。興起于西方國家中產家庭的科學育兒往往需要投入高時間與財力,給家庭造成了很大壓力,安德婧在科學育兒的高標準之下,需要不斷尋找心理醫生來消解內心的焦慮和失落,同時她的孩子也感到不開心,在應試教育的大環境里,他始終覺得自己在學校的表現對不起母親的付出。科學育兒的話語霸權也造成了對自然成就式養育和養育直覺的污名——完美媽媽適用于經濟好的中上階層,平民家長在科學育兒的話語之下變成不合格的家長,正常的媽媽淪為“失敗的媽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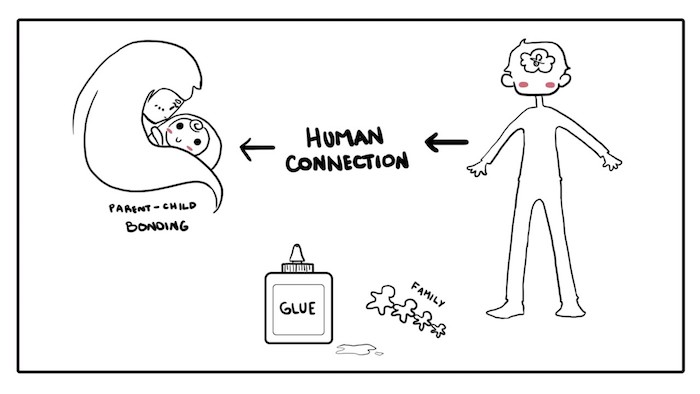
庶民教育里的“功德”、品行與同伴學習
在與安超的一場線上對談中,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許晶認為,“現在大多數的育兒書籍都是強調核心家庭,以兒童為中心和本位。而實際上如果拋開我們熟悉的樣式,去看一個更廣闊的世界,所謂‘科學育兒’背后是一套理性主義的權力和系統,如果參考人類學和民間教育學研究,全球不同文化里的民間育兒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作為通過讀書升學進入大城市工作的鄉下子弟,安超在自身家族教育史的田野調查里發現,從小受到的鄉土社會庶民教育為自己留下了許多珍貴烙印,或可為如今城市教育癥結提供新的可能。
和刻板印象里“小鎮做題家” 、“讀書改變命運”的功利性讀書相悖,“回饋社會”經常在鄉土民間社會作為勸勉讀書的目的出現,這類具有公共性的讀書目標已經很難在當下城市激烈的教育競爭里找到。在安超的觀察里,庶民教育雖然在不同時期有程度不同的功利性,但也始終帶有超越性和公共性。人們對學習的目的不僅是自利與物質的,老人認為孩子讀書是為了“學好”,“好”是“走正道”、“對人有用”等,而非僅僅對自己的“實用”,“功德”在村里人的教育中是比“功名”更重要的事情。安超發現,這種“功德”意識在每代人身上都有所體現,村里出的讀書人在經濟獨立后往往都會盡其所能為族人提供幫忙,完成經濟回報和道德回饋。人們對讀書懷著純粹的精神向往,許多村民雖然沒有機會讀書,但會尋找一切機會搜羅有字的東西。沒有上過學的老人也會一直保持將筆墨紙硯放在家中,寫寫畫畫。
與激烈的教育競賽對“出人頭地”的追求不同,安超注意到,庶民家庭里的孩子長大后不一定很有出息,但也很少會品行敗壞,她歸功于庶民教育中的“底線性教育”。底線性教育主要包括對勤勞、節制和體恤的強調,這些都是生計中重要的品質,比如“不勞作不得食”(勤勞)、“不眼饞、莫伸手”(自我節制),“報恩與回饋”。底線教育內化于日常的生活、禮儀、言教之中,不能保證孩子成年后可以出人頭地,但也同時防止了他們墜入社會底層。出于生計考慮,民間還會強調自立性勞動,比如兒童自己料理生活、照顧自己的能力,強調公益性勞動,從小鼓勵孩子獲得勞動所得后回饋社會的重要性。
許多研究認為閑暇是貴族式教育的特點之一,同勞動相對立,而忙于生計的庶民階層被視為少有閑暇和精神生活。但安超的田野調查發現,閑暇活動是庶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平民的閑暇往往和生計相結合。孩子們一邊摘果子、割麥子,一邊和同伴玩耍,雖然游戲常伴隨著暴力和受傷,但兒童也在其中學會控制自己的攻擊性,比如“打人不打臉”的規則,同時也在游戲里鍛煉膽量、培養伙伴情誼。許晶在對談中也提到,非洲采集部落的兒童很少單獨玩耍,玩耍和生計、勞作往往結合在一起,童年的學習有傳統上是非正式的,這些培養了孩子們很強的好奇心。在當下的中國,從研究到實踐都非常強調親子關系的教育,而相對忽略了同伴學習(Peer Learning)——在和同伴相處的過程中習得社會知識并培養自立能力——的重要性。

安超在《拉扯大的童年》一書中指出,平民生活中的世俗交談(拉呱)也是閑暇生活的重要部分,老人下棋時,“人們一邊東家長、李家短,這些話也全都落在孩子們耳朵里”,孩子也從中學到了成人世界的道德監督、審判、教化;村子里還常有流動的手藝人,到村里來干著剃頭、補鍋等活計時,孩子往往會圍攏聽他們談村外新鮮的故事,豐富對世界的認知。在鄉土社會里,兒童有很多參與公共閑暇活動的機會,比如集市廟會、節日祭祀。這些公共生活既與生計綁定,又充滿人情味,讓兒童學習到社會中的人情往來和買賣情誼,比如“買賣不成仁義在”、“聊著天臨走時賽上兩本菜,這次零錢沒帶下次再補上”。在紅白喜事里,孩子也獲得了最初的關于死亡、愛情和性的概念;喪葬儀式中“孩子們就跟在隊伍后面看熱鬧,他們對‘死亡’懵懵懂懂,但并不恐懼,孩子們跟著大人完成整個儀式,可以慢慢消除對死亡的恐懼”。無論是通過同伴游戲獲得非真實暴力的體驗,還是與各式各樣的人閑聊、參與公共生活,兒童都可以在這些活動中里習得日后的社會經驗。相較之下,過度保護孩子、甚至將之與社會百態隔離開來的教養方式卻可能適得其反,阻礙了兒童在社會參與中培養道德、開放心胸、發現同伴、與其他成年人相處并認識世界的可能。
城市育兒有可能超越原子化核心家庭嗎?
安超觀察到,城市養育行為越來越退守核心家庭,孩子也仿佛成為父母的私有財產。“管不得的寶貝疙瘩”說明家長對孩子的情感越來越私人化的同時,對他人的孩子也越來越缺乏公共之愛。安德婧的孩子在自述中提及,“我的母親常說,媽媽為什么偏偏管你而不去管街上的路人呢?因為他們和我沒有關系,我只關注我自己的孩子。這樣的話表達了媽媽對我獨一無二的關愛。”當大人斬斷同公共社會的聯系,這種“獨一無二”的愛將孩子和家長都禁錮在狹小的空間里,既限制了父母與兒童的發展,也使得家庭內部承擔著巨大的養育壓力。澤利澤也指出了現代社會中兒童的神圣化現象,成人在資本世界中遭受冷漠的商業文化和異化的勞動后,將全部情感與心靈依賴轉向孩子,兒童成為如同宗教的神圣性存在,家庭成為現代風險社會中的避風港,而不再是個體通往廣闊世界的橋梁。
實際上,從人類歷史來看,以原子化核心家庭為中心的養育模式是非常晚近的產物。農耕時期,中國平民的養育模式是親緣共養,一個家庭的育兒既依靠家族支持和女性合作,也有同村人互相的關照,比如一家孩子缺奶時可以讓另一家媽媽幫喂奶,比如一些條件困難的孩子“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緊密的熟人社會與親人紐帶誠然可能導致很多問題,比如生活私密性難以維持、個人邊界被侵犯等。但這種互助共養模式無疑也有可取之處,既能減輕家長尤其是母親的巨大壓力,又得以不將養育局限于沖突劇烈的兩代人之間。
如何使對兒童的愛超越私人家庭的邊界,把兒童和成人重新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引向公共生活?許多地方正在努力嘗試超越核心家庭的互助育兒模式。“四環游戲小組”是北京師范大學的師生在北京四環農貿市場發起的互助組織,農貿市場的外來攤販面臨孩子在北京“入園難”問題,他們自身也因菜場工作繁忙無暇看護和陪伴幼兒。北師大的師生們借鑒了20世紀六十年代英國的“社區家庭自助育兒”,組織攤販家長互助輪崗,組織讀書會、出游、玩具制作,為菜場的孩子們提供基本的學前教育和社交環境,如今,游戲小組已經從大學生主導變成了攤販間的自發互助,數百個流動兒童通過這樣的方式得到了基本的學前教育。“雙減”政策之后,上海五角場街道也出現了社區互助育兒組織。在假期里,要工作的父母既不愿意讓孩子獨自在家,也不想把教育全權托付給市場上昂貴的補習班。于是,家長們自發依靠專長組織課程,輪流講課陪伴鄰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變成了“我們的孩子”,家庭養育變成了小范圍的公共生活,互助組織也創造出超越核心家庭的多元復雜的社群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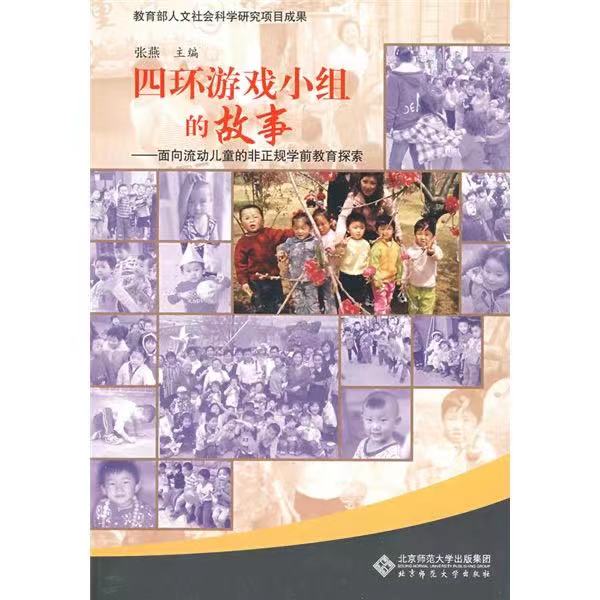
張燕 主編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9年
中華女子學院社會工作學院副教授李潔在《重新發現兒童|“雞娃”背后:從“外包”課外生活到社區互助育兒》一文中說,“從歷史的長度來看,養兒育女完全落到家庭只是近來的事,撫育帶有公共屬性,且不僅僅局限于對于兒童和家人的照顧,還包括營造社會共同體,維系共享的意義紐帶、情感和價值等其它不同性質的勞動。”安超認為,當今的城市家庭可以借鑒庶民教育的共養經驗,建立具備邊界感的互助養育共同體,讓教育超越私有制家庭。政府也應建立適合人際互動的公共場所,比如社區花園和城市公園這類更自由的、非組織化的人群交流場所,而不是讓城市被商業中心的房地產綠地占領。同時社會也應對邊緣的、由人們自發所形成的教育嘗試更加寬容,讓父母和孩子有機會從單一的教育想象中解放出來。
參考文獻:
群學書院 安超《拉扯大的孩子》沙龍討論紀要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3899996/
維維安娜·澤利澤 .《給無價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科學育兒”可以紓解城市中產的育兒焦慮嗎?》, 界面文化http://www.cfztjj.com/article/2189905.html
《重新發現兒童|“雞娃”背后:從“外包”課外生活到社區互助育兒》,澎湃思想市場https://mp.weixin.qq.com/s/TTdpVAnPDjeTl4k5J7sBw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