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作家尹學蕓居住在天津薊縣,多年間她從一個單位遷徙到另一個單位,從文聯、文廣局、旅游局到住建委,基層單位的工作經驗讓她對單位工作、生活和人際關系體察深刻。在她的小說中,單位的會議報告、職位升遷、人際變化等風吹草動總是牽動著人們的敏感神經,而各種波動中的基層“文化人”經常扮演著重要角色,文化對這些人物的作用是雙重的:文章幫助他們博得重要人物的重視,同時也讓他們的境遇充滿誤解。
前作《曾經云羅傘蓋》中的“我”曾經是報告文學的作者,現在作為掛職鎮長,前往村落勸說曾為勞模的釘子戶同意拆遷;《玲瓏塔》里的“我”是內部雜志的一位編輯,因為借了一本內有手繪的民國方志給別人,導致古塔遭受被盜;《士別十年》則寫出了女性工作人員在單位十年間的變化,其間變化最大的是她對人的認識,她認識到熱愛談詩歌的上級是在用文學“籠絡”她,跟她爆料的同事心里有其他打算。
尹學蕓日前推出新作《尋隱者不遇》,收錄了《望湖樓》《比風還快》等篇目,前者以一場酒局為中心展開身份懸殊的參與者——前市長與普通農村的不同生活,《比風還快》以鄉村知識分子去城里辦事為窗口,展現了托人辦事遭遇的尷尬與窘迫。與尹學蕓之前的小說集《我的李海叔叔》諸篇相比,我們可以到發現,這些作品的相似點在于將人物置于單位或跟單位相關的情境中考察世情冷暖以及人間生存智慧。

5月,尹學蕓因新作出版來到位于上海中心的朵云書院參加了一場新書分享活動,并在活動之后接受了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專訪。訪談中,她講到了自己多年間作為基層創作者的經歷,走過許多彎路,碰過不少釘子,別人說她大器晚成,只是因為不了解她這么多年一直都在這個行當中,也主辦小型文學刊物、指導作者創作,而像自己這樣的基層創作隊伍,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
01 人物只有放到歷史長河中才能看清行為軌跡

界面文化:你的小說很多都是關于單位體制下基層人員的生活,這樣的題材是怎么進入你的視線的?
尹學蕓: 我寫了方方面面的人和事情,但基本都是我的工作和生活范圍之內的,很少去寫陌生的領域,所有的故事人物和一些細節都是從生活中來的。我在很多領域工作過,過去在住建委,更早的時候在文化局、文聯、文廣局、旅游局,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我的工作環境比較社會化,不是像大學和部隊那樣面向單一的群體。我生活在薊州,這是一個地級城市,離天津有一百公里,有高山盆地湖泊,又是革命老區,我常說這里像是一個大的行政形態的縮影。我能夠寫出各種題材也得益于這么多年生活在一個小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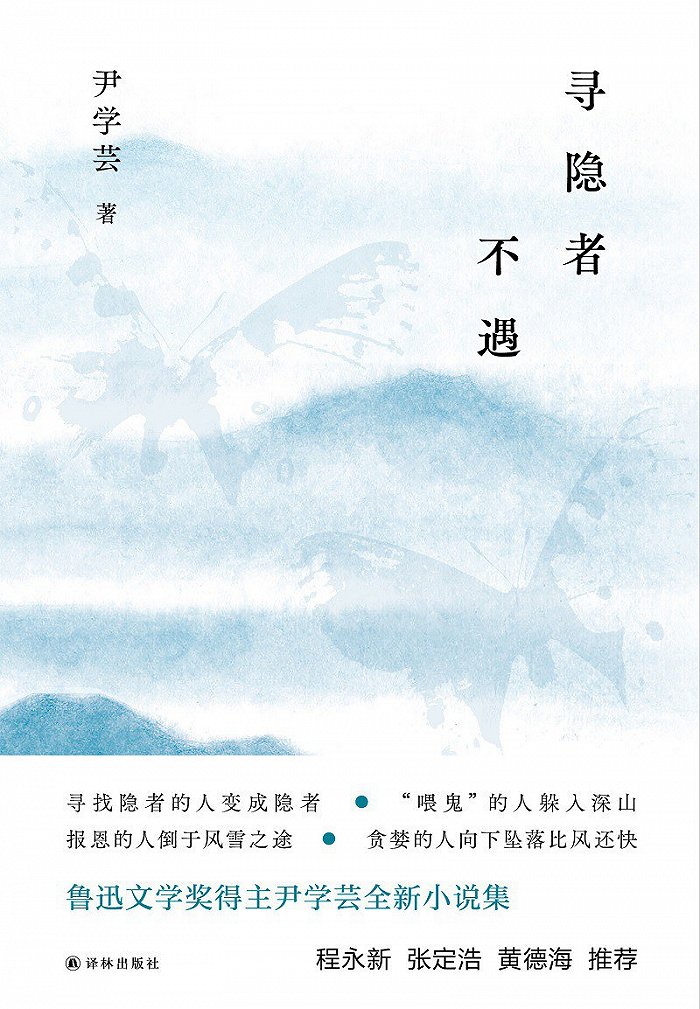
尹學蕓 著
譯林出版社 2021年
界面文化:在單位工作,人際關系這一點會特別地浮現出來嗎?比如說你的小說里寫有些人的真正面貌展現出來時,會給人悚然的感覺,看起來單純善良實際上可能是告密者,《曾經云羅傘蓋》里的年輕后輩陳珂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尹學蕓:我在寫那個小說的時候就發現,人是在不斷地變化的,一個人永遠有你不了解的地方,要一點點慢慢發現。機關跟鄉村又不一樣——鄉村不用刻意強調人與人的關系,因為大家都是平等的;機關會分出很多層面,領導和非領導,年齡大的和年齡小的,甚至身后的背景都會有人刻意衡量和揣測。這就意味著很多人總要面對不同的人,處理不同的人際關系。為什么說機關復雜呢?也就復雜在這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這些其實都很正常。但這些日常的東西用文字強調出來,就變得不那么尋常了。陳珂這樣的人在她的朋友圈很可能是很可愛的形象,但人性都有弱點,不知道什么時候這個弱點就暴露出來,有些是出于利己,有些是習慣的反應,說起這個話題覺得好有意思,還可以再寫個小說。
界面文化:那么女性在這群基層公職人員當中有什么特別之處嗎?
尹學蕓:應該說會玲瓏一些。環境造就人不是一句空話,過去總說三日不見(當刮目相看),《士別十年》里寫十年中一個女性都經見了什么,發生了哪些改變。任何人都會有一個漸變的過程,只是很多時候不自知而已。文學作品是濃縮了時間和空間的產物,人物只有放到歷史長河中,才能看清行為軌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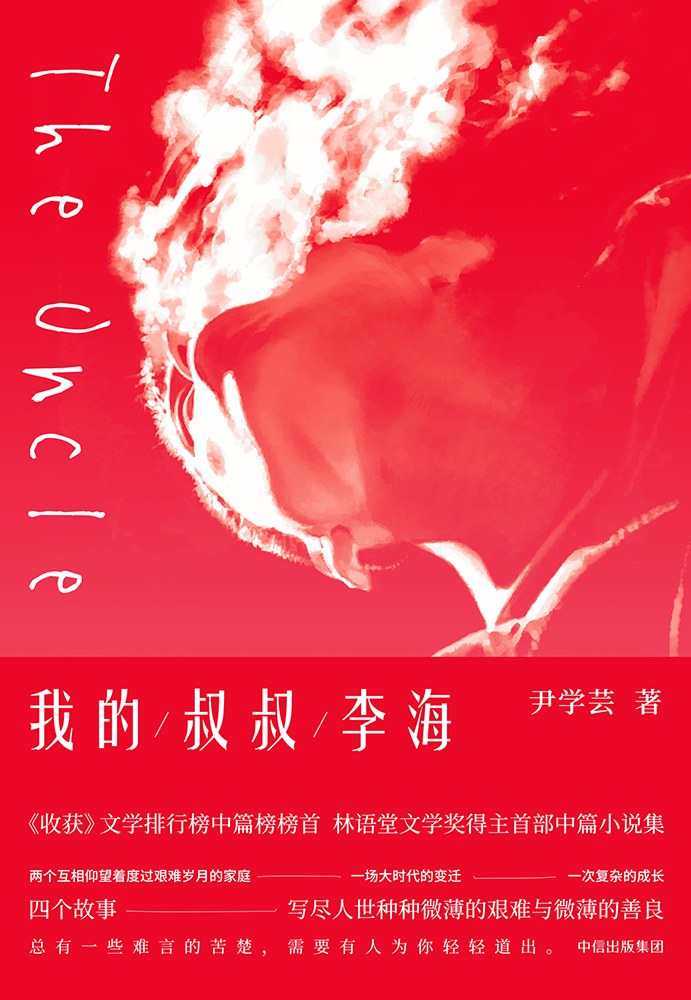
尹學蕓 著
大方·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
02 書寫獲得榮譽卻被時代拋下的人
界面文化:《比風還快》里講了一個辦事的故事,一個農村自由知識分子為了幫妻弟要回來被押走的摩的,找到城里在公安局工作的表哥,兩個人其實有著市民/村民、官員/普通人的不同。這樣的故事在你的工作中也出現過嗎?
尹學蕓:這就是大城市的很多作家很難接觸到的形象,但對我來說很尋常,我的生活中很多這樣的人。鄉村的小知識分子,在鄉村中屬于知識階層,比一般的老百姓要有眼光,屬于鄉村能人;另一方面這樣的人通常也自命不凡,有點傲嬌的性格。找人辦事這樣的事情太多了,我們這樣一個熟人社會,求人辦事,和別人求你辦事,都很普遍。就因為尋常多見,我就想寫這樣一個人物。
這個作品寫得很早,里面很多的現象都不存在了,像那種摩的載客,現在都不允許上路了,當時有這樣一個歷史階段,摩的被圍剿、追殺。這種辦事情境也折射出許多社會問題,他心目中覺得表兄和縣長在一個樓辦公就已經高不可攀了,但只有表哥自己知道自己是一個很小的人物。人的一生很多時候都有這種虛妄和錯位,有時候是主動虛妄錯位,有時候是被動虛妄錯位。眼下的朋友圈其實最能體現,同樣是圈,與生活中的圈很不一樣。
界面文化:酒局也是一個有趣的場合,《望湖樓》就是一個以酒局為主的故事。
尹學蕓:酒局會呈現各種各樣的人物,還可以聽到各種酒后吐真言,這是一個熱鬧的場合,人在酒后會變得非常有趣:平時話很少的蔫人可能變得妙語連珠,一個很羞澀的人會變得開朗放松。酒可以拉近人和人的距離,三杯酒之后就可以稱兄道弟。總之我還是蠻喜歡微醺的那種狀態,看別人喝酒也是享受。不過現在這樣的狀況已經少見了。
小說里寫到了那個不適應酒局處境尷尬的人,這種人在生活中隨處可見,有的人因為很少出席這樣的場合,在某個場合中那種不適應感非常強烈;有些人雖然收入不高職位不高卻一直在酒局上混,和從不參加酒局的人不一樣。
界面文化:你在小說里寫過一個有意思的人物朱玉蘭,是一個曾經有信仰有榮譽,時過境遷后來變成拆遷釘子戶的人。為什么會寫這樣一個人呢?
尹學蕓: 我那個時候一直在留意這樣的人,也不光是朱玉蘭,有不少過去得到很多榮譽的、非常光鮮的人,都面臨著相同的處境。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個撫順的勞模,自己變得很窘迫,還停不下來要幫助別人。這群人可以說是被時代拋下的人,時代列車從他們身邊經過,他們上不了這輛車,但總能聽見隆隆的車響。他們與時代脫節,生活在自己曾經榮耀的光環里,自己是走不出來的。我是真的受到了這個撫順勞模的影響,我想一個好的社會不應該忘記他們曾經有的貢獻,不應該說不需要了就忘記他們。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善于遺忘的社會,這點太功利了,這些人會讓你覺得很難過的。

界面文化:主角“我”是掛職鄉長,你自己是不是也有掛職的經歷?這個經歷會讓你更深入了解村莊嗎?
尹學蕓: 對,我也曾經掛過職,這和回自己生活的村莊不一樣,因為別人看你的眼光不一樣,你在家里的村子就是家里的丫頭,村民跟你也沒有距離感;作為知識分子掛職去一個地方,不好的地方是很難真正融入到老百姓當中,但可以換個角度看村莊的變遷。
說起來,《曾經云羅傘蓋》這個作品曾經被多家刊物退稿,退稿的理由五花八門,當時《收獲》要稿時我還說,這個小說到《收獲》是最后一站,不發我就私藏了,我不想為了發表而發表,因為對朱玉蘭這類人物和她的遭際的情感超越了同情,在我心里她是一個大人物。
03 人們不了解基層寫作者的工作,彎路最終變成積累
界面文化:寫作上你有相應的偶像嗎?
尹學蕓:我閱讀非常有限,因為沒有讀過大學,都是在鄉村一點點成長起來的,沒有受過系統的訓練,也沒有人告訴你什么作品是應該讀的,經常自己感嘆好書太多了,讀不過來啊!有時索性就讀曾經讀過的。比如《百年孤獨》,我連臺灣的版本都讀過。但因為讀得龐雜,我倒覺得不受局限,對作家擴展視野也是好事。
我記得最早讀外國文學都不太讀得懂,讀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時先把人物名字背下來再去看小說。1981年讀高中時看《紅樓夢》,記不住那么些人物,就把所有人物分成寧國府、榮國府,列成兩張表格,貼在我家土炕旁邊的房山上,我經常站在中間記,誰是誰的小廝,誰是誰的丫鬟。后來接觸張愛玲,她說出名要趁早,我說那是沒出生在靠山屯,要出生在那么偏遠的地方,她就不這樣說了。現在通訊便捷了,朋友圈里有個著名作家都不鮮見,我們那個時候認識一個報紙的編輯都很困難,郵寄個稿子過去人家也不一定看。張愛玲寫她寫了稿子敲主編的門,鄉下的那些作者哪有這種便利呢。這意味著你要多走很多彎路,但這些彎路都不可怕,慢慢地,你的彎路都會變成你的積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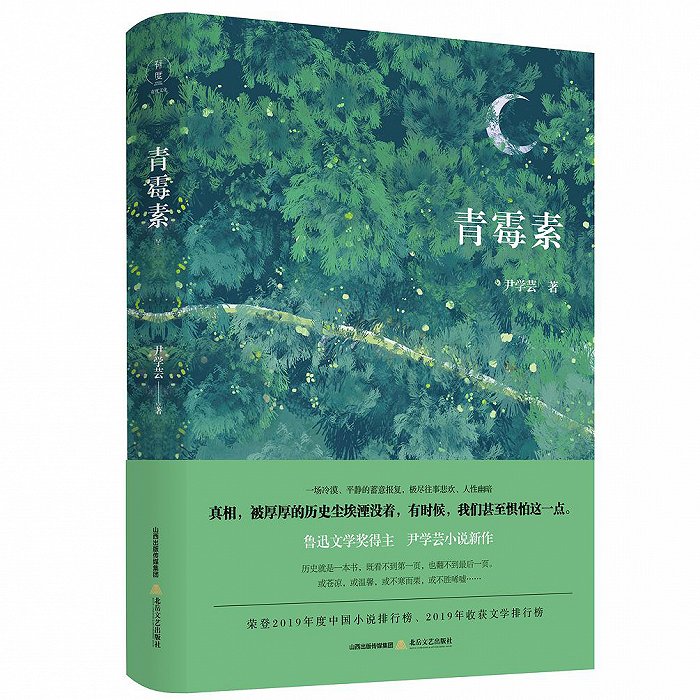
尹學蕓 著
北岳文藝出版社 2021年
界面文化:什么樣的彎路?像是被退稿嗎?
尹學蕓:那當然了。90年代中期有一群著名作家來薊縣,我陪著他們登盤山。有位作家非常炫耀地說自己今年發了四部中篇,我想我也發了四篇啊,還都是頭條,但我發再多的中篇,我也不是著名作家。這個事情一直都記得,這是沒辦法的事。很多時候不是你寫得不行,是你沒在那個位置。在那個位置,就容易被更廣泛地傳播,被選刊選,被評論家評,或者獲獎。這對基層作者來說都是很困難的事,但除了努力你別無選擇。現在有很多作家,跟當年我的情形非常像,所以我特別理解他們那種狀態。寫了很多發了很多,但仍藉藉無名,這是沒辦法的事。剛才說微妙,這個微妙無處不在。對我自己來說,最重要的是心態調整得好,為什么心態調整得好,因為這么多年一直在底層,90年代發四個中篇也不會想自己會領“魯獎”,因為你就是最基層的作者,離文壇很遙遠。
過去我一直做群眾文化工作,也主編小的文學刊物,周圍也有一些業余作者,全國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文學創作隊伍,都是很基層的業余創作隊伍,我就是在這個層面跟形形色色的作者打交道,昨天在高鐵上還有作者給我發稿子。有些人總覺得自己寫得好,別人說什么他都不相信。 但話說回來,生活中戴有色眼鏡的人很多,有慧眼的人不多,最近《收獲》上發了我的一個中篇,編輯寫的梗概里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沒有人有一雙慧眼,歷史總在事后睜著無用的雪亮的眼睛。
總有人說我大器晚成,因為人家不了解嘛,我從事寫作辦刊物輔導作者,一直都是在這個行當里,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后來好多內部刊物,像是山東的、河北的天津的、區縣級的內部刊物,都向我要稿子,要發《我的李海叔叔》,想讓他們的作者看看——因為我是從這樣的隊伍中成長起來的,我獲獎也讓很多人對文學燃起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