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積極心理學火爆到了什么程度?在哈佛大學,積極心理學超過了曼昆的經濟學導論,在選修課程中人數排名第一。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心理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喻豐在最新出版的隨筆集《遇見幸福》中稱,他在西安交通大學講授積極心理學課程時,“凡選課必過千人,凡上課必擠滿教室”,教室里不僅有選課的學生、旁聽的同學,還有心理學同行甚至外地來的愛好者……
積極心理學火爆的另一面,是社會上涌現出了多種多樣、令人眼花繚亂的幸福方法論。受到認可的學院派積極心理學和雞湯民科的區別在哪里?積極心理學和我們常說的“正能量”是不是一回事?在《遇見幸福》出版之際,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專訪喻豐,就如何看待積極心理學成為一門顯學展開了探討。
他在《遇見幸福》中向讀者提供了一些積極心理學的知識和方法,尤其強調一顆“主動的人心”,指人應該主動、理性地思考生活和追求幸福。在采訪中,喻豐也對不同的“積極”做出了區分。他認為,“我能夠被人利用說明我自己還有價值”這樣的積極不是真正的積極,所謂“狼性文化”中的員工也不是真正的積極;真正的“積極”是讓人出于內在的興趣,朝著發揮自己美德和優勢的方向去發展。

一種常見的批評是,過度迷戀幸福、僅僅關注個人內在情感可能會遮蔽一些重要問題,例如社會和企業的責任,是一種符合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社會哲學。對此,喻豐看到,積極心理學是一個微觀學科,無法像社會學、政治學那樣進行宏觀思考,他說這門學科告訴人的就是,“哪怕在非常悲觀的情況下,你也可以積極地來做個體能做的事情。”

01 幸福真的可以商品化嗎?
界面文化:《遇見幸福》談到,積極心理學成為了一門顯學,而顯學則容易成為庸俗之學。能談一談這方面的具體體會嗎?
喻豐:體會太多了。自從積極心理學開始熱門,一下子就特別火。本來積極的東西就沒有消極的東西深刻,而且一旦大眾化,也往往難以很深刻。為什么積極心理學很容易大眾化?因為教人開心是有吸引力的。市面上就會有很多人開始做積極心理學的事情,如果確實能夠幫助到別人,掙錢也是應該的,但是正兒八經經過科學訓練來做這件事情的人相對不多,憑著一腔對生活的體驗就來干這個事兒的人,數量是我們這些科研人員的百倍千倍。科研人員做了許多實驗才能說一句不那么滿、推廣性不那么強的話,社會人士卻可以說很極端的話,創造出的一些自己的方法,讓積極心理學變成一個有些魚龍混雜的行業,這也讓不少學者很困擾。
界面文化:因為是顯學,積極心理學似乎很容易和消費聯系起來,讓幸福變成一種產業。你是怎么看待幸福商品化這種現象的?
喻豐:我出書也是幸福商品化了,也沒什么不好。因為公眾需要有了解如何科學地幸福的渠道,而科研人員跟公眾之間的距離又特別遙遠,中間給公眾傳遞信息的是熱愛積極心理學的社會人士。商業化的好處是有可能讓公眾能夠接受到一些好的信息;另外,公眾花錢就是投入了,對一件事情有沉沒成本,就更有可能真的去做這件事情。但壞處是有可能讓信息變得爆炸,人們需要在紛繁的信息里面去尋找可信的信息。
界面文化:既然市面上的積極心理學作品魚龍混雜,有沒有什么積極心理學作品比較適合普通讀者看的?
喻豐:都適合普通讀者看,積極心理學的內容就是寫給普通讀者的。馬丁·塞利格曼(美國心理學家、教育家、作家,被稱為“現代正向心理學運動之父”)就說,積極心理學是脖子以下的,也就是更多是去做的,而不是去想的。科研成果也是服務于普通人的。
社會人士引用的一些東西其實有一定的來源。比如正念這個概念特別火,這是積極心理學的一個研究點,正念時人會進入一種意識相對集中的狀態,會心跳減速,感到平靜。民間就有很多人把它聯系上一些離奇的東西,例如喝茶可以正念,喝咖啡也能正念,聽講佛法也能正念。但引入這種概念其實是需要做實驗的,是需要經過科學檢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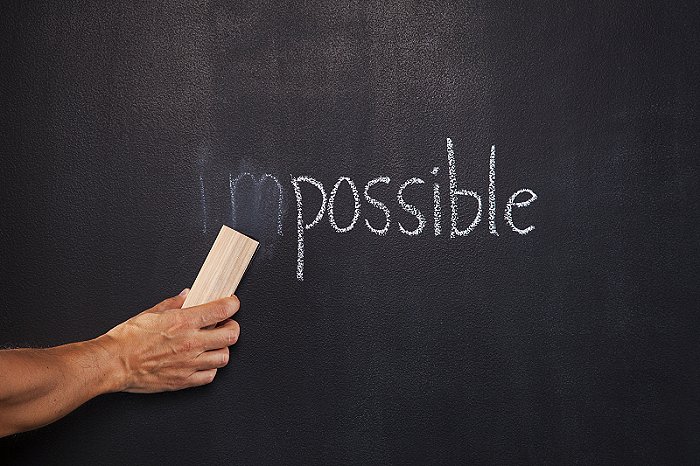
界面文化:積極心理學跟所謂“正能量”有沒有關系?
喻豐:積極心理學是在傳播正能量嗎?倒也是。積極心理學是一種心理學內部的思潮,把心理學朝某個方向上導引,肯定不是某種人的內在的能量。在量子力學出現之前,所有的偽科學、民哲都喜歡說能量。從普通人的理解上來說,積極心理學肯定更偏向于正能量,而不是負能量。
界面文化:有人批判“正能量”和積極心理學在社會范圍內似乎形成了一種霸權,但你不認可這種觀點。
喻豐:社會層面上可能有霸權,純發表層面我認為沒有。一些學者認為做消極的東西更難以發表,我不這么覺得,我在很多雜志做審稿工作,退稿的更多還是積極的內容。雜志上發表的文章,雖然積極心理學的比例在上升,但從數量上來說,其他內容還是多于積極心理學的。
界面文化:是不是學積極心理學的學者會比較積極,做精神分析的學者比較消極?
喻豐:不能說消極,每個學者都會受自己所學的東西影響。精神分析強調人的潛意識,強調人的早期經驗,就會把人朝著潛意識的方式去理解,會盡量把原因扯到小時候、原生家庭的各種事情上,否則很難用理論來聯系實際。每個學科都會給做這個學科的學者帶來一些烙印,人也不可避免受到自己習得那些理論的影響,用自己獨特的方式解釋世界。
積極心理學解釋世界的時候不看過去,我們傾向于覺得過去就過去了。如果你覺得它有很大的影響,它就有很大的影響;如果你覺得沒有那么大的影響,就沒有那么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人生還有很長,你未來還有潛能可以開發,還有自己的優勢可以應用,這些跟過去沒有那么大的關系。
02 幸福可以量化嗎?快樂積極是個體的責任嗎?
界面文化:我看積極心理學的一些內容,好像總是設定了一個特別完美的狀態在那里,但一個人總是離那個最理想的完美狀態很遙遠,總是有什么缺陷,有某種品質需要提升。積極心理學是不是會帶來這種新的焦慮和自責,或是某種自我提升的執念?
喻豐:你看我的書應該不會有這種感覺,我沒有設定一個很完美的形象,我甚至說人性都不是善的。我接觸過在中國做積極心理學的老師,他們常常秉持人性善的想法,人性不善怎么積極心理學?但我設定了一個很低的標準,就是相信在壞的情況下,一個人還能選擇做一些好的事情。
積極心理學不是要你完美,而是要你找到自己的長處和優勢,把它們發揮出來。每個人都達不到自己的上限,人就是要接受自己永遠達不到自己能夠達到的上限的狀態,但是你知道哪個方向能去做就好了,朝著發揮你自己美德和優勢的方向去就好了。你有一種內在的志趣,這樣去做你高興,至于能達到什么樣的成就,那是之后的事情了。

界面文化:有種意見會指出,我們這個原子化社會,社會隔離已經造成了很多的孤獨感。這個時候追求幸福其實可能有以自我為中心的問題,加劇人的自私自戀,加深孤獨感。但是我從你的書中看到,你其實有好幾篇文章是在講人和人關系的。所以這些批評有沒有道理?
喻豐:我的好多篇文章都是講社會支持的,從積極心理學角度上來講,一個人如果缺了社會支持,沒有朋友,會缺乏自尊,這很痛苦。社會拒斥,或者叫社會性死亡給人造成的負面心理結果極大。實際上我講的是人的主動性、能動性,能動性不完全是自私自利,而是我們能主動地、有一種內在動機驅使地去做某件事情。我要去主動做,不是別人逼迫我來去做。而我主動做的這種事情可能是利己的,也有可能是利他的。那就是一種選擇。
界面文化:積極心理學好像總是在量化幸福,比如說一個人賺的錢在什么區間內,幸福感如何變化,幸福是可以量化的嗎?這樣是不是一個人的快樂也好像變成了KPI?
喻豐:因為要做實證研究,就不可避免要量化它。最初的積極心理學研究就很淺顯,就是做金錢和幸福感的關系——有錢幸不幸福,有多少錢才幸福,這是日常生活中老百姓最關心的事情,也是最容易做的事情,這就是最早量化的由來了。
我們在研究的時候會用正向負向情緒量表,讓你給自己的情緒打分,把快樂或悲傷的程度從1到7打個分。對人心的測量就是這樣,只能把它當成一個連續體,進行分割,做出量化,不是一個特別精確的值。心理學上認定快樂是個積極情緒,悲傷是一個消極情緒,但有的情緒是混合的,比方說敬畏的情感是想靠近又想遠離,這種情緒就是積極和消極混雜。還有一種情況,比如悲喜交加,是一個人可以同時加工積極和消極的情緒。
積極心理學有一個積極比,也就是消極情緒和積極情緒混合在一起的比例,大概是8:2,也就是8分的積極情緒和2分的消極情緒。還有一些其他的比例,比方說夫妻關系的研究中,夫妻之間有一件糟糕的事情發生,比如兩人吵架,大概吵一次要做5-8件好事才能抵消回來。你產生了一絲消極情緒,得要產生強度大于它5倍的積極情緒才能補回來。
界面文化:剛才談到金錢和幸福感的關系,比如積極心理學會認為,人的收入超過了一定數目,對幸福感的影響就沒那么大了,這是不是可能讓我們忽視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
喻豐:有可能會產生這樣的感覺,這個結論你也可以把它講成沒錢肯定不幸福,有錢也不見得幸福。這樣解釋的話,對沒錢的人來說,最重要的還是錢,但有了一定金錢之后,錢也就沒有太多的作用了。所以,人究竟怎么去尋求幸福?還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的。積極心理學就是幫助你找到這些方式方法。
界面文化:這是不是有一種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個人的感覺,好像社會就不需要承擔什么責任了。
喻豐:積極心理學很想去影響政府決策,不過不容易。每個人身處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你當然可以抱怨,但你也可以想把它變好。雖然以你一己之力很難變好,那我教你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夠讓你自己過得幸福快樂一些。哪怕在非常悲觀的情況下,你也可以積極地來做個體能做的事情。

界面文化:也不光是國家,比如企業老板也會讓勞動者積極起來,認可諸如“996是福報”那一類說辭,好像企業也不要負什么責任了。
喻豐:我們做過積極企業的項目,讓企業有積極向上的文化不是個人的事情,是企業上下之間的配合,也是人和人之間交流的問題。有一些基于企業的研究發現,積極心理學提倡的積極或者是道德的企業文化,不會讓公司的凝聚力和業績下降,但要看領導愿不愿意冒這種風險。
積極的企業文化不是那種“狼性”的企業文化,我們不覺得“狼性”文化是有內在動機在驅使的,我們想要創設的是一種隨和、平靜、有愛的文化,讓員工充滿內在的動機,讓他們自己想要去做,而不是后面拿個皮鞭抽你。企業的事情很復雜,但基礎的理念就是找到每個人的優勢,然后發揮優勢——這個人有領導力,就讓他/她當領導;這個人的優勢是公平,你讓他/她去干薪酬;這個人的優勢是對美的欣賞,你就讓他/她去把關設計。調動員工的這種內在優勢,公司不用“996”勝似“996”,因為大家做事情都很有興致。當然很多時候,企業文化不是由員工自己兩兩之間交互或者是一群人之間交互就能創設出來的,更多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似乎做這件事情的前提是要改變企業領導人,把他/她變成一個信奉積極心理學的人。
積極企業并不像積極教育那么容易。教育好做一些,因為雖然成年人有時候是邪惡的,但大家都希望小孩子生活在童話里,成年人的“狼性”大家能忍,但讓小孩子“狼性”大家不能忍。傳統教育理念是衡水中學那樣打罵逼和應試,孩子被摧殘得特別慘。用積極心理學的方式找到這些孩子的優勢,讓它得以發揮,孩子的內在動機就會出現,成績自然而然也會提高。這樣的方式大家非常容易接受,我認為家長和老師對孩子的期望多半是童話式的,不想讓孩子接受社會黑暗的那一面。
界面文化:哲學家韓炳哲在《倦怠社會》里就有講新自由主義下的個人的自我剝削,你怎么看待這種“積極”?
喻豐:這用心理學的話來說叫自我非人化,即覺得自己是個機器,不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經常聽到“我能夠被人利用,說明我自己還有價值”這樣的話,為什么要加這句解釋,從心理學角度上來說,這叫認知失調——我的內心不能承受這件事情,但是要給我自己一個理由,如果不給我自己一個理由,我會崩潰。
這是社會病態的結果,從積極心理學觀點來說,我們不覺得這種情況是人真的出于內在興趣來做事。這是一個你不感興趣的事情,非要去做,然后給自己強加的理由,因為依靠內在興趣來做事是不需要理由解釋的。
界面文化:剛才我們討論了這些,你其實挺悲觀的。
喻豐:我也許是挺悲觀的。心理學不像社會學、政治學那樣進行宏觀的思考,它是微觀學科,微觀學科就是在你不能宏觀地做什么的時候,對自己做些積極性的事情,調試看待自己的方式。
03 積極心理學對所有心理學子學科都有“染色”作用?
界面文化:可能讀者較早接觸積極心理學是哈佛幸福課,這個課當時的熱度超過了曼昆的經濟學導論,成為了哈佛最受歡迎的課,能不能稍微講一講積極心理學在中國是怎么引發重視和關注的?
喻豐:Positive psychology這個詞在英文世界里流行起來,是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我的導師彭凱平教授是清華心理系主任,他2008年回國復建清華大學心理學系,認為清華大學心理學系要找一個研究的方向,不和傳統研究方向離得很近,那樣就沒有特色和優勢,但也不能太脫離大眾,所以就找到了積極心理學,他自己也受到了積極心理學理念的感召。我2010年到清華大學讀博,是他第一個博士。現在積極心理學做得最好的就是清華,今年12月6日積極心理學專業委員會在清華成立,似乎才標志著中國心理學界開始認可積極性心理學作為一個學科方向的確立。
界面文化:書中你有談到,亞伯拉罕·馬斯洛(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第三代心理學的開創者)提倡“積極心理學”,他是從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個體心理學創始人,人本主義心理學先驅,現代自我心理學之父)《自卑與超越》當中得到的啟發。你還談到,“積極心理學”混雜在存在主義、人文主義甚至個人體驗中。作為一門學科,積極心理學的思想來源究竟是什么?
喻豐:馬斯洛學術背景很復雜,他是出身于行為主義流派的心理學家,最后變成了人本主義的心理學代表人物。馬斯洛博士論文做的是猿猴的支配權和性行為,他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就拋棄了這個方向,覺得人應該像人,人應該有人的尊嚴,發揮人的潛能。他在《動機與人格》里提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需求層次理論,這本書的最后一章叫Toward A Positive Psychology,朝向一種積極心理學,他認為人本主義心理學會朝向一種積極心理學的方式去發展,但并沒有說清楚這是什么東西。

人文主義強調個體,強調個性,和現在西方流行的思潮幾乎類似,馬斯洛也是這樣,特別強調人的主動性,強調人的潛能,強調人可以成為最好的自己。有心理疾病不要怕,你有潛力戰勝自己的心理疾病;自卑也不要怕,你有潛力超越自卑。這是從阿德勒那兒來的思想。存在主義心理學,簡單來說就是人人都有存在焦慮,比如死亡恐懼,我們面臨各種各樣的威脅時會產生一些心理反應,產生某種固定看法或者意識形態,影響人之后的行為。一旦產生了存在焦慮,人就會覺得喪失控制感,就想要補償,找一些自己能夠控制的事情來做。存在主義心理學的宗旨就是要靠發揮人的潛能來愈合存在焦慮。
馬斯洛出身行為主義流派,這個流派是約翰·華生最先倡導的,華生出身于功能主義心理學,功能主義心理學和美國當時最主流的實用主義哲學有關。按照心理學講實用主義來說,說清楚事情的功能比說清楚事情本身的結構要更加重要一些。也就是說,心理學要有用。馬斯洛反對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有用,但是他的用處是神經病心理學,只對神經病人有用,馬斯洛覺得要對所有人都有用。他也反對華生——華生也有用,但那是小白鼠心理學,只對動物有用,對人來說沒有太多作用。
積極心理學的創始人是馬丁·塞利格曼,他原來也研究行為主義心理學,做臨床咨詢心理學,跟馬斯洛一樣研究小動物。他做了一個成名作,把老鼠裝在籠子里,外面放吃的,老鼠出去吃東西,一出門就電擊,一直到老鼠眼睜睜看著你把電擊裝置拆掉,外面再放吃的,老鼠很餓,但再怎么誘惑都不出去吃了。這就是習得性無助,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面臨老鼠那樣的境況。他于是就想,能不能不要習得性無助?能不能習得性樂觀?他來清華時我們聊天,他說女兒出生了,就覺得不能把他女兒像動物一樣關注,在教育女兒的過程中,他認為原來的教育似乎都沒有關注孩子本身的優勢和天性的發展。傳統心理治療是治療心理焦慮或者抑郁,而他指出大部分人沒病,把人的天性潛能發揮出來是重要的。

界面文化:馬丁·塞利格曼提出積極心理學之后,它就在美國流行開來了嗎?
喻豐:馬丁·塞利格曼1999年當上了美國心理學會的主席,在致辭上做了一段演講。他說,傳統心理學有三大命題,第一個是治療心理疾病,第二個是尋找天才兒童,第三是發揮人的優勢和美德,似乎我們都忘記了后面兩個主題。他當美國心理學會主席,就要扭轉心理學研究的方向,把原來傳統的主題重新拾起來。他于是開始倡導積極心理學,找了一批研究幸福、道德、審美這些更積極話題的心理學家,在美國心理學會的旗艦雜志上發了一期專刊,就叫“積極心理學”,他把自己的致辭寫成引語放在最前面,從這時起,積極心理學才正兒八經開始火了。雖然他之前也做過一段時間積極心理學,但如果沒有當美國心理學會主席的經歷,我想可能也難流行。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認為,積極心理學的主題不僅是幸福,而是一種思潮,一種研究偏好,和一種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個人選擇。積極心理學對任何心理學子學科都有“染色”作用,能不能講講具體是什么意思?
喻豐:有人會把積極心理學當成心理學的子學科,也就是一個獨特的研究方向,我覺得不是。因為不管做什么,都可以從積極的角度上做,也可以從消極的角度上做。現在做心理疾病的方法是什么?我們進行分類,說這個叫心境障礙,這個叫焦慮障礙,這個叫人格障礙,心境障礙里面又有200多種分類。我們也可以用積極的方式來做,把人的優點進行分類,就是對同樣一個事情你怎么看。再比如組織管理心理學,你可以研究員工的職業枯竭、職業倦怠,研究他們為什么干不下去,你也可以研究員工的幸福感。像消費心理學,原來研究人在壓力的時候進行購物,現在也有很多人研究消費者的幸福感。所以我覺得對于心理學所有的子學科來說,積極心理學就是一個思潮,讓人知道這些概念還有反的一面,也可能是好的一面。

喻豐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