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王芊一 記者 姜妍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本月初,第97屆奧斯卡在一片爭議聲中落幕,不少觀眾為《某種物質》近乎“陪跑”抱不平。這部2024年的爆款電影,把小眾的邪典驚悚元素毫不客氣地扔到了觀眾面前。盡管也得到了不少“精神污染”“惡心”的評價,但它的爆火也表明——觀眾對于“精神污染”的接受閾值越來越高了。
網絡小說和電影構建了一個又一個“瘋掉”的世界和“瘋掉”的主角。在《道詭異仙》里,是分不清自己要殺怪物臘月十八還是幼兒園小女孩的李火旺;在《我不是戲神》里,是發現自己的記憶和身份是虛假的陳伶;在《博很恐懼》中,是在暗流涌動的生活中發現閣樓上囚禁著巨大生殖器怪物的博(Beau)。這些在過去被視為小眾審美的作品,卻在近年間,成為了新的流行趨勢。
這些作品帶給我們一種新奇的感受,互聯網討論自發地將這種感受稱為“精神污染”:讀者和觀眾跟隨著主角進入了一個個詭異、惡心或獵奇的場景中,在主角置身的世界里,瘋狂與清醒只有一步之遙。主角的精神狀態也觸發了讀者和觀眾抑郁、恐慌與焦慮的情緒,但人們卻依然控制不住地想繼續看下去。這種如此吸引我們的“精神污染”到底是什么?為什么人們一邊恐懼,一邊迷戀著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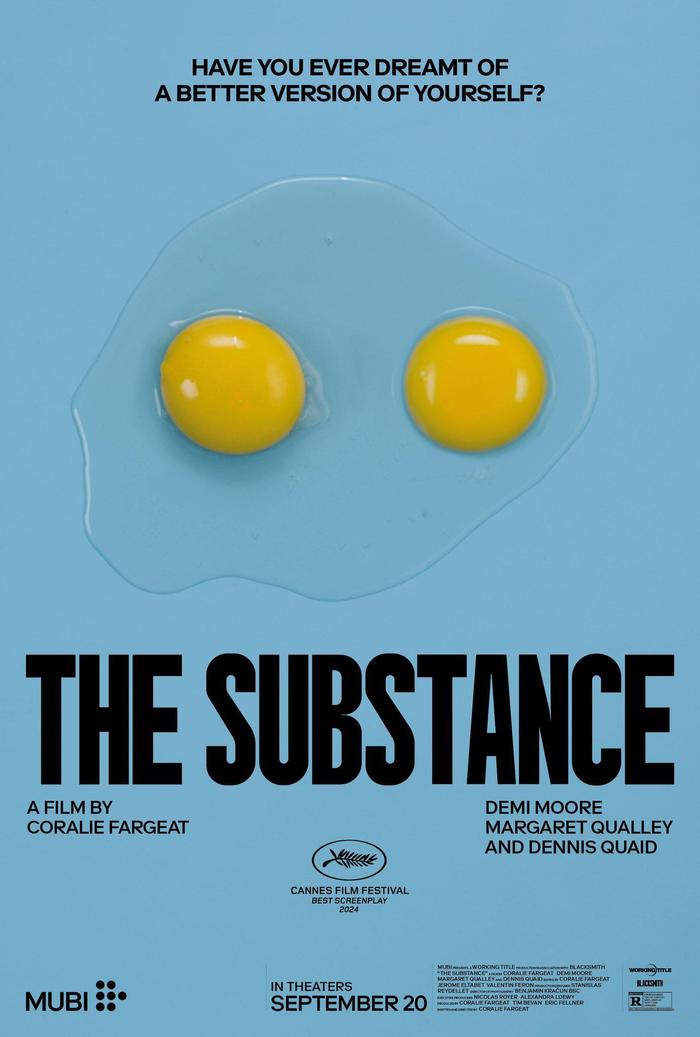
互聯網的鬼畜現象和克蘇魯世界觀
“精神污染”一詞借用自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這一政治活動是在改革開放的語境下提出的,旨在清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污染,主要污染來源是某些文學、藝術、音樂等。如今,網絡上的“精神污染”一詞早已脫離了當時的語境,僅僅保留了原義的兩個特點:污染的隱蔽性和對精神世界的直接作用。事實上,“精神污染”現在的內涵主要來源于互聯網的鬼畜現象和克蘇魯世界觀。

鬼畜創作近幾年在互聯網上已顯頹勢,但是它對于“洗腦”的追求仍影響著流行文化。鬼畜最早的形式是音MAD(對音視頻進行二次加工并使其充當和替代原曲),由于中國互聯網上最早出現的音MAD視頻標題有“鬼畜”一詞,網友就將這類視頻稱為鬼畜視頻。鬼畜視頻迅速與中國互聯網文化相結合,發展出一條新的道路。創作者將音視頻快速重復地剪輯起來,配上動感的背景音樂,形成“洗腦”的效果。相比于鬼畜,克蘇魯世界觀有著更長的歷史,這一神話體系出自1928年洛夫克拉夫特發表的短篇小說《克蘇魯的呼喚》。在克蘇魯世界觀中,人類作為極其渺小的存在,若是對浩淼無垠的世界探究太深,直面世界的真相,就會導致理性崩潰、知覺發狂。后來,克蘇魯世界觀不斷擴展,并出現了各種衍生作品。在小說同名桌游中,SAN值這一概念第一次出現。SAN值直譯為理智(sanity),即玩家的理智程度。當玩家遇到各種邪神的時候,SAN值就會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的玩家會進入發狂狀態。在現在的網絡文化中,當人們看到詭異、惡心、獵奇的事物時,就會用“掉SAN值”來形容自己的精神狀態。
精神污染一詞發源自上世紀80年代,綜合了鬼畜的“洗腦”和克蘇魯的SAN值設定,最終糅合成一個網絡上被廣泛使用的流行概念。現在,當我們使用這個詞時,一般是用來形容流行文化中的視頻、文字、圖片、音樂等等將人帶入瘋狂、惡心、詭異的氛圍中,使接收者感受到心理上的不安與不適,卻又無法抑制地回想起這些片段。
分不清真實與幻覺的體驗感
2018年,由A24出品的《遺傳厄運》催生出一種新的恐怖片類型:高級恐怖(elevated horror)。與依賴怪物、血腥、跳嚇(jumpscare)等外部威脅的傳統恐怖片不同,高級恐怖更依賴行為、情緒和認知紊亂的角色,在對現實的隱喻和象征中,營造出心理上的壓抑氛圍,也就是一種精神污染。盡管這一名詞受到了“新瓶裝舊酒”的質疑(更早的一些恐怖電影,比如1968年的《羅斯瑪麗的嬰兒》其實也是高級恐怖),但是這類電影從未如此廣泛地受到大眾歡迎,這代表了觀眾對于恐怖片的期待發生了變化。

2023年,《遺傳厄運》的導演阿里·艾斯特的新作《博很恐懼》上映。盡管該片被導演定位為黑色喜劇,但是觀影過程卻絕不輕松。正如一位豆瓣網友的高贊評論所說的“不僅博很恐懼,我也很恐懼”,博的情緒完全污染了觀眾的神經。影片從開頭就滲透著日常的焦慮和詭異的無序。作為焦慮癥患者,博開始服用一款新藥,但是這款藥必須就水服下,否則會有致死的副作用。吞下了藥的博卻發現礦泉水喝完了,家里又莫名停水,于是他不得不穿越混亂無序、到處都是可疑的邊緣人的街區。在他冒險穿越街道的時候,這些邊緣人侵占了他的家,將他的房間搞得一團糟......博的日常生活充滿了幻覺與妄想、象征和隱喻,無論他走到哪里,都沒有所謂的安全。帶入博視角的觀眾,也仿佛陷入一場夢魘,或者是一幅超現實主義的畫作中——萬事萬物都并非其表面的樣子,空氣中飄散著不祥、詭異的征兆與氣息。
同樣在2023年,網絡小說《道詭異仙》成為當年首部連載期間就突破10萬均訂的作品。主角李火旺比電影中的博瘋得更加“外放”。他無法分清自己到底屬于哪個世界,是在充滿了怪譎邪祟的修仙世界,還是正躺在精神病院的床上接受治療?小說的第一個高潮是李火旺試圖借助現實世界和修仙世界的聯系,在現實世界殺死邪祟臘月十八。他一路追蹤到一個別著紅色發卡的幼兒園小女孩,正當他對小女孩舉起玻璃時,媽媽卻苦苦哀求他不要這樣做。徹底陷入迷茫和崩潰的李火旺于是發出了貫穿全書的一句吶喊——“媽,我真的分不清”。其實,分不清真實與幻覺的不僅僅是李火旺,也是每一個讀者的閱讀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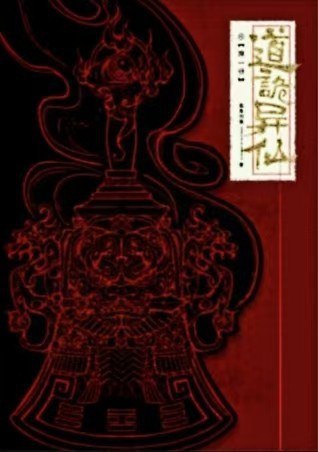
版本:三月兔亭有限公司 2025-1
將精神病患者作為主角的設定在網文中并不新鮮。2011年,豆子惹的禍開始連載一部以精神病患者為主角的網絡小說《神經天下》,主角董陽逃出精神病院,向西進發準備參加倫敦奧運會,卻在路上被閃電劈中穿越到異世界。自此之后,《驚悚樂園》、《玩家兇猛》、《地獄app》等一系列作品都塑造了與眾不同的主角。但是,這些主角與其說是有精神疾病,不如說是行為邏輯比較清奇的怪人。這類“精神病流”小說(即主角的精神狀態“異于常人”的小說,又稱崩壞流)輕松愉快,主角并不迷茫和痛苦,行為邏輯更是一以貫之。在與“正常人”的互動中,他們獨特的腦回路甚至使他們占據上風。這類“精神病”主角,帶給讀者的反倒是充足的安全感。
但是,從《道詭異仙》開始,網文主角真正開始變得瘋狂、迷茫和痛苦,讀者被迫體驗到主角內心世界的掙扎。當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都變得不可理解,主角的心靈是不可信的,主角眼里的世界更是不可信的,原來寄托于主角身上的安全感便蕩然無存。正如學者王雨童在《莫比烏斯式現實:網絡文學中的克蘇魯風格及其癥候》一文中所指出的,“恐怖世界不僅侵入了日常生活的外部,還會侵擾自心底生發的‘內部的外部’”,新的恐怖開始更多地發生在熟悉而又陌生的內心世界中。
在恐懼和錯亂中探索內心
在這類精神污染的作品下面,總能看到“心理狀態不好者慎看”等評論,但仿佛自虐一般,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點開它們,并從中感受到一種復雜的快感。這種快感不能簡單用“享受驚嚇”來解釋,因為相較于《咒怨》《電鋸驚魂》等經典恐怖電影帶給人的感受,精神污染式的作品吸引我們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有多恐怖,而是它太奇怪了。當代文化理論家馬克·費舍在他的遺作《怪異與陰森》中也描述了這種現象——我們對于奇怪事物有一種癡迷,它關乎一種對外部,對常規感知、認知和經驗所不能及的東西的著迷。使我們著迷的正是怪異(the weird)與陰森(the eerie)。

新行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11
費舍認為怪異就是一種錯誤的感覺,即一個怪異的東西怪得讓人覺得它不應該存在于此地。當外部的某物對此世界產生了入侵,這就是怪異出現的標志。因此,怪異的事物必須存在一個現實的對照物。比如,在《道詭異仙》中,無論是修仙世界本身還是現代世界本身,都沒有那么怪異,但是當兩個世界相互滲透,真正的怪異便出現了。同樣地,這種怪異也出現在《博很恐懼》中。電影里,博總是在跨越不同世界之間模糊的界限:推開平凡的閣樓門,里面藏著不屬于這個世界的怪物。劃船從河道逃入洞穴,卻進入了一個坐滿觀眾的審判場......所有的世界都令人懷疑,顯得不自然。而在另外一部爆火的網文《我在廢土世界掃垃圾》中,一個經常被提及的精神污染的情節就是女主在被污染的牙醫館里,發現患者的每顆牙齒里都有一個小人在痛苦地大喊。此時,讀者感到精神污染的原因也正是在于作者將日常世界扭曲,將平常看牙的經歷與讓人掉SAN值的怪物并置。
陰森則被定義為一個關于自我行動能力的問題。陰森的存在往往是帶有懸念的,某件事發生了,我們卻不知道是否有一個具備自我意識的存在推動了這件事的發生,更不知道推動事件發生的到底是什么,它為什么會消失?一切都是缺席的。進而,這種陰森導致我們對自己的感知能力產生懷疑,我們無法理解支配自己生活和整個世界的力量。在《博很恐懼》的第二幕里,我們感受到的就是一種典型的陰森。博住在一對夫婦家里,意外地發現他們家里的監控能快進看到自己的未來:從馬上要闖進來的小女孩,到那只將載著博去往死亡審判的小船......它們飛速地閃過。可是,監控為何竟能播放博的未來?誰在控制著博?此時,命運這種非人的存在卻仿佛存在著自我意識,對博展現出了陰森的惡意,令人狂掉SAN值。
讀者和觀眾對于精神污染的著迷,首先就來自于我們和主人公共享這個“瘋掉”的、怪異且陰森的世界,并對此產生了同樣的困惑。以《我在廢土世界撿垃圾》為例,這部小說借“污染世界”來暗喻現代社會的一系列問題——加班、房貸、容貌焦慮、藥物成癮等等。“精神污染”區別于一般恐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常有極高的社會隱喻性。恐怖作家協會主席約翰·帕利薩諾(John Palisano)試圖解釋為什么近年間社會恐怖終于得到了應有的關注,他說:“恐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向所有世代的人訴說著。在 20 世紀 50 年代,它讓人們有辦法應對原子彈的恐懼.......在 80 年代,它涉及艾滋病。現在,整個國家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來自內部的威脅。”當然,帕利薩諾所指的國家特指美國,內部的威脅也主要強調的是美國政治上的分歧。但是,這種內部威脅并不僅僅局限在一兩個國家,而是疫情后許多國家都要面對的社會問題——分歧、沖突和不穩定因素加劇。怪異與陰森的社會和我們所處的現實社會充滿了共通之處,許多不應該出現的事物突然出現,許多應該出現的事物卻遲遲不肯現身,我們無法理解和控制這個世界。在費舍看來,怪異-陰森概念不僅是對恐怖文化的分析,更是對它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格局的反思。正是這種對于社會現實的困惑,吸引著我們進入“被污染”的世界,帶著恐懼觀看詭異而令人不安的現實。
其次,對“精神污染”的癡迷還來自于我們對于內心世界從未有過如此強的探索欲望。2022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世界精神衛生狀況的綜述,指出全球近10億人(包括全球14%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礙。而大部分“精神污染”的作品都與精神疾病相關,比如《博很恐懼》與強迫癥、《危笑》和抑郁癥,以及《道詭異仙》與精神分裂。在這些作品中,主角最終極的恐懼永遠是對自我的懷疑——“我”在哪里?“我”是“我”嗎?為什么“我”會這樣做?誰在對“我”做什么?人們對于“精神污染”類作品這種恐懼又著迷的態度,與他們現實的心境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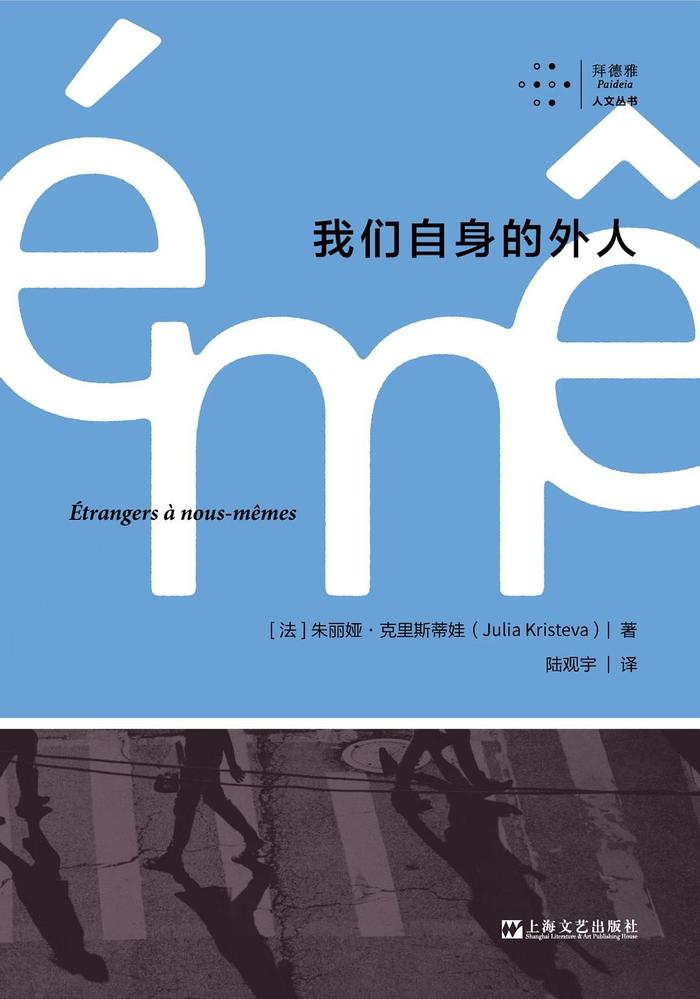
拜德雅·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2-11
哲學家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在《我們自身的外人》一書中探討了類似的問題——外人的問題。在這里,外人也可以代表著一切陌生性,比如精神疾病。她在弗洛伊德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觀點:“要承認我們的怪怖,我們對它的忍耐與享受,都不在外部。怪異就在自我身上,因此我們都是外人”。這句話說明:我們對精神疾病好奇且恐懼,恰恰在于這種怪異也在我們自己身上。每個人的自我都不是簡單的統一,而是存在不協調的部分、陌生的部分,讓我們自己都無法理解。作為一個“正常人”,在生活的某個瞬間,總會或多或少感到自己處于瘋狂的邊緣:身體里躁動的自毀的欲望、暴力的困擾、一閃而過的病態感受......這些模糊的、被壓抑的自我往往渴望被釋放,這就構成了對精神污染的癡迷;而在遭遇精神污染的時候,自我可能會再次回歸,這就構成了對“精神污染”的恐懼。
此時此刻,當人們轉向外部,沖突和不穩定因素加劇;當人們轉向內部,內心世界瘋狂而迷亂,“精神污染”類的電影和小說,就提供了一個合適的空間:在怪異和陰森中反思現實,在恐懼和錯亂中探索內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