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鏡相工作室 黃依婷
編輯丨趙磊
華為存儲產品線測試崗員工向洋新來了個同事,985理工類高校畢業,和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簽的勞務派遣合同,也就是OD,職級為D3,對應到華為正編職級,比他還高一級。向洋感到有些開心,終于有人可以分擔組內的工作了。
很快,他察覺到不對勁——新同事的代碼能力幾乎為零,腳本不會跑,部署不會做,連最基礎的python循環語法都不會寫。“怎么過的機考?”這個疑問盤桓在向洋和其他同事的腦中。
在華為,OD員工的招聘流程一般有五輪,分別是線上機考、綜合(性格)測試、技術一面、技術二面、HR面,如果兩輪技術面試判定的職級不一致,會再加一輪主管面試。
招聘流程嚴格,但難免有疏漏。3月10日,華為對內通報ICT產品與解決方案等多部門多人在OD招聘中的舞弊腐敗行為,共處理62名正式員工,其中,開除或勸退員工36名,閃存存儲產品線為重災區。
向洋在違規當事人名單中看到了熟悉的名字,他們都參與了新同事入職事宜,“替考的是勸退,運作招聘流程的是開除”。事發后,違規當事人跟向洋說,沒想到幫了一個小忙,把自己搭進去了,還一分錢沒拿到。
作為科技巨頭,華為對違規人員的處置反映了其對舞弊腐敗行為的零容忍,這與騰訊、字節跳動、美團等大廠的步調是一致的。但大廠規模巨大,每年招聘數千上萬人,具體到招聘環節,類似的事情時有發生,且舞弊手段越來越難以察覺。
當OD、外包成為流行的用人模式,當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幾乎壟斷招聘渠道,當拿著瑕疵簡歷的名校畢業生站在求職路口,一條灰色產業鏈無聲無息地運作起來,鏈條上的每一個相關方都仿佛有所獲益,但又不得不正視那頭房間里的大象。
成為OD,又累又沒錢
互聯網語境中,OD是介于正式雇傭和項目制外包之間的用人模式,網友會用“華為正編>華為OD>中小廠正編>華為外包“的不等式表示其中的差異。
在華為,OD則是個特殊的群體。
OD員工和正式員工一起在華為辦公地工作,工作強度和頻率、加班待遇等,和同一團隊內的正式員工相差不大。但OD在身份層面上似乎總是“低人一等”:他們不和華為直接簽署勞動合同,和第三方的外企德科或科銳國際簽約,是通報里的“非雇員”;OD員工的工號通常以“300”開頭,而正式員工工號以“00”開頭;而更大的區別是,華為OD員工幾乎不參與涉及公司核心技術的工作,也無法享受華為每年的分紅。
OD員工的工資待遇幾乎是透明的。如,OD的D1職級對應華為正編職級的13級,月薪一般在9000元-13000元,年終獎取決于個人績效,2-4個月不等。
華為是從2018年開始試點OD用人模式的,到2020年全面實施。如今,成為華為正式員工的途徑幾乎只剩校園招聘,或應聘者本人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其他人想通過社招進入華為,大概率要走OD的模式。
在倡導小團隊作戰的氛圍下,華為OD員工的日子好不好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PL(項目組長)和PM(項目主管)的管理風格。
2024年6月,小西一畢業就成為了華為OD員工,從事開發工作,“累”和“卷”是他最大的感受。入職半年多,工作日每天上午九點半上班,晚上九點后下班,一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永遠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工作本身并沒有什么挑戰性,小西絕大部分時間都在“拉會”,自嘲是“抽空寫代碼”,根本沒時間鉆研技術。
而被外界所熟知的培訓體系也輪不上他,入職后遇到的大部分問題要靠自己解決,給他分配的導師很少有時間回答他的問題。小西談到這里時有些生氣,“導師就是甩幾個文檔給我,讓我讀讀阿里的論文啥的”,并沒有更多業務上的指導。在他看來,招OD本來就是把華為低職級的活解放出來,讓成本更低的OD去做,如果再讓華為正編員工帶,反而本末倒置。
但同樣是2024屆應屆生,清寒作為OD員工的工作體驗截然不同。他是其他專業轉行寫代碼,入職第一個月幾乎都在按照導師制定的培訓計劃學習,有線上課程,也有線下培訓班,培訓內容具體到代碼規范等方方面面。上班時間不長,組內要求每天打卡滿8小時就好。
和正式員工的差異造成了一些OD員工心態上的擰巴,甚至傳導至負責招聘的正式員工身上。
張千是華為海思員工,不久前招聘了一位OD同事。這位同事本科和碩士都畢業于一所985高校,是其他專業“轉碼(指轉行寫代碼、做程序員)”,之前也不太清楚OD究竟是什么。入職之后,她發現自己對業務的熟悉速度比較慢,壓力也特別大。
看同事狀態欠佳,張千心里不是滋味兒。他想,雖然薪資待遇并不差,也有華為做背書,但歸根結底,OD帶有外包性質,作為第一份工作,可能會污染簡歷——在這之前,張千已經聽到不少OD同事對此事表達煩悶。
小西把這種狀態概括為“不上不下”。在他的設想里,工作要么累,但有很多錢;要么沒太多錢,但有很多業余時間。而OD屬于兩不沾,既累又沒太多錢。
瑕疵簡歷碰上用人壓力
盡管成為一名OD員工有諸多弊端,仍然不斷有985、211高校的畢業生爭先恐后地投遞簡歷、參加機考。公開渠道流傳著一張華為OD招聘目標院校名單,其中有39所985院校、112所211院校和75所“雙非”院校——這些所謂“雙非”院校包括中國科學院大學、深圳大學、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等,綜合實力不能小覷。
張千解釋說,華為對OD招聘的具體要求并不嚴格,目標院校和機考是最難通過的環節,也正因為如此,公司要求OD員工具備極強的學習能力,可以在入職培訓環節快速吸收知識、接觸業務,而目標院校畢業生們已經踏過高考獨木橋,大概率很努力且學習能力不會太差。
擠破頭要成為OD的名校畢業生們,簡歷一般存在瑕疵,兩份工作之間有較長時間間隔、專業不對口、沒有項目經歷等。對于他們來說,一個只要努力就有概率在華為轉為正編的工作機會還是挺難得的。
小西有點特殊情況。臨近畢業,他的秋招offer被毀約,家人施加的壓力較大,在一位學長的建議下,他向華為OD投遞了簡歷。這位學長同樣是華為OD員工。流程很快,兩周左右就拿到了offer,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但簡歷有瑕疵的名校畢業生總是不可多得,更多人還是更愿意嘗試應聘其他大廠的正編。因此,華為許多業務部門長期處于缺人狀態。向洋在職期間,加班成為常態,辦公室徹夜燈火通明;為了趕產品測試進度,團隊幾個人輪流通宵,不讓機器閑下來。即使這樣,工作仍然做不完。
有別于其它科技巨頭,為了保障業務部門人員流入順暢,盡可能匹配用人需求,華為的HR很少參與招聘工作,一般僅是監督招聘流程的合規性,絕大部分招聘工作由業務部門管理層負責,核心就是“誰缺人誰招人、招適合團隊的人”。
這次招聘舞弊的重災區,存儲產品線是承擔招聘壓力最大的產品線之一。向洋在職的2022-2023年,整個存儲市場處于收縮周期,產品價格下降,各大廠商縮小產量、減少預算,華為也不例外,用人預算縮減了一些。與此同時,原有的運營商和企業客戶需求持續上升,研發、測試部門承擔了大量滿足客戶需求的責任,人力嚴重不足。
雙重壓力下,為了緩解人力困境,向洋的PL曾被拉到小會議室里,被他的上級盯著給投遞了簡歷的候選人打電話,邀請候選人前來面試,招聘OD還被納入了PL的考核內容。
為了更快招到人,基層管理者們也會把招人指標分配給手下的正編員工或OD員工,不同組之間也會互相推薦簡歷。據電廠報道,招到人之后為了感謝對方,負責人之間也會有轉賬等行為,而這些也是違規的。PL曾讓向洋承擔一部分招聘工作,被向洋以不在職責范圍之內為由拒絕——這在后來讓向洋躲過一劫。
業務部門的用人壓力也傳導至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王麗曾在外企德科負責招聘OD,白天在招聘軟件打招呼的回復率比較低,忙的時候需要加班到晚上八點多。按照要求,她每個月要招聘2位OD并辦理入職,幾乎每天都要在招聘系統中鎖定2份簡歷,每周要安排一次機考。這不是強制規定,但每個人需要上交日報和周報,工作數據會被放在一起比較,是一種無形的壓力。
HR努力,但招聘并不順利。畢業于目標院校的候選人們對OD的下意識反應是拒絕,“有偏見”;有意向應聘的候選人可能會“折損”在機考環節。實習期間,王麗的績效為0,她沒有幫助哪怕一位候選人入職。
或許正因為招聘需求旺盛、招聘難度較大,華為給外企德科的招聘提成比較理想。候選人定級為D1的,入職成功后為每人1500元,最高的能到4000-5000元。
OD招聘是如何變形的?
OD招聘是個正三角,拿著瑕疵簡歷、迫切找到一份工作的名校畢業生,依賴招聘服務費賺錢的人力資源公司,以及面臨著用人壓力的業務部門,三方需求碰撞下,“正三角”穩定且持久地運行,直到其中一方或兩方違背規則,開始扭曲變形。
華為OD的招聘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由外企德科、科銳國際這兩家人力資源公司篩選、推薦簡歷,組織機考,機考通過再交由用人部門推進后續流程,候選人成功入職后,華為向推薦簡歷的公司結算服務費用;
二是用人部門直接在招聘系統中搜索符合條件的簡歷,并推進招聘流程,幾乎不經過人力資源公司,華為也不需要向其結算招聘費用。
對于用人部門而言,如果都由自己來,搜索簡歷、鎖定簡歷、與候選人溝通、組織機考,這些流程瑣碎而漫長,候選人還經常無法通過機考。
張千透露,為了提高招聘效率,有的用人部門會主動輔導候選人,以便順利通過機考。這種輔導通常是無償的,僅是為了填補用人需求,但顯然也違反了公司規定。王麗還聽說,有招聘需求的用人部門負責人會請外企德科的HR吃飯,只為了請求對方多給他們推薦簡歷。
無償、微妙的操作之下,也有人看到了利益尋租的空間,一條灰色產業鏈正在滋長。
有的是個人利用職權尋租,比如內部員工和外企德科HR勾連,將已被用人部門鎖定的簡歷釋放出來,交由外企德科重新鎖定、推進招聘流程,候選人入職后雙方按照一定比例瓜分1500-5000元的服務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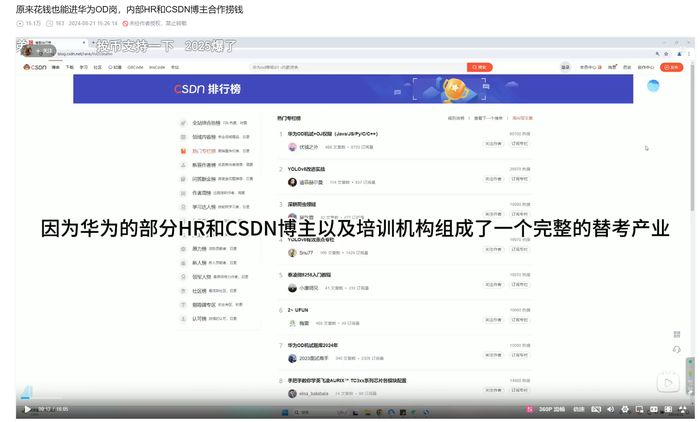
還有成體系的牟利方式。去年8月,B站用戶“程序員正義”發布一則視頻,舉報華為OD招聘人員和CSDN博主共謀運作招聘流程。
視頻內容顯示,HR聯系到OD候選人后,會推薦其向某CSDN博主購買機考題庫,該博主會引導候選人加入特定QQ群,群內有專門人員介紹、推薦“包過”入職方案,內容包括偽造薪資流水、機考替考、面試運作等,費用為6900元。
視頻里,該用戶播放了一段通話記錄,在該用戶對招聘流程合規性和可行性提出疑問時,對方胸有成竹地回答說:“所有流程我們都參與了。”
華為曾察覺到這類交易。王麗說,去年9月開始,華為規定,曾被用人部門鎖定簡歷的候選人再通過人力資源公司參與招聘,入職后人力資源公司無法獲得提成。同時,偽造銀行流水也不再那么容易過關——前述視頻里,對方建議候選人通過P圖的方式偽造薪資數據——現在華為搭建了新的系統,要求候選人上傳相關證件證明。
而在這次的內部清肅中,華為更是以雷霆手段處理了一大批人,流傳出的華為公告顯示,“經審計發現,ICT產品與解決方案、半導體業務部、人力資源管理部、ICT銷售與服務部、終端BG、質量與流程IT部多人在非雇員人員選擇業務中,存在安排/參與替考、向候選人透露服務能力考查題目等違規行為,同時,多人通過出賣公司信息資產獲利”,涉案高達60余人,被華為一舉開除或處罰。
降本增效滋生出的招聘腐敗
華為的境遇也是科技巨頭們的境遇。反舞弊腐敗已成為大公司每年甚至每個季度對內外公告的重要議題。
公開信息顯示,2024年,騰訊反舞弊調查部共發現并查處觸犯“騰訊高壓線”案件百余起,百余人被解聘,其中二十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同年,網易游戲營銷線多名高管因涉嫌貪腐被調查,震動游戲行業。
具體到招聘環節,2021年,騰訊集團反舞弊調查部曾協助公安機關對付費實習騙局進行偵查,并將公司內部參與付費實習騙局、且存在違法行為的員工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在騰訊集團披露的案例中,有5例是騰訊員工與外部求職中介合作,由外部中介負責招募實習生,然后由騰訊員工安排實習生進行虛假的遠程實習,并從外部求職中介處分得實習應聘者支付的部分費用。
今年春招伊始,騰訊發布公告提醒應聘者,騰訊員工利用內推進行收費的行為違反了《騰訊陽光行為準則》,如果應聘者在求職過程中遇到利用伯樂碼收取費用的情況,可以向騰訊反舞弊調查部反饋。
而當OD或外包成為大公司必不可少的人力補充,因為涉及第三方公司,中間模糊地帶更廣,也就更容易滋生舞弊腐敗。去年11月,字節跳動發布年內第四份反舞弊腐敗通報,103人因違法違規行為被辭退,其中就包含外包及實習生。
OD和外包人數眾多、難管理,用人部門權責泛化,這些都是招聘環節出現舞弊腐敗的原因。但大公司們為了降本增效,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尋租是難免的。
以華為為例,薪資待遇上,正式員工和OD員工的最大差異是,OD員工沒有股權,不參與分紅,而股權分紅是正式員工的收入來源之一。潮新聞測算,按照華為于今年1月公布的2024年度員工持股計劃的分紅方案,每股分紅1.41元,以2023年的總股本數513億股為基準進行推測,此次華為的分紅總金額應該不低于723億元;按照去年的參與人數151796人來計算,人均分紅應該不低于48萬元。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降本是降下來了,但外包員工能不能帶來增效,尤其在目前AI、機器人等領域創新不斷發生的時候,諸多大廠正面臨著組織效率低下、創新動力不足的問題,如果再缺乏新鮮血液的注入,長遠來看也是一個問題。
咿呀作響的體系之下,小西有些扛不住作為OD的壓力,得到的回報也讓他沒有動力自我調節。他正在找新工作。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向洋、張千、小西、清寒、王麗皆為化名。)
參考資料
潮新聞:《起底“內推實習”!花數萬元可進大廠?套路太深了》
科創板日報:《華為,為什么要反腐》
電廠:《獨家對話華為被開除員工:不存在OD招聘牟利,違規原因是團隊長期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