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100年前,日本女性用脫脂棉與和紙自制衛生巾,小心翼翼地應對月經的困擾。直到1960年,現代衛生巾才在日本問世,它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女性的生活,也推動了她們大規模進入職場。
月經不僅是生理現象,更是文化、社會與權力的交織點。青春期時,初潮是進入“女性世界”的儀式;成年后,月經是生育能力的象征;一旦進入更年期,失去月經的女性便被貼上“衰老”的標簽。在另一邊,女性也正在重新定義這些節點。日本詩人伊藤比呂美在《閉經記》中寫道,閉經帶來了“全新的自由”;學者希珀則指出了女性如何倒轉并利用月經禁忌的神話。
從月經貧困到更年期的沉默,從污名禁忌到身體自主,下面這份書單記錄了女性如何用身體的經驗書寫神話,又如何在文本的縫隙中尋找聲音。
月經與神話

[荷]米尼克·希珀 著 王晚名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3
在許多文化中,月經被賦予了禁忌的色彩。女性在經期被認為是不潔的、危險的,甚至是有害的。比如直到20世紀60年代,日本部分地區仍保留著“月經小屋”的習俗。女性被要求進入這些簡陋的小屋,獨自度過經期,甚至不能與家人共餐。當她們在小屋中進食時,放學的孩子們會從旁經過,無論是路過者還是屋內的人,都會因為意識到小屋的用途而感到羞恥。

然而,我們也能找到慶祝月經的地方。北美印第安人的阿帕奇部落會慶祝初潮,當地精心設計日出儀式,女孩們穿著特殊的服裝度過四天四夜,通過跳舞、跑步來展示力量。
《樂園之丘》還指出,圍繞月經周期建立的禁忌,并不一定只作為禁錮存在。在某些情況下,女性巧妙地利用了這些規則,將其轉化為一種權力。巴布亞新幾內亞北部沃吉歐人(Wogeo)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男性發展出了一套關于女性“不潔”的理論,認為女性在經期是危險的,但這一理論也讓女性擁有了某種隱形的反擊力量:如果一個男人打了他的妻子,妻子可以在下一次經期時觸碰他的食物,讓他染上致命的疾病。
為了避免這種風險,沃吉歐男性發展出了一種儀式:主動讓自己的陰莖出血,并認為這樣可以讓身體充滿能量和自信。獵人們在織網捕獵野豬前進行這一儀式,勇士們在發動突襲前會這樣做,商人們在鑿制獨木舟出海前也會這樣。月經雖常常被用作貶低女性、將她們排除在公共空間之外的手段,但是,月經也讓男性恐懼,讓女性創造了自己的“月經”儀式。
衛生巾與“月經貧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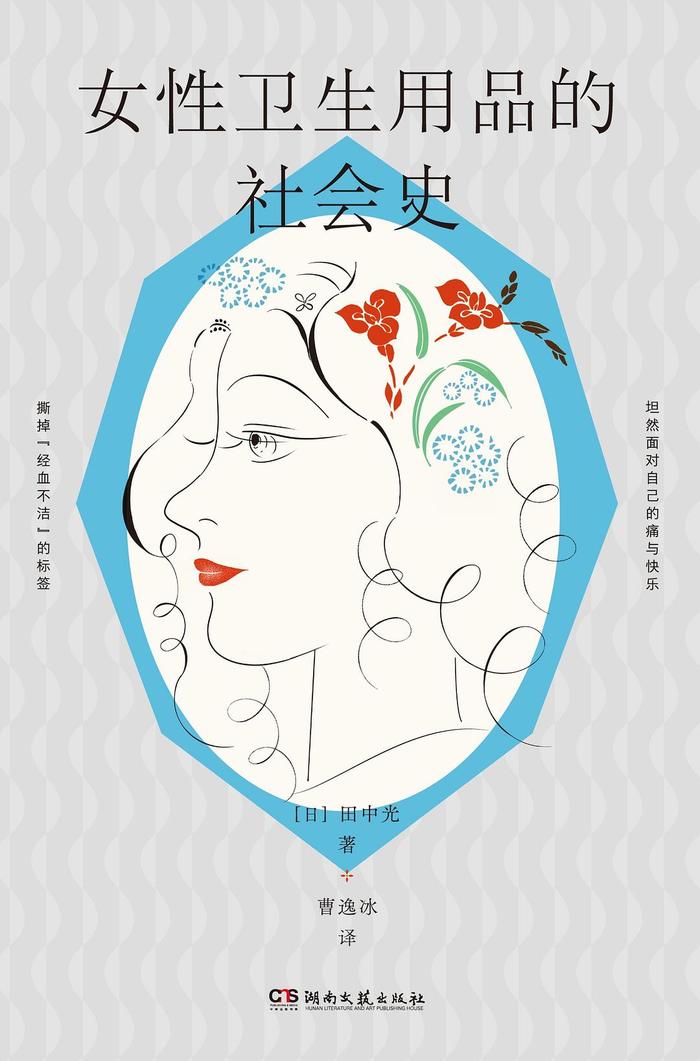
[日] 田中光 著 曹逸冰 譯
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5-1
“她們買來脫脂棉裁剪成方形,再把和紙裁小了、揉軟了塞到棉片中間,做成一根根小棍子,來了月經就塞到下面去,說是出門在外也不容易漏。”這是100年前的日本女性自制衛生巾的過程。
日本學者田中光在《女性衛生用品的社會史》一書中討論了衛生巾的歷史。她發現,直到1960年,現代衛生巾才在日本問世,距離現在不過60年的時間。而如果一次性衛生巾沒有登上歷史舞臺,日本女性在經濟高速發展期邁入工作場所就難以實現,因為月經期間不方便活動的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1920年,美國“高潔絲”研發出了廣泛銷售的一次性衛生巾。這款產品剛上市時完全賣不出去,因為女性不好意思去商店購買。負責廣告業務的阿爾伯特·拉斯克想出了一個辦法:他通過報刊廣告宣傳高潔絲可以自助購物(進店后直接拿起高潔絲,再往旁邊的盒子丟50美分即可),全程無須開口。
“八點健聞”曾撰文梳理中國衛生巾的發展歷史,從只能使用草紙,到1991年寶潔在廣州工廠率先推出了護翼型衛生巾。然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仍有許多女孩正在經歷“月經貧困”。與“散裝衛生巾”相關的微博曾數度沖上熱搜。這些散裝衛生巾沒有外包裝、保質期等相應標識,價格低廉,消費者可以一次性購買上百片,平均每片單價在2毛錢左右(市面上常見衛生巾品牌的單片價格約為1-2元)。后續的一系列討論加深了公眾對女性“月經貧困”的認識。
女性主義團體“若爾熱特·桑”曾在2015年的巴黎舉行示威游行,原因是國民議會否決了一項預算修正案,該修正案提議將經期用品的增值稅從20%降至5.5%。目前,中國的衛生巾增值稅為13%。
閉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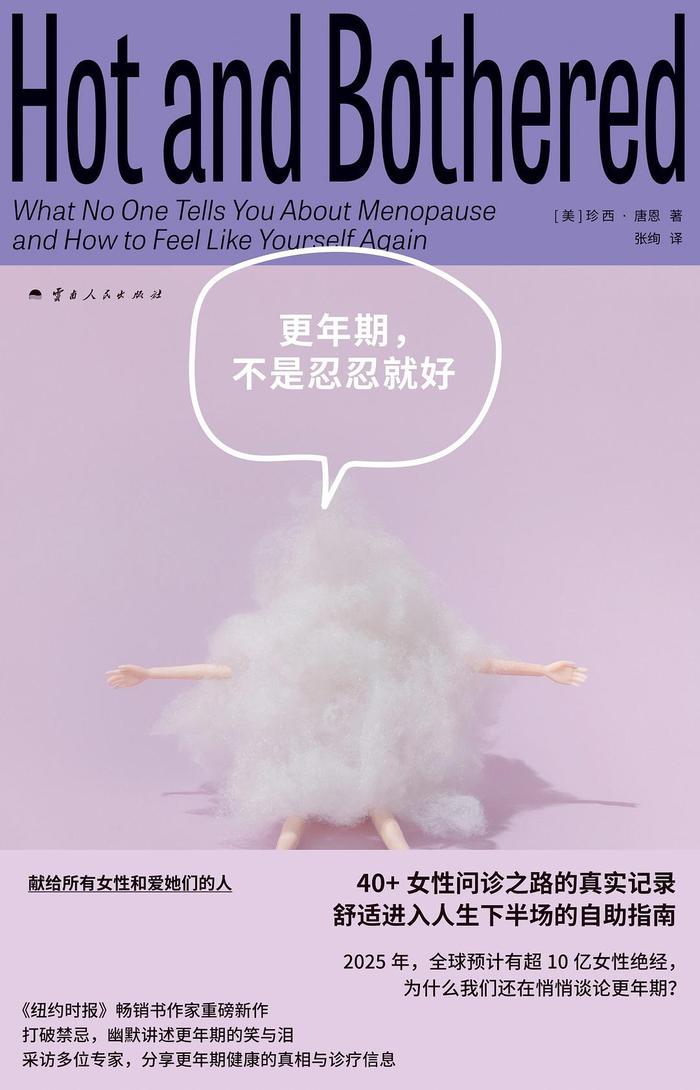
[美] 珍西·唐恩 著 張絢 譯
理想國·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5-2
四十多歲時,一直關注女性身心健康的專欄作家珍西開始被一些癥狀困擾:出汗、嚴重失眠、口干舌燥、神經緊張……在多次問診后,她發現一切的源頭竟然是更年期。即使長年耕耘于健康報道領域,珍西在更年期悄然到來時也還是感到措手不及。
她于是寫作了《更年期,不是忍忍就好》。長期以來,更年期的話語源于男性和醫學界對更年期的厭惡,認為更年期是生命力、美麗、憧憬和價值的終結。如果卵子過了保質期,只能被清倉處理。絕經意味著女性生命衰敗的轉折點,沒有月經后“女人從此不再是女人”。
珍西將《倫敦生活》里的臺詞與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所說的絕經后“熱情”聯系在一起:“是的,你整個骨盆都毫無用處了,你變得富有魅力,但也沒人會撩你,然后,你就自由了。不再是奴隸,不再是生育機器,你只是個單純的處于事業中的人。”一種完全進入自我的興奮感,一種從購買衛生棉條以及對懷孕的無盡恐懼中解放出來并隨之獲得的甜蜜感受,一種擺脫“取悅癥”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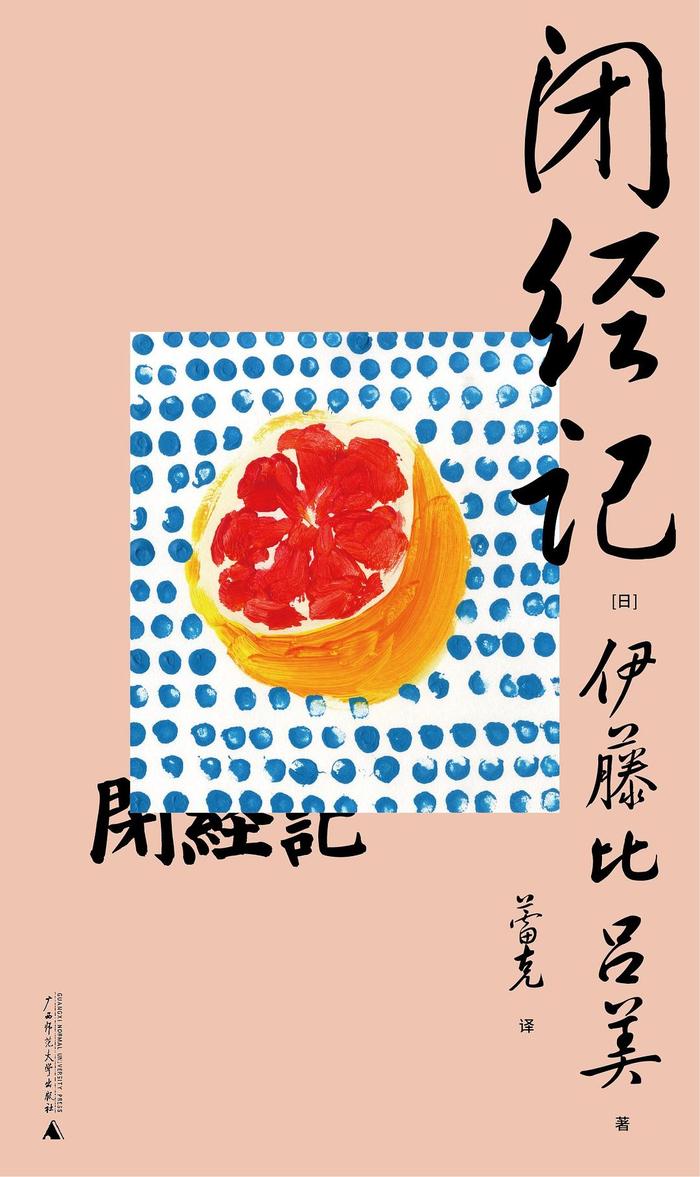
[日] 伊藤比呂美 著 蕾克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7
和珍西一樣,2012年,57歲的日本詩人伊藤比呂美發現自己進入了更年期。她的寫作展現出了月經另一種自由的面貌。她在報紙上開設專欄,以《閉經記》為題連載兩年,記錄下了這一時期的生活與身體。
她賦俳句悼念逝去的月經:“經血啊,淅淅瀝瀝無精打采,透著寂寞。”她也在衰老中看到新生,“美還是不美,都去他的。變老意味著自由,全新的自由。”
同《倫敦生活》視經期為父權枷鎖的決然態度略有不同,伊藤比呂美對逐漸逝去的月經感到了真實的不舍。她嘆道:“閉經之前的月經,清冷寂寥,靜悄悄的。”她也做出了挽留月經的努力,開始接受激素替代療法(HRT)。月經在比呂美的視角中擺脫了生殖與性別凝視,回歸為真實的鮮血,迸發出快活又純粹的能量。
她定期服用卵泡荷爾蒙和黃體酮,斷斷續續的經期又再次到來:“幾天后,仿佛聽到了遠方傳來的戰鼓,聞到了黃昏前隱約的雨氣,要來了要來了,躁動之后,啊,那種熟悉的感覺!血滴了下來。”月經來的那一刻,她感受到了運動會的振奮——一個大多數人經期不會想到的地點——“月經的勢頭啊,就和三十幾歲時一樣,嘩嘩猛。赤紅的血好似夜空中綻放的輝煌煙花,運動會上隨風飄揚的旗幟,完全是種喜慶。”
是綻放的煙花,是飄揚的旗幟。伊藤比呂美說,看到重來的月經,如同興高采烈地與老朋友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