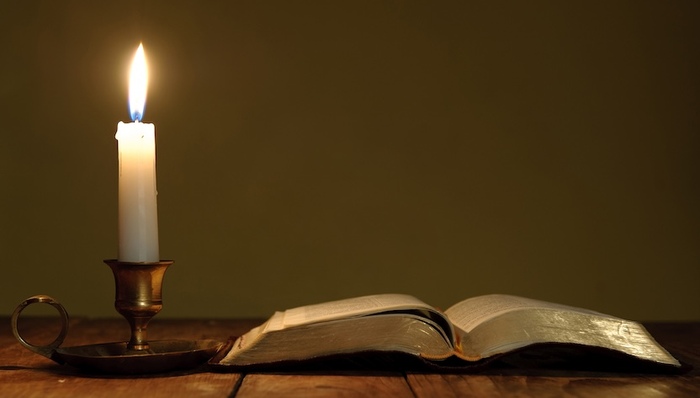界面新聞記者 | 陳升龍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13日,歐洲管理學大師查爾斯·漢迪(Charles Handy)在倫敦家中去世,享年92歲。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漢迪就陸續前瞻性地提出了零工經濟、遠程辦公、外包、三葉草組織結構等人性化的商業概念和理論。他對管理學的貢獻不僅激勵了商業精英,也啟發了普通勞動者,成為研究組織文化的基礎工具。
漢迪于1932年出生在愛爾蘭基爾代爾郡的宗教家庭。在牛津大學奧里爾學院大學就讀期間,他就大量研讀人類歷史和哲學大師的經典、進行系統性的批判思考,為日后的高質量輸出打下基礎。例如針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人生幸福觀”,漢迪將其理解為“在自己最擅長的領域里做到最好”。
從牛津畢業后,漢迪于1956-1965年分別在東南亞和倫敦的殼牌公司國際部工作,一路升至營銷最高管理崗位。在這期間,殼牌公司開始進行多元化發展,尤其是進軍煤炭、核能和金屬領域。之后他還在成立不久的地方電信公司Charter Consolidated Limited服務了一年。這10年的職場經歷成為他后來寫作的重要素材來源。
1967年,漢迪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學習組織研究。在短短一年求學里沃倫·本尼斯(Warren Bennis)等師長的諄諄善誘使他逐漸對企業管理及其運作原理產生濃厚興趣,積累了理論基礎。漢迪同時還抽空回到英國創辦了英國首家管理研究生院——倫敦商學院。之后他決定從事教育工作,并在閑時開始演講和寫作。

為了有充足的時間來寫作,漢迪在1981年決定成為自由職業者。從《通曉組織》開始,漢迪至今出版了至少20部影響深遠的管理學著作,圍繞商業社會中權力、角色、任務和個體多個緯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不僅提出了管理哲學和永續生存的企業觀,還論述了在不斷變革的社會中更為廣泛的個體生存問題。
進入21世紀,漢迪在全球首個管理思想家排行榜(The Thinkers 50)評選中排第二,僅次于美國人彼得·德魯克。倫敦商學院前院長里克曼(Andrew Likierman)稱,漢迪打破了美國人在該領域的壟斷。

他在麻省理工的導師本尼斯曾這樣評價這位弟子:“如果說德魯克確立了管理學的地位,那么漢迪則賦予了該領域的哲學氣質和思辨的表達。”事實上,漢迪在多個場合強調自己是“社會哲學家”,而模糊管理學大師的標簽。
在1989年出版的《非理性的年代》中,他指出未來社會是非理性的,只有那些打破傳統思維模式的人才會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人們應該擁抱變化而非抵制,任何組織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必須創造積極、強大的企業文化,同時幫助員工在競爭中全身心地堅持學習、脫穎而出。
其作品敘事的方法往往是“蘇格拉底式對話體”,并頻頻使用生動的隱喻和創新概念。漢迪在早期多本著作中反復預言“三葉草”組織結構形式的出現:重要管理人員、承包商和兼職人員形成穩固的三主體。而在這種模式下,企業必須始終留住至少10%的核心成員,才能確保組織的持續發展。
他還在2001年出版的《大象和跳蚤》中形象地探討大公司和獨立勞動者的共生關系。在多年后的采訪中,他透露寫這本的初衷是想說明這一殘酷的現實:很多人幾乎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大機構,他們必須走出這個牢籠,掌握具有競爭力的生存技能,即成為頑強的“跳蚤”,而這當中職業培訓機構的作用也很重要。
漢迪還主張,公司為了精簡結構,其核心管理規模應該減半,個體薪金翻倍,產量提高3倍,這才是一個公司的獲得生產力“P” (productivity)或利潤“P”(profit)的關鍵。他將此歸納為一條公式:1/2×2×3=P。
漢迪常年保持寫作的熱情,即使是在晚年中風住院期間,也能說服護士允許他繼續在病床上工作,探索組織中的人類價值觀。
而隨著人工智能的崛起,漢迪就自動化高速發展的風險敲響了警鐘。他在2017年的一次演講中說道:“如果一個組織完全數字化,那將是一個非常沉悶的,是人類靈魂的監獄。”
漢迪之所以取得巨大的學術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家人的支持。在攝影領域頗有造詣的妻子伊麗莎白也是他的事業合伙人。漢迪決心全身心投入創作之后經常做義務演講,家庭收入大降,于是伊麗莎白重新撿起了攝影師職業,以彌補家庭開銷不足,她同時還承擔丈夫的經紀事務和形象設計。
伊麗莎白在2018年3月5日的一場車禍中不幸去世。而漢迪去世那天,8名子孫圍繞在床邊,陪著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