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二十年前,韓江的第一篇小說在中文世界亮相,譯者是韓國文學研究者薛舟,那部短篇小說題為《蒙古斑》,譯文發表在《外國文藝》上。二十年后,當54歲的韓江成為第一位捧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亞洲女性,薛舟在接受界面文化專訪中回憶道, “我記得當時關注她,是因為她剛獲得韓國最重要的文學獎——李箱文學獎。”
得知韓江獲獎消息,作為她的譯者,薛舟“非常驚喜”。“這確實令人意外,她應該是第一位獲諾獎的70后作家,也是第一位獲諾獎的韓國文學作家,我估計今晚韓國人會狂歡。”薛舟指出,此前東亞三國中只有韓國尚未獲得諾貝爾獎,他曾思考是否會將獎項頒給像黃晳暎、李文烈等老作家,沒想到給了這樣一位年輕的作家。
他回味初讀韓江的感受說,“韓江是70后,20年前還很年輕,但她那種語言的冷靜、對人性的發掘、對人際關系的剖析之細膩,都讓我很震驚。”
他認為,韓江三十歲出頭便榮獲韓國最重要的文學獎項,說明她的作品非常過硬。此外薛舟也特別提到,韓江出身于文學世家,父親韓勝源也是韓國知名作家,二人都曾獲得李箱文學獎。
薛舟強調說,韓江的文字十分敏銳,尤其擅長挖掘人類心理與人際關系中的復雜性。她在創作初期主要關注個人內心世界,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將目光轉向民族歷史與集體苦難的書寫。薛舟認為,韓江的早期作品《植物妻子》和《素食者》“文學性強烈且深刻挖掘人性”,很好地代表了她的創作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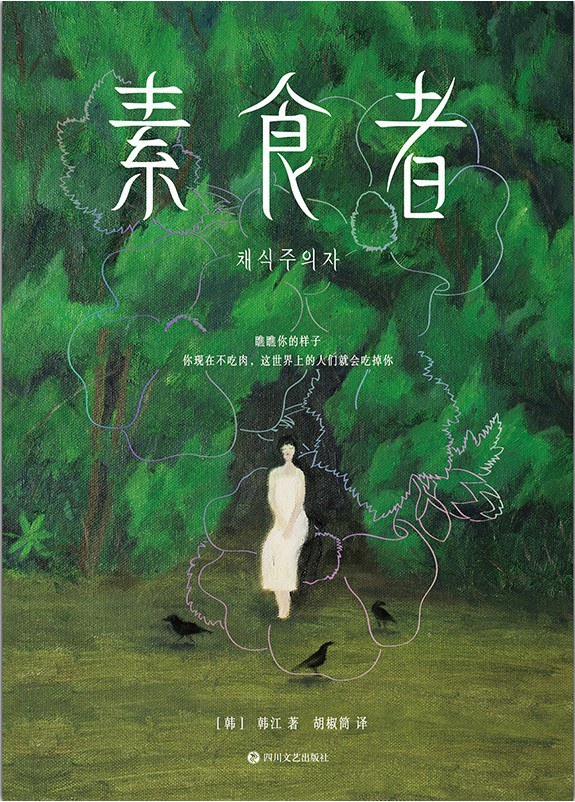
因善于描繪人類處境中的孤獨與悖論,韓江有“韓國文壇的卡夫卡”之稱。薛舟提到,這種孤獨感可能使得她在韓國的受眾不如其他作家廣泛,但她本人的個性也相對安靜,主要以作品說話。
在后期,韓江的寫作領域擴展到了更廣泛的題材。《少年來了》聚焦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不做告別》則圍繞駐韓美軍在濟州島的屠殺事件展開。在韓國文學中,這些是鮮有作家處理的題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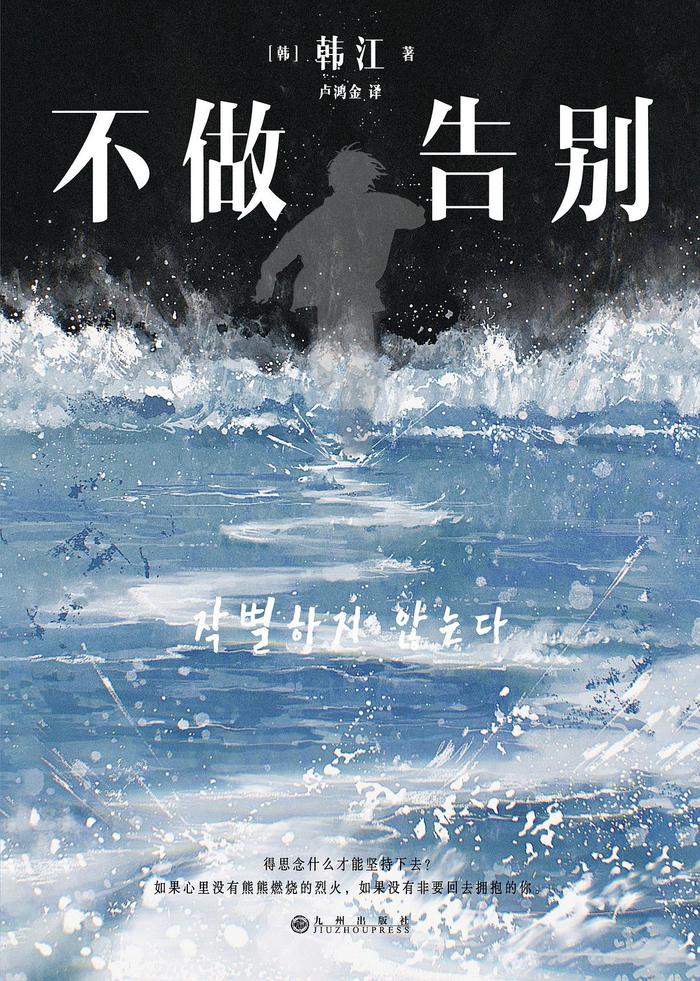
薛舟提到,在韓國文學領域,“70后”作家眾多,這一代作家與前輩呈現出了不同的風貌。“借用詩人王家新的話,這一代作家從集體的歌唱轉向了個人面對時代的感受。”他們逐漸脫離了集體敘述的方式,轉向個人剖析的寫作風格。
薛舟注意到,這幾年韓國文學在中國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他認為,中國讀者與韓國作家之間會產生許多相似的共鳴,無論是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還是生活、社會、家庭等方面,兩個地方都有一些相似性。他舉例自己曾翻譯過的韓國80后作家金愛爛,強調她側重于大城市中小人物的生活,從讀者評論中常常看到“東亞人的特有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