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周文晴 記者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法國當地時間9月8日,第17屆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巴黎閉幕。似乎要接續其在奧運會上的大膽前衛,這座城市也將極大的開放性投注給了它所承辦的第一場殘奧會。開幕式同樣在體育場外舉辦,巡游和文藝演出的地標覆蓋香榭麗舍大街、協和廣場及方尖碑。
然而,更可貴的創新或許在于,這一屆殘奧會不再一味歌頌表面上的殘健融合,而是直面非殘障者與殘障者之間——乃至殘障者與其自身之間——長期存有的誤解、貶低、偏見。正如其開閉幕式導演托馬斯·喬利(Thomas Jolly)所言:“我們的主題是提出一個有關和諧的問題:我們真的達成一致了嗎?——特別是在殘障問題上。”

殘奧賽場之外的寂靜,或許正印證了喬利的追問:中國本屆殘奧會名列金牌榜第一,但社交媒體上熱度最高的討論是“殘奧熱度怎么這么低”。零星的評論者試圖就展演方式、賽事設計、商業模式等要素探討殘奧會如此靜寂的緣由,但在靜寂的水面之下,分類機制顧自讓人類的身體呈現為完滿/殘缺、正常/失能的兩級,國族主義和消費文化前后夾擊,使特定體格淪為次等地位又充分得以開發,對身體的規訓與控制正使運動和競技偏離本初的意義。上述力量暗潮洶涌,共同形塑著我們眼中可見的奧運與殘奧的面貌,但中文互聯網鮮少針對這一問題進行梳理澄清。
殘奧會的不受矚目還有望作何解釋?撥開表層的靜默或喧囂,當代盛行的各類身體話語如何以殘障為焦點輾轉騰挪?遙望將來,對于更切近人類本真性的運動態身體,我們還可能給出怎樣的希冀?
01 兩個“奧運”,根植于完滿和殘缺的身體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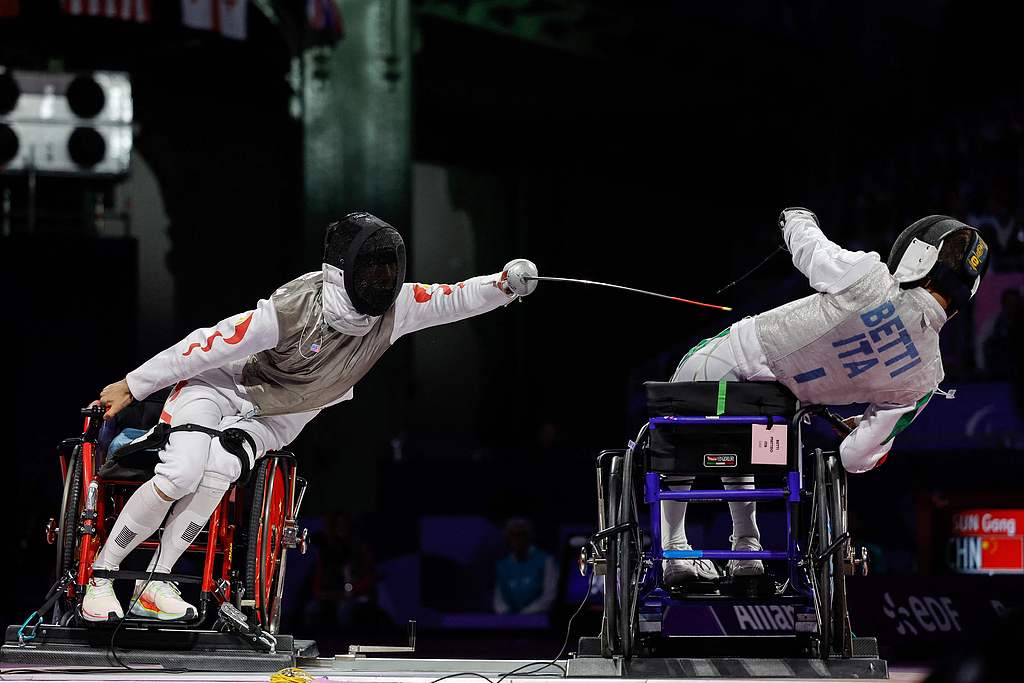
一個困擾許多人的問題是:為什么殘奧會不像奧運會那樣激動人心,沒有一位殘奧運動員如劉翔、谷愛凌、鄭欽文那般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
有媒體評論指出,部分原因在于殘奧會過于復雜繁多的項目明細,使它變得“不好看”。例如,此次巴黎奧運會設有32個大項、329個小項,而殘奧會的22個大項細分至549個小項。單以公路自行車比賽為例,殘奧會首先根據運動員的“殘疾類型”分成4種不同的自行車,包括標準自行車(上、下肢活動受限)、手動自行車(脊髓損傷或一肢或雙肢截肢)、三輪車(腦癱或偏癱)、雙人自行車(盲人或視力障礙),每一類又根據運動員“殘疾程度”標定2—5個等級。如此浩繁的金牌項不僅讓觀眾面對著更高的觀賽門檻,也稀釋了每一枚金牌的稀缺性。但“分級”作為一項醫療上的規范標準,被認為旨在考量殘疾對運動員體育表現的影響,進而確保公平競爭——“為公平而做出的觀感上的犧牲”似乎成了“殘奧會不好看”問題的最終解。

奧運會也同樣有責任維護競技公平,卻反倒“容忍”了太多的差異匹配。就在本屆奧運會期間,“多名中國神射手竟是近視眼”的新聞一度沖上熱點,曾獲2004年雅典奧運會男子10米氣手槍冠軍的王義夫視力僅有0.1。其他項目中也不乏運動員存在或多或少的障礙。在奧運會場景下,除性別之外那些零零總總的身體特征(如種族、身高、健康狀況等)普遍不被認為影響參賽,人們更多關注的是運動員的運動技巧和形象魅力。由此反觀殘奧會,我們似乎很難對運動員除殘障之外的特點(如外表、個性等)如數家珍,在其精確化、體系化的分級系統之后,呈現出的是一個“殘且僅殘”的高度同質化的群體。
事實上,殘奧會的緣起本就并非出于競技目的。“二戰”結束后,歐洲出現了大量傷殘退伍軍人。1948年,在英格蘭的一家脊柱損傷療養中心斯托克·曼德維爾醫院,醫生路德維希·古特曼(Ludwig Guttmann)參照同期舉辦的倫敦奧運會,為全院脊髓損傷者開展了首屆“斯托克·曼德維爾運動會”,旨在通過體育運動提升患者身體素質。這場醫院范圍內的運動會被認為是日后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雛形,殘奧會的英文名稱Paralympic便是由Paraplegia(因脊髓損傷等導致下半身不遂者)加Olympic(奧林匹克)組成。中文世界僅有中國臺灣地區將Paralympic以音譯譯作“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其他地區皆稱“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臺灣地區原稱其為“殘障奧運”,后在身心障礙者與社會各界的呼吁下,于2004年改稱作“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殘奧會的設立初衷其實僅僅鎖定了身體的殘缺,是讓長久位于體育空間之外的殘障人士(也能)參與到運動中,至多達到康復治療的效果。此后,國際殘奧委會(IPC)和國際奧委會(OPC)達成合作,協定殘奧會和奧運會需于同一個城市相繼舉辦,其與奧運會的高度綁定關系,加之為比賽公平而日趨精巧的分級體系,使人們誤以為殘奧會原本便為競技而生。實際上,身體損傷及由此衍生的能力判定——可否運動、有無參與特定比賽的能力、項目分級還是合級——始終是殘奧會考量的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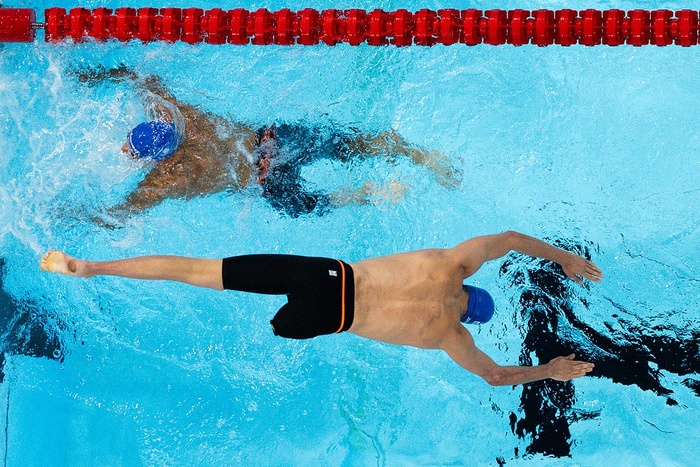
由此看來,殘奧會相比奧運會的關注度懸殊,不僅源自對比賽項目的分級,也根植于對身體的分類。屬于奧運的身體默認完滿無缺,有能力角逐“更快、更高、更強”的人類極限,并呈現技巧和個性上的多樣性,在一定限度內偏離“正常”身體規范可以說瑕不掩瑜。另一類是殘奧會上的默認殘缺的身體,其參賽資格、競技能力必須與其生理構造一一對應。“殘缺”身體的特征匹配如同一場大型“連連看”,依據的標準僅僅是生理損傷,高度、寬度均遠輸“健全”身體,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奧運”不可能同樣精彩。
02 殘障之軀,不屬于“我們”又服務于“我們”
自1988年夏季殘奧會與奧運會舉辦時程同步的近40年來,奧運會的意義已經遠超競技體育范疇,成為承載國族身份(nationhood)、時代精神、世代文化的載體。拋開競技屬性不論,其日漸復雜的文化意涵也幾乎從未能“輻射”給同期殘奧會。
包括奧運會在內,競技體育的敘事常常為國族話語占領。特別是近現代中國遭蒙積貧積弱的國力窘境和“東亞病夫”的污名,身體話語與民族國家的話語異常密切地交織在一起。歷史學家黃金麟在《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中提出,對軍國民思潮在西方和日本等國所造成的優勢情勢的向往,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描繪的景象的緊張,使中國力爭以身體的改造達成維護國權的目標,以雄美健壯取代柔美孱弱。近些年中國在奧運會上的佳績折射了人們的熱望也滿足了這一渴求,每每國歌奏響,強烈的“我們”感油然而生。涌現出的明星運動員不止是流量焦點,更已凝結成形塑共同體意識的標志性符號,在某種程度上是國家的象征。

黃金麟 著
新星出版社 2006
殘缺的身體仿佛與此截然對立。由于生理性損傷與功能性失能之間長期存有的牢固關聯,殘障者無可避免地被卷入當下盛行的能力主義話語。能力主義認為,一個有能力的身體才是公民的身體,相比之下,女性、衰老、肥胖、畸形、耳聾、截肢和失明的身體不能構成身體政治。而在幽微的個體心理層面,根據精神分析的觀點,我們被分裂成好的和壞的自我,殘障恰恰成為壞的、失能的、碎片化自我的投射對象,進而遭致排斥。
這種心理機制可以具體化為殘障研究者哈蘭·哈恩(Harlan Hahn)提出的“兩種焦慮”,即殘障的出現喚起了人類的“存在焦慮”(預期能力喪失的威脅)和“審美焦慮”(對不符合慣常身體吸引力特征的恐懼)。這樣令人陷入焦慮的身體,如何具備合法性來凝聚起哪怕是想象的共同體?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放眼殘奧會的輿論場,鮮有如奧運會那樣充斥著民族主義、旨在捍衛國家榮譽的交戰或互噴,殘奧運動員的成績不論國籍,都得到等質的喝彩/忽視。盡管冠軍如云,ta卻——至少在大眾心理層面——代表不了國家,其自身也不復享有“為國爭光”所帶來的符號或商業紅利。

由于長期在媒體和文藝作品中代表性不足,殘障運動員既不足以構成共同的文化符碼,也不在時代風潮的敘事和商業力量的青睞之中。殘奧相關報道中最常用來指稱殘障者的代詞是“他們”,這個詞彰顯的他者化意味正代表著,不會有人認同這樣一些身體是“我們”的一部分,他們不屬于“我們”。
處于國族敘事、時代精神、商業力量之外的殘缺身體,很多時候作為奇觀存在,喚起觀眾的娛樂或憐憫。且看被譽為“名場面”的數次殘奧會開幕式點火炬儀式:在2016年里約殘奧會,倒數第二棒火炬手、巴西殘奧首金得主馬爾薩拄著拐杖不慎摔倒,但“這位70歲的奧運冠軍頑強地爬起來把火炬傳到下一棒,這一幕感動了無數觀眾”;2022年北京冬殘奧會,火炬交由雙目失明的殘奧冠軍、退役運動員李端點燃,他于萬眾矚目之下伸手摸索了許久,遲遲未能找到正確位置插入,在全場一分多鐘的“加油”聲中,終于成功點燃了火炬,網友爭相評論“淚目”“動容”。

整個人類歷史都有一種“迷戀差異景觀”情節。在古希臘和古羅馬,豪門大戶如果沒有幾個侏儒、啞巴、白癡、太監和駝背供人羞辱玩樂,幾乎是不完整的。時至今日,有研究指出當今大眾媒體中的殘障者身份仍然無外乎具有以下特點:可憐可悲的,陰險邪惡的,煽情的,“超級小強”,嘲笑的對象,一個累贅,與性無關的,不能充分參與日常生活的。
就在此次巴黎殘奧會前夕,英國廣播公司第四頻道的一項調查發現,殘奧會觀眾中近60%旨在“看運動員克服殘疾”,而只有37%是因為“激動人心的體育賽事”。有媒體呼吁觀眾不應鎖定生理性的個人問題,而應著眼于致殘性的社會問題。這一社會模式視角誠然為當代所急需,但更迫切的或許是分析殘障身體處于貶低和著迷的雙重目光的深層動因——殘缺的身體代表不了國家,卻可充分注解國家的人道事業;萬不能算作“我們”,卻撩撥著“我們”最隱秘的渴求。
事實上,殘缺身體的特殊意義非但“可有”,而且“必有”。曾經有參與殘奧開幕式表演的視障演員披露,他們被要求戴上墨鏡,以便觀眾區分出盲人和明眼人群體。這似乎暗示殘障不能僅僅是存在,還必須有所表征。對此,一本力圖貫通殘障理論和文化理論的小冊子Culture - Theory - Disability用懷孕做類比:如果讓影視中的某個角色懷孕,你必須為懷孕提供完整的理由和背景,然而在大街上看到懷孕的人是很正常的!殘障也是一樣。

借用弗洛伊德的話,盡管有時“截肢的腿只是截肢的腿”,但媒介中這一設想永遠不可能成立——殘障必須蘊含其他東西——悲慘、邪惡、柔弱、勵志、純真……否則,如果上述的巴西身障運動員馬爾薩沒有摔倒而后奮起,視障運動員李端無需費力摸索便可分分秒點燃火炬(現有AI場景識別技術很容易幫助實現),那得多么無趣!觀眾也會迷惑為什么要插入一個殘障人讓原本的“正常性”受到干擾。所以,殘缺的身體連同殘奧會是被“判定”在了一個意義之場——一個由非殘障人驅動的需要、幻想、投射之場。或者毋寧說,他們必須被表征,才能存在。
與之相反,奧運會不需要解釋,它不必被清晰界定為“非殘奧運會”,也不必解釋為“健全/常態亦或其他冠以修飾性成分的奧運會”,它不僅“更快、更高、更強”而且“更團結”,而作為“他們”的殘奧運動員和更多殘障人士,不僅距離平等地共享“更團結”這一愿景千里之遙,就連平等地存在、平等地被看見仍困難重重。
03 在內核上整合奧運與殘奧,或可松動身體理性化的鐵籠
殘障者在運動場景下一邊被開發一邊遭受排拒,健全者也不可能“坐享其成”而毫發無損。為捍衛國族主義,運動員的生產力被持續大力發掘;商業力量同樣力促極限成就,從而把商品與相關功用和快樂意象相維系。致力于兌現這種超強績效承諾,我們的身體已經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根據國際奧委會的數據,2016年里約奧運會期間,小輪車、拳擊、山地自行車的受傷率分別是38%、30%、25%;超過一半的美國橄欖球運動員在近期幾屆夏季奧運會上受傷……且不論這些損傷,訓練規制本身就掌管了有意取得體育成就的人們的生命:飲食起居的點滴細節都規定詳實,以求集中于最強績效的目標。
究其根源,運動與身體已經深深嵌入現代大規模理性化進程,與往昔形成鮮明對比。在中世紀歐洲,球賽遍布鄉間田野,全村人都參與其中,競跑、舞蹈和狂歡也隨處可見。彼時的運動會更像追逐天性多樣性的游戲,參與而非績效展演維系著游戲的共同體。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曾用“游戲的人”(homo ludens)來界定人,把體育活動解讀為人類本質的展現。但在今天,大到國際賽事、小到日常健身的運動,日漸受制于功效或成就的要求,曾經表達文化創造性的體育活動更加趨近于一項工作。理性化的最后一站,是使身體臣屬于計量標準的意志——不僅是殘缺的身體遭到界定、排除并傾盡其可用性,如不加審視,所有人都將被置于單向度、標準化的系統中監控、趨同、磨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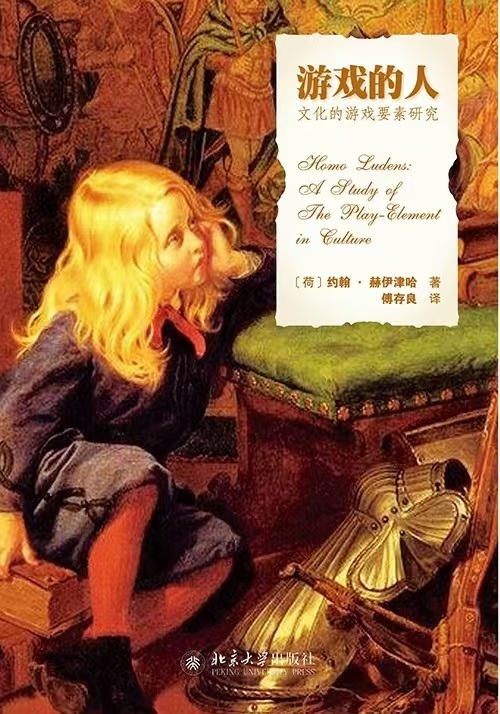
約翰·赫伊津哈 著 傅存良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讓殘奧會和奧運會合并的建議近年常常見諸網絡。單就殘障與健全的區隔而言,合二為一是否可以看作一條緩解過度理性化的出路?英聯邦運動會(The Commonwealth Games)已自2002年起增設了殘障人項目,但反對者擔憂,合并將會使殘奧會所擔負的殘障權利和無障礙環境倡導使命淹沒在奧運會的主流報道之中。
我們的想象力或許可以再一次革新:不去拘泥于兩場賽事在時空上的合并,而是設想看似涇渭分明的殘奧會—奧運會項目設計在內核上的整合。譬如,盲人門球原本為視力障礙者專設,球員不論視障等級一律戴上眼罩,借助球體內鈴鐺發出的聲音完成比拼。是否可以將這一運動加以改造,使之反過來包容明眼人,成為所有運動員蒙上眼睛即可自由選擇參加的項目,從而探索排除視覺之后人類體育可以具備的可能性?如此,“盲人門球”將成為“非視覺門球”,類似的項目整合將使健全—殘障從本質性的差異轉化為流動性的經驗,其文化隱喻也不再是美與丑、正常與異常、完滿與殘缺……
這當然只是一個難以捉摸的夢,畢竟,當代人身處身體理性化的鐵籠中無所遁形,從國足認同、強健情節到他者的意義總需有所著落,將身體天然的差異就此抹平也不啻于一種反智主義。我們僅僅暢想:體育文明的未來進程可以重拾原初的創造力,承載和延展每個人的、每一種情態的身體。
感謝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謝卓瀟老師為本文提供的寶貴建議。
參考資料(按引用先后排序):
體育產業生態圈:《殘奧會為什么“不好看”?》,2024-08-31,https://mp.weixin.qq.com/s/fJJ7PafZ8TO5PS4kdAv-tQ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 2006
Dan Goodley: Disability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SAGE 2011
Harlan Hahn, The politics of physical differences: Disability and discrimination, Social Issues, 1988, 44(1)
科林·巴恩斯、杰弗·默瑟,《探索殘障:一個社會學引論》,葛忠明、李敬 譯,人民出版社 2017
烏云裝扮者:《中文社交網絡不感興趣的殘奧會,正在重新討論“殘障”和“運動”,2024-08-29,https://mp.weixin.qq.com/s/nU3NfjeeJtaAeS7hiaBr_w
Anne Waldschmidt, Hanjo Berressem, & Moritz Ingwersen (eds.): Culture - Theory - Disability: Encounters Between Disability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transcript Verlag 2017
Vladimir E. Martínez-Bello: The representation of athletes during Paralympic and Olympic Games: a Foucauldi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 in newspapers, Disability and Society, 2023, 38 (6): 1053-1075
TIME: Olympic Sports That Are Hard on the Body and Lead to Injury, 2024-07-20, https://time.com/6999787/olympics-hardest-sports-body-injuries/
克里斯·希林:文化、技術與社會中的身體,李康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