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倪瑜遙
編輯 | 黃月
在近期院線電影中,《姥姥的外孫》可算一匹黑馬。影片上映一周已躋身中國市場泰影票房歷史前三,截至目前的豆瓣評分為9.0。
電影以清明祭祖儀式開始,以姥姥的葬禮結(jié)束,一個散居在泰國暹羅的潮汕家族是其中主角。子女成年后搬離父母家,三代人的生活漸行漸遠:守著老屋的姥姥信觀音菩薩,堅持不吃牛肉;大兒子阿強炒股,小兒子索伊賭博,女兒阿秀在超市當(dāng)?shù)陠T,各自奔忙;外孫阿安已不識得潮州話,輟學(xué)在家,幻想成為游戲主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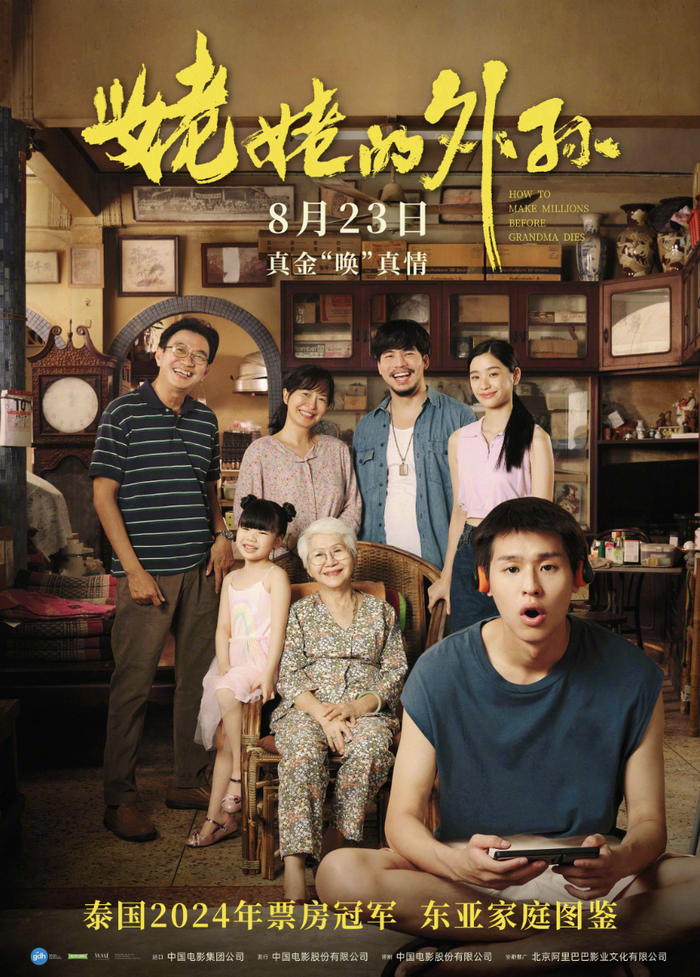
影片的主題是照護和親情,其敘事延續(xù)了華人家庭片的含蓄溫情。但導(dǎo)演并未止步于情感層面,而是直指親人之間的利益糾葛。溫情之下是堅硬的內(nèi)核:期許獲得遺產(chǎn)可以構(gòu)成照護親人的動機嗎?當(dāng)維系孝道倫理的土壤瓦解,還能靠什么來支撐家庭照護的責(zé)任?
家庭情感與利益戰(zhàn)爭
在清明祭祖儀式上,姥姥意外摔倒,之后被查出患癌。外孫阿安自此開始對姥姥的照護。他回到潮濕的老屋,被拉回到姥姥的生活節(jié)奏中。每天五點起床賣粥,給門前的花木剪枝澆水,按時帶姥姥去醫(yī)院化療。同時也受到姥姥的管束和挑剔:沖茶拜神的水不能用微波爐加熱,觀音像不能移動,睡覺只能在樓下。

近年來,家庭照護作為情感勞動、親情羈絆的主題常被書寫。對于照護者而言,照護親人是時間、體力和精神層面的多重付出,也是在陪伴中重新理解親人、認識死亡與告別的過程。界面文化此前曾專訪《照護》一書的作者凱博文,他指出:“人性的‘在場’(presence)是護理和照護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當(dāng)下的照護書寫多側(cè)重于情感經(jīng)驗,或多或少回避了對于利益的探討。《姥姥的外孫》更進一步,剖開親人之間的利益沖突,試圖補全在情感之外更立體的照護圖景。
除了是病人,姥姥還是有遺產(chǎn)待分割的家族長輩;除了是照護者,阿安還是需要本錢立足的年輕人。無論是阿安、母親還是兩個舅舅,他們都惦記姥姥的遺產(chǎn);而姥姥對財產(chǎn)分配也自有打算。這些糾葛并未隨疾病而隱退,在綿密的親情下,一場家庭戰(zhàn)爭如火如荼。

照護換遺產(chǎn)?
阿安照顧姥姥的初衷很功利——他想要姥姥的房子,他需要一筆錢。看到表妹阿梅照顧姥爺并最終繼承房產(chǎn),他決定依葫蘆畫瓢,把姥姥當(dāng)作“本錢”。盡管阿安也懷疑過這是否妥當(dāng),但自始至終,他對利益的訴求并未改變。
事實上,影片中的人物并不避諱談?wù)撳X。金錢的力量在大兒子阿強身上體現(xiàn)得最明顯。姥姥摔倒后,阿強沒時間照顧姥姥,給了妹妹阿秀一筆“陪護費”。此后他還想給阿安“工錢”,作為照顧姥姥的酬勞。阿秀讓阿安多陪陪患癌癥的姥姥,阿安的第一反應(yīng)是“你給我發(fā)工資嗎?”在情感之外,金錢也是連接家族成員的紐帶。
就連姥姥也抱怨:她任勞任怨地照顧父母,但父母什么都沒留給她。她的怨言反映出一種觀念:家庭照護作為一種情緒勞動,很多時候由女性承擔(dān),卻常被認為是瑣碎且無償?shù)模辽僭趧趧舆^程中是無償?shù)摹?/span>
英國作家羅斯·哈克曼在《情緒價值》一書中指出,與體力勞動、智力勞動一樣,情緒勞動也是一種需要時間、精力和技能的工作形式。在性別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情緒勞動被認為是女性化的,但人們卻常常忽視這種勞動的真正價值,無論是在公共領(lǐng)域還是家庭內(nèi)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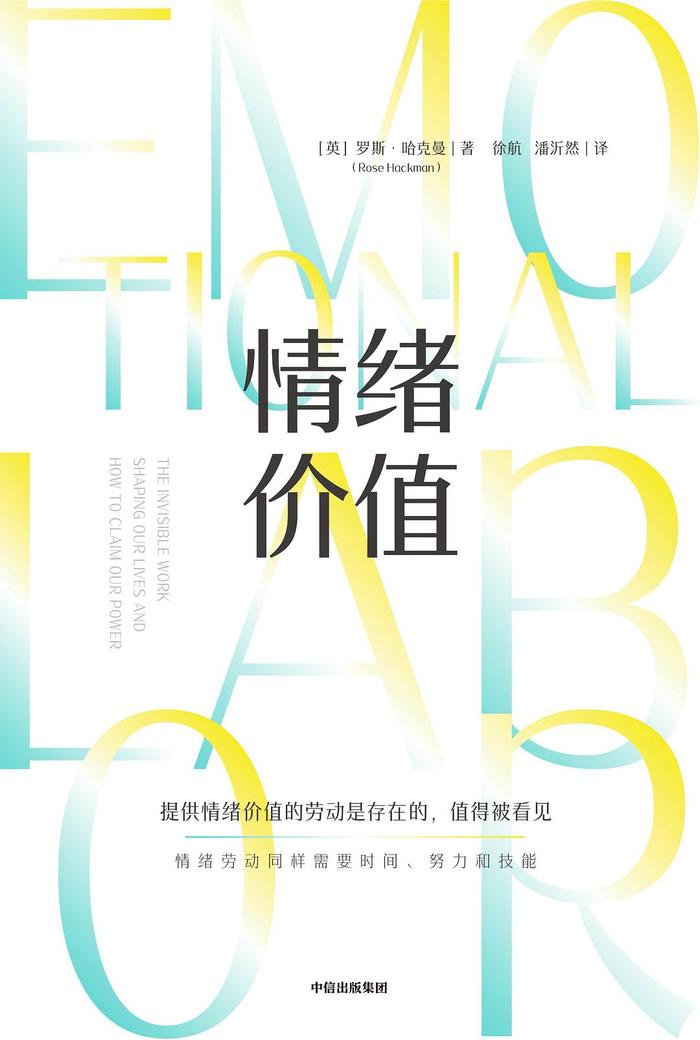
[英]羅斯·哈克曼 著 徐航 潘沂然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4-02
在華人的傳統(tǒng)觀念中,家庭照護是孝道倫理的一部分,子女照顧老人被認為是天經(jīng)地義之事。在當(dāng)代社會,這種“天經(jīng)地義”卻可能成為家庭矛盾的導(dǎo)火索。今年4月,胡泳在《當(dāng)一位北大教授成為24小時照護者》一文中談到:“在照護老人這種事情上,也需要開家庭會。怎么分工,去不去養(yǎng)老院,得病了怎么治療。中國人有個特點,很多事兒不明說,說了好像傷和氣。恰恰是很多時候你不明說,暗流的涌動就會導(dǎo)致很多矛盾。”
父權(quán)制本位的孝道倫理壓制了對于照護者的責(zé)任與利益的探討。孝道以家長的支配性權(quán)威為前提,照護者與被照護者之間并非平等關(guān)系。孔子主張“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晚輩對長輩的供養(yǎng)義務(wù)被強調(diào),而對利益分配的訴求則可能被視為不敬。
在華人傳統(tǒng)社會,即便女性承擔(dān)了照護責(zé)任,在財產(chǎn)分配中也難有話語權(quán)。法學(xué)學(xué)者羅冠男指出,在中國傳統(tǒng)的繼承制度中,財產(chǎn)被嚴格地留在父系家族內(nèi)部,以保證家族的延續(xù)。女性難以像她們的兄弟和丈夫那樣繼承財產(chǎn)。
這一不平等的原則在影片中也有所體現(xiàn)。盡管姥姥承擔(dān)了照護父母的主要責(zé)任,但她沒有繼承遺產(chǎn),因為家人認為“即便財產(chǎn)分給她,也會被她敗家的老公花光”。到了下一代人,相比于阿強和索伊,女兒阿秀付出了更多精力來照顧母親,但母親同樣沒有把遺產(chǎn)留給她。

對于更年輕的阿安和阿梅來說,他們照顧長輩的主要動因并不在于孝道倫理的約束,而在于與其他親屬競爭遺產(chǎn)。盡管有人批評“為了遺產(chǎn)而盡孝”的價值觀,但這恰恰是影片的一大亮點。電影直指照護者的責(zé)任與權(quán)利這一常被遮蔽的問題。當(dāng)維系孝道倫理的家族和禮法土壤瓦解,期許應(yīng)得的利益回報也是照護者的正常心態(tài)。
耶魯大學(xué)醫(yī)學(xué)人類學(xué)博士葛玫在著作《誰住進了養(yǎng)老院》中談到,人口流動、個體化、生育率下降等因素使子女越來越難盡贍養(yǎng)老人的儒家孝道。老年父母選擇住進養(yǎng)老院,或者減少自己的需求,但他們并不愿意用“不孝”來評價子女。社會學(xué)者吳心越在其關(guān)于養(yǎng)老機構(gòu)的論文中也指出,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加劇和家庭養(yǎng)老功能弱化,更多子女將老年照護“外包”給養(yǎng)老機構(gòu)。養(yǎng)老機構(gòu)作為“孝親代理”重新嵌入家庭秩序和孝道文化,建構(gòu)起照護專業(yè)主義。
拆解空洞的“孝”
無論是父母主動住進養(yǎng)老院,還是子女將孝道“外包”,都反映出了一個問題:當(dāng)傳統(tǒng)孝道在現(xiàn)代社會衰落,我們需要新的話語資源來理解照護和養(yǎng)老。《姥姥的外孫》中的臺詞“多出力者應(yīng)該多得遺產(chǎn)”就是一種對于照護的闡釋。阿梅則是這一觀念的成功踐行者。
電影中有一個細節(jié):包括姥爺在內(nèi)的親屬都覺得阿梅應(yīng)該找一份體面的工作,而不該守在姥爺床頭。言下之意,照護失能老人是盡孝,但犧牲了自己的前程,并不劃算。在這套價值體系中,為家族付出的孝道倫理讓位于功利的個人主義。
學(xué)習(xí)護理專業(yè)的阿梅看待照護的視角則更加“職業(yè)化”。她盡職照顧癱瘓的姥爺,在姥爺心目中爬到第一位,最終在姥爺去世后繼承房產(chǎn)。于她而言,照護親人是一份“輕松又賺錢的工作”,發(fā)揮專業(yè)技能,付出時間、勞動和情感,換取利益,毫不拖泥帶水。一端是照護的責(zé)任,另一端是優(yōu)先繼承遺產(chǎn)的權(quán)利,這是阿梅重新給出的天平,直接而自洽。
但如果說阿梅和阿安對于長輩只有功利的算計,也不盡然。阿梅很干脆地賣掉姥爺?shù)姆孔樱?dāng)阿安問她是否夢到過姥爺,她含淚說姥爺一定去了極樂世界,不會再牽掛她。她的祈愿也發(fā)自內(nèi)心。在得知姥姥將房子給了舅舅索伊?xí)r,阿安生氣地指責(zé)姥姥愛錯了人。但姥姥去世后,他將姥姥為他存的錢全部用來買墓地,這份付出也心甘情愿。
影片中還有一段精辟的對白,阿秀對母親說:“兒子繼承遺產(chǎn),女兒繼承癌癥。”母親回應(yīng)她:“我不知道最愛誰,但最希望你在我身邊。”女兒壓抑多年的委屈是真實的,母親在生命盡頭的依戀也是真實的。
照護病人的辛勞和對現(xiàn)實利益的渴求,感性的掛念與理性的計算,疾患降臨在姥姥身上,也將這個潮汕家族推向紛亂的潮水中。當(dāng)主人公們從父母之仁和子女之孝的框架中松綁,親人之間自然流淌的是更復(fù)雜也更真摯的感情。解構(gòu)空洞的孝道,轉(zhuǎn)而描摹家庭內(nèi)部現(xiàn)實而幽微的羈絆,這或許也是《姥姥的外孫》動人的地方。
參考資料:
【英】羅斯·哈克曼:《情緒價值》,徐航、潘沂然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
【美】葛玫:《誰住進了養(yǎng)老院 當(dāng)代中國的“銀發(fā)海嘯”與照護難題》,劉昱 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3.
鳳凰網(wǎng):《當(dāng)一位北大教授成為24小時照護者》,2024-04-10,https://culture.ifeng.com/c/8Yf87k3Wpd4
羅冠男:《我國繼承制度中的價值取向和利益平衡》,法學(xué)雜志. 2019 ,40 (10) .
鄭玉雙:《孝道與法治的司法調(diào)和》,清華法學(xué). 2019(04).
吳心越:《從“孤老救濟”到“孝親代理”:養(yǎng)老機構(gòu)的角色轉(zhuǎn)型與專業(yè)興起》,婦女研究論叢 . 2024 (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