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李彥慧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每個周六,“文化周報”向你匯總呈現最近一周國外文藝圈、出版界、書店業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我們關注安東尼·福奇出版回憶錄、青少年文學作品著迷“謀殺”題材、第77屆托尼獎等內容。
01 安東尼·福奇回憶錄出版,講述職業生涯的關鍵時刻
當地時間6月18日,美國前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S. Fauci)出版了自傳《隨時待命:一個醫生的公共衛生服務之旅》(On Call: A Doctor's Journey in Public Service),回顧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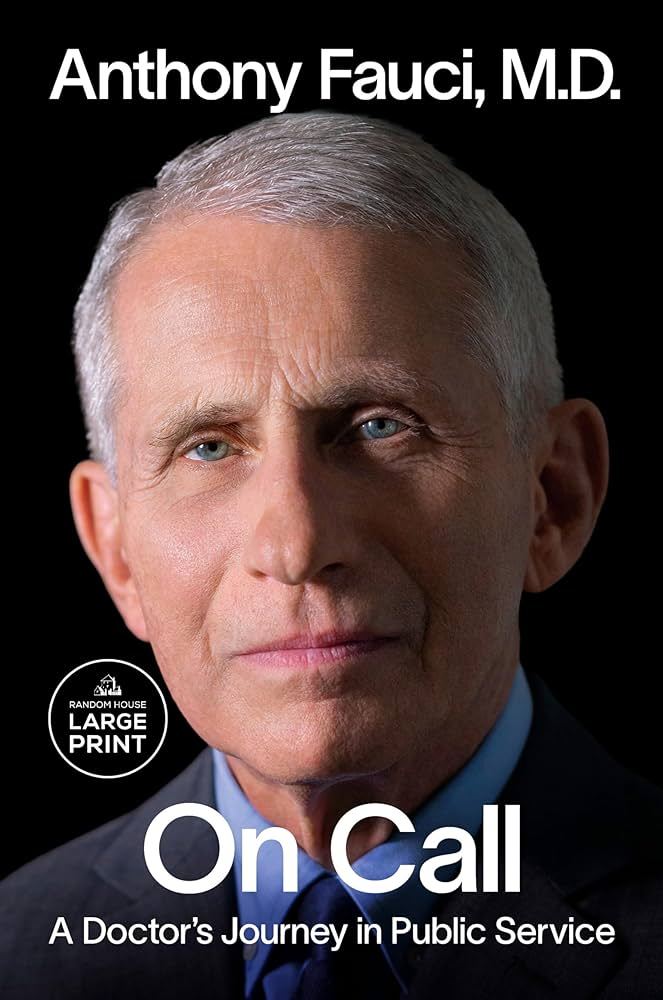
福奇1940年出生于美國紐約,1966年在康奈爾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968年加入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擔任NIAID的研究助理。16年后福奇出任該所所長,并于2022年卸任。福奇出任NIAID所長的38年間,服務了多任美國總統,致力于預防和治療感染性、免疫學以及過敏性疾病的研究。
即使新冠疫情沒有發生,福奇依然是過去五十年來美國醫學界最重要、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然而,正如福奇自己在書中所說,這場大流行使得他本人成為了“政治避雷針”——對一些人而言,他代表著希望,對另一些人而言,他則是邪惡的化身。
本月初,福奇在美國眾議院接受關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特別委員會的質詢時,共和黨人士瑪喬麗·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堅持稱呼他為“福奇先生”而非“福奇醫生”,并稱“那個人不配擁有醫生執照,他的執照應該被撤銷,他本人應該被關進監獄”。針對這樣荒謬的指控,福奇在《隨時待命》中表示,“安東尼·福奇首先是一名醫生。”
福奇任NIAID所長期間,經歷了兩次大型的公共衛生危機——HIV和新冠疫情。兩次危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涉及到感染、爭分奪秒的治療、公共宣傳以及尋找疫苗。每一次,福奇本人都會遭受大量誹謗,先是激進的艾滋病活動家,然后是反疫苗者、反對戴口罩者以及一大批陰謀論者。在新冠疫情期間,福奇被妖魔化,他被認為欺騙了國會、資助了危險的實驗室研究,并且要對無數不必要的死亡負責。福奇提到,此前他每個月會收到幾封辱罵信,但在新冠疫情期間,他和他的家人遭到了大量電子郵件、短信和電話的騷擾。福奇對自己女兒們遭受的騷擾感到尤為憤怒,他表示“想猛烈抨擊那些恐嚇無辜年輕女性的人”。

福奇表示,將回憶錄命名為《隨時待命》,是因為在他看來醫學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種使命。他將自己的這一信念追溯到童年時期——福奇的父親是一位藥劑師,他總是慷慨地對待那些付不起藥費的病人。福奇寫道,后來,當他的影響力逐漸增大,被允許進入白宮并向總統、副總統以及白宮工作人員提出建議時,他的一位導師提醒他“將每一次進入那扇門都視為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而要做好“做正確的事”的心理準備。
福奇以不關心政治聞名,無論是在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的政府中,他都推動了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在比爾·克林頓政府期間,福奇推動創建了一個專門用于艾滋病病毒疫苗研究的中心;在小布什政府期間則推動了為發展中國家艾滋病患者提供藥物的項目。
在這本長達450頁的回憶錄中,福奇用了大約70頁的篇幅講述了新冠疫情爆發的第一年,他坦率地描述了自己與特朗普的關系“很復雜”。起初,福奇發現特朗普比他預期的“更風度翩翩”。然而,他回憶了自己2020年2月與特朗普的一次通話,他提醒特朗普不要低估形勢的嚴重性,但第二天,特朗普就在南卡羅納州的一次集會上稱新冠病毒是民主黨的“新騙局”。

福奇的麻煩并沒有隨著特朗普離開白宮而結束,相反,攻擊他成為了極端共和黨人對現任總統拜登以及民主黨人“發動戰爭”的某種方式。在書中,福奇對自己出錯的地方保持開放態度,他強調,雖然人們會將科學和“不變的真理”聯系在一起,但事實上,科學是一個“不斷發現新信息的過程”。人們想從醫學、科學中尋求明確的答案,但隨著對病毒理解的發展,科學家們提供的建議也不得不發生變化。
在本書的結尾,福奇也表達了對社會現狀的不安:“我們已經發現,完全捏造的事情成為了被一些人接受的‘事實’。如果這種‘真相危機’持續下去,未來大流行病的影響將會更嚴重。”
02 第77屆托尼獎創造多個歷史性時刻
當地時間6月16日,第77屆托尼獎(Tony Award)頒獎典禮于美國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的大衛·H·科赫劇院(The David H. Koch Theater)舉行。講述20世紀70年代一支嶄露頭角的搖滾樂隊錄制新專輯過程的話劇《立體聲》(Stereophonic)斬獲了包括最佳話劇、最佳話劇導演在內的5項大獎。《立體聲》此前獲得了13項提名,打破了歷史上托尼獎話劇類提名紀錄。
除《立體聲》外,本屆托尼獎還創造了多個歷史時刻。今年10位最佳導演的提名中,有7位是女性導演。導演丹雅·泰莫(Danya Taymor)憑借《局外人》(The Outsiders)成為了第六位獲得托尼獎最佳音樂劇導演的女性導演。演員卡拉·楊(Kara Young)則成為了第一位連續三年獲得提名的黑人演員。今年她憑借在《普利的勝利》(Purlie Victorious)中的精湛表演獲得了最佳話劇女配角獎。在接受采訪時,楊表示自己延續了黑人女演員魯比·迪(Ruby Dee)、黑人演員及導演奧西·戴維斯(Ossie Davis)的遺產(兩位演員都曾出演過本劇),“63年前,他們的工作并沒有獲得應有的榮譽。這(托尼獎)是對在我之前的所有人的認可。”

曾在哈利·波特系列電影中飾演哈利·波特的丹尼爾·雷德克里夫(Daniel Radcliffe)當晚捧得了最佳音樂劇男配角獎,他與托尼獎最佳男主角得主喬納森·格羅夫(Jonathan Groff)一起出演了《歡樂歲月》(Merrily We Roll Along)。格羅夫將自己成功的表演歸功于《歡樂歲月》的導演瑪麗亞·弗里德曼(Maria Friedman),后者也收獲了今年最佳音樂劇導演的提名。“毫無疑問,一位女性導演在角色中發現了其中的人性與愛,專注于友誼與人際關系,而不是讓角色變得憤世嫉俗。” 格羅夫說。
托尼獎1947年由美國戲劇協會設立,旨在表彰每年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最佳音樂劇和話劇,是美國戲劇領域的最高獎項。
03 為什么青少年讀者著迷“謀殺”題材文學作品?
青少年文學(young adult literature,簡稱YA)是為12-18歲的青少年讀者創作的文學作品,題材涵蓋了幾乎所有門類,《饑餓游戲》《心跳漏一拍》等暢銷書就屬于青少年文學。
據《書商》(Bookseller)雜志報道,近年來,恐怖驚悚小說的銷售額在2022-2023年間增長了54%,達到770萬英鎊,這也是有準確記錄以來該類型小說銷售額最高的一次。青少年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類似的狀況——年輕的讀者們似乎更“偏愛”以謀殺、驚悚情節為核心的作品。
這類青少年文學作品通常伴有懸疑色彩,閱讀這樣的作品就如同玩角色扮演類游戲,讀者能有機會與主角一起拼湊線索,積極地參與到故事當中。當情節出現重大轉折或真相大白時,跟隨主角一起“破案”的讀者常常能從中獲得極高的成就感。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以游戲題材或高風險競賽為特點的青少年文學作品數量激增。
此外,青少年讀者還認為有驚悚情節的小說能夠幫助自己“理順混亂的大腦”。格洛麗亞·馬克(Gloria Mark)在《注意力廣度》(Attention Span)中揭示了她從2004年以來進行的一項調查的結果,她發現,人們集中精神觀看屏幕的平均時長從2.5分鐘下降到了47秒。曾出版過幾本青少年讀者驚悚小說的作家戴安娜·厄本(Diana Urban)近期在《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上的文章也指出,數字時代中的青少年注意力和集中力都有所下降,但閱讀驚悚小說卻能讓他們擺脫注意力不集中的困境——一旦讀者試圖弄清真相,他們就會獲得閱讀的強大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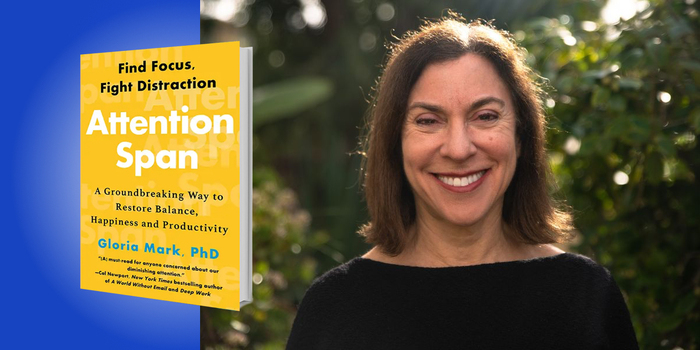
厄本也認為,以謀殺、驚悚情節為核心的小說一方面給了青少年們探索人性陰暗面的途徑。正如那些大受歡迎的、與真實犯罪相關的電視節目與播客,對受眾而言有一種近乎病態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這些小說也為青少年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間,讓他們通過故事中角色的經歷探索與自己相關的事件,包括校園欺凌、親友過世等等。例如,作家辛迪·R·X(Cindy·R·X)在作品《完美小怪獸》(Perfect Little Monsters)中講述了高中校園內的一起謀殺,并反思了校園欺凌。在厄本看來,這樣的書為青少年讀者們提供了一種處理沉重話題的方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他們復仇的欲望。
參考資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4/06/18/books/review/on-call-anthony-fauci.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06/14/us/politics/fauci-trump-book-covid.html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4/06/24/on-call-a-doctors-journey-in-public-service-anthony-fauci-book-review
https://www.publishersweekly.com/pw/by-topic/childrens/childrens-authors/article/95257-why-ya-readers-love-murder.html
https://www.forbes.com/sites/jerylbrunner/2024/06/19/this-years-tony-awards-celebrated-women-in-an-epic-and-historic-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