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為什么在美國這樣一個資本具有超然地位的國家,文學正典中關于金錢的小說卻那么少?這個困惑驅動著埃爾南·迪亞斯(Hernan Diaz)寫了一部小說——《信任》(Trust)。
從四個不同身份的人、四種不同的視角出發,《信任》講述了1920年代一個華爾街大亨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信任》在2023年獲得普利策小說獎,至今已有37個譯本,正由HBO改編為限定劇,由凱特·溫斯萊特擔任制片和主演,預計2025年播出。
這一成就讓迪亞斯處于某種眩暈之中,對生活中的巨大變化有些不知所措。本月在上海舉辦的新書發布會上,他說,“我在最狂野的夢里,沒有想過會來上海發布我的新書簡體中文譯本。我現在還在等人過來叫醒我說這是一個夢,一個錯誤的幻覺。”

獲普利策獎的作品是他的第二部小說,在此之前,44歲的他被一家小型出版社接納——那家出版社一年只有一天接受主動投稿——《遠方》(In the Distance)才得以出版。而在更長的人生灰暗期里,迪亞斯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采訪時說,“被拒絕的冷酷陰影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籠罩著我,但出于對語言和句子純粹的熱愛,我一直在寫。”
《遠方》和《信任》講述的都是發生在美國歷史關鍵時期的故事:前者的時代背景是美國西部的淘金熱,后者發生在大蕭條時期。迪亞斯對隱藏在財富故事背后的女性更感興趣,這也構成了貫穿《信任》全書的一條線索。

“我想重新解釋這樣一種歷史的書寫,我想看到為什么一半的人口這樣默默無聞地被清除出了我們的歷史。”
01 沒有任何虛構作品能脫離歷史存在
界面文化:《遠方》的時代背景是美國西部的淘金熱,《信任》則發生在大蕭條時期,都是美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你為什么對美國歷史如此感興趣?你會定義自己為歷史小說家嗎?
埃爾南·迪亞斯:哦絕不!我認為“歷史小說”是一個很蠢的詞。我從來沒有讀過任何“不是歷史的”(ahistorical)作品,所有的虛構作品都是“歷史的”,虛構作品以文字書寫,文字是沉淀下來的歷史,語言就是一種歷史制度。寫作形式是歷史的、文學類型是歷史的,甚至我們對語氣和措辭的感知也是歷史的。沒有任何虛構作品能脫離歷史存在。
當你說歷史小說時,你或許是指那些設定在可辨識的歷史瞬間的小說,我同樣對這種小說不感興趣。我只是對那些我有共鳴的故事感興趣——既在情感層面打動我,也在政治層面刺激我的思考。它們是那些吸引我的文學傳統中有待解決的、亟需探索的內容,這里存在我發揮的空間。
以西部小說為例,我對評價那個歷史時期沒有太大興趣,當我把西部小說當作一種文學類型的時候,我覺得奇怪的是,為什么它從未成為最卓越的美國文學類型?(西部小說)粉飾了美國歷史中最糟糕的面向:以種族滅絕為代價進行的“深入荒野”,對自然的剝削,厭女,槍支迷戀,以及美國社會至今依然沉迷其中的治安文化(vigilante culture),這些元素在西部小說中都有所指涉。我們很自然會認為,這將成為一種國家敘事,但并沒有。西部小說一直是邊緣化的、劣質的(pulpy)廉價小說(dime novel),在文學正典中難見蹤影。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文學謎團,而這也給了我很大的創作空間,而不是拜倒在神圣的文學傳統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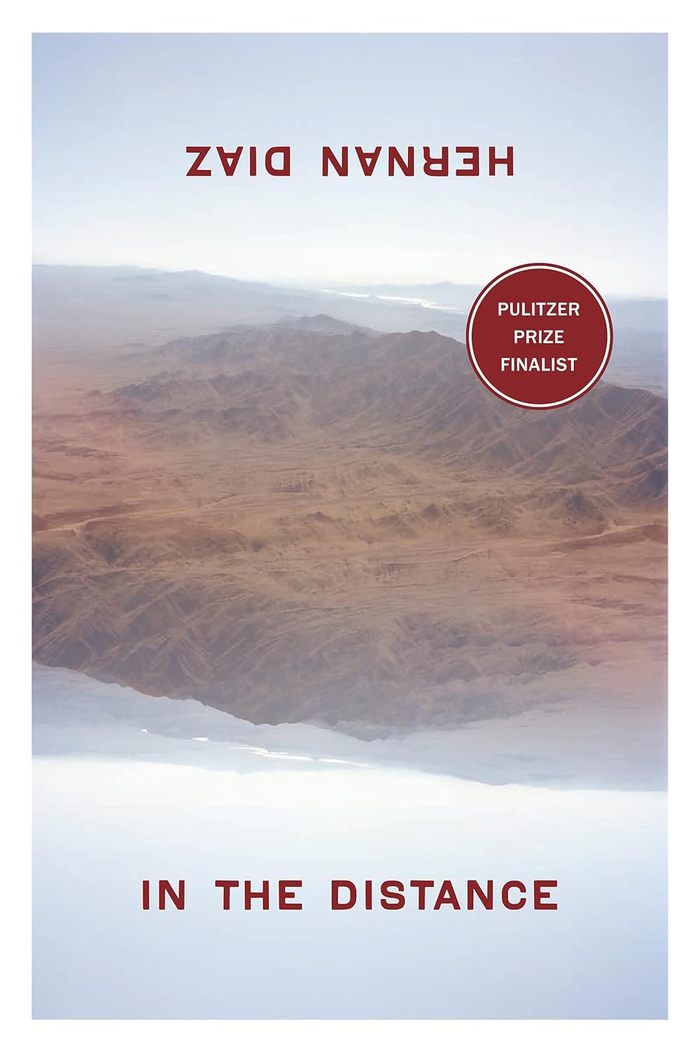
Hernan Diaz
Coffee House Press 2017
我出于各種原因對金錢感興趣,我以為讀美國小說時肯定會發現美國文學正典中有很多這方面的故事,但是并沒有。我發現這里也有供我發揮的空間——在一個資本具有如此神秘、如此超越性地位的國家,我們本應有許多關于金錢的書,這太讓人困惑了。這種困惑是我創作的動力。
所以,我并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歷史小說家,我只是對一些能夠引領我們探索未知領域的文學問題感興趣。
界面文化:《信任》的靈感來自何處?書中描寫的那位大亨安德魯·貝維爾是完全虛構的還是有歷史原型?
埃爾南·迪亞斯:是完全虛構的。我閱讀了(書中)艾達讀過的所有那些偉大美國人的自傳,亨利·福特、安德魯·卡內基等等,但“安德魯·貝維爾”是我創造出來的角色。
我確實發現了一個歷史人物,杰西·利弗莫爾(Jesse Livermore),曾在1929年股市崩盤中賣空了股票大賺一筆。他多年后寫過一本書《如何在股市中交易》(How to Trade in Stocks),然后在1940年自殺,我不知道具體原因,顯然他患有抑郁癥。所以歷史上確實有人在1929年股市崩盤中獲益,但他不是股市崩盤的幕后黑手。沒有誰有能力操縱如此規模的股災,這只有在小說中才會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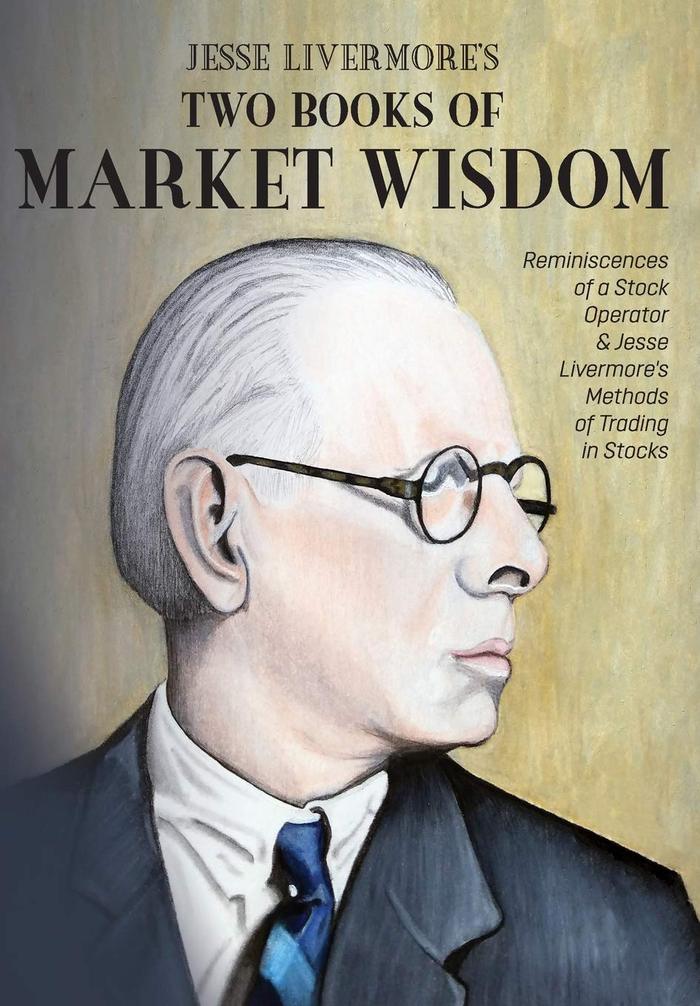
Jesse Lauriston Livermore, Edwin Lefèvre & Richard DeMille Wyckoff
Mockingbird Press 2019
界面文化:這本書的書名也很有趣,“Trust”既有信任的意思(但我們不能信任這位作者!),也是一個金融術語。
埃爾南·迪亞斯:這部小說有很多個敘事層次,我希望書名能在語義上表達出這個特點,具有多重含義。Trust這個書名實現了三件事:第一,這是一個金融術語,甚至在金融領域這個單詞也有多重含義,我感興趣的是“壟斷”,而這部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嘗試壟斷真相的故事;其次,“trust”也是一個具有情感意義的名詞;另外,這也是我對讀者的一個請求——請你信任這本書。

[美]埃爾南·迪亞斯 著 劉健 譯
群島圖書 |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4-5
02 金融事務對女性的排除曠日持久、有意為之
界面文化:揭示父權制如何壓制女性聲音顯然是《信任》的主旨之一。比如說在小說的前三個部分,我們都看到了那位金融家或多或少在試著控制他的妻子、減少她的影響力和存在感。直到讀第四部分妻子的日記,我們才會意識到這本書前半部的男性中心敘事多么可笑。為什么這本書中女性角色和女性聲音如此重要?
埃爾南·迪亞斯:當我書寫美國資本的故事時,我感到自己必須寫寫女性是如何被我們國家的金融事務排除在外的,這種對女性的排斥曠日持久、有意為之,且已經體系化了。這是我在書中創作這些女性角色的原因。我意識到她們才是我感興趣的角色,我對“偉大男性”不敢興趣,我想轉換一下主角。
界面文化:雖然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發生在100年前的故事,但我們是如此熟悉這個故事——我們對女性的認知、對女性應該在社會和家庭中占據何種角色的看法并沒有發生很大的改變。
埃爾南·迪亞斯:是啊。至少在美國,毫無疑問進步是發生了的,但還不夠。我們還沒有取得性別同工同酬,公司董事會成員依然絕大多數都是男性。人們依然認為,女性掌權時過于情緒化,這是一種完全荒謬的觀點。還有對女性應該承擔家務的期待,認為女性應該是充滿母性的、能帶來家庭溫暖的人。我們依然生活在父權制社會中,很不幸,我寫的這個故事與當下的情況依然相關。
界面文化:今天一些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傾向于認為,男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女人,男性作家不可能擺脫性別刻板印象寫出可信的女性角色。你會如何回應這種質疑呢?
埃爾南·迪亞斯:對我來說,作家工作的核心組成部分以及道德責任之一,就是嘗試去想象成為他人是怎樣的。也許我會失敗,但這種嘗試是成為小說家的一個關鍵。我認為那些聲稱只有自己掌握真相的人讓人害怕,你剛才說的這個觀點就有點這種意味,我不喜歡其中的原教旨主義色彩。說這些話的人或許不是我的對話者。
界面文化:《信任》似乎也在呼應當下的危機:貧富差距在擴大、人們擔心下一場經濟危機即將來臨、富人用金融手段獲取了太多財富等等。這是你寫《信任》的意圖嗎?
埃爾南·迪亞斯:不,我不是那種政治性的寫作者,我不想說教。通過一個發生在1920年代的故事展示一個關于我們時代的寓言,這不是我的目的。在寫作過程中,1920年代和2020年代的相似之處、關聯和對稱性慢慢浮現出來——請相信我,這不是我刻意為之的。
話雖如此,我身上有一部分當然對這些話題是有興趣的。當你書寫美國的資本時,肯定會涉及到不平等問題。“特權”(privilege)是這本書開篇第一句話中出現的詞語,這是一個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希望這本書以一個包含“特權”的句子為開頭,因為這本書就是講述特權的——金融特權、性別特權、種族特權。
界面文化:在金融家安德魯·貝維爾的自傳里,很多段落都讓我們想到幾十年來在美國社會和許多其他社會深入人心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
埃爾南·迪亞斯:沒錯。雖然我不是一個歷史小說家,我依然在寫作時做了很多研究去了解我筆下的那個時代,閱讀了很多一手史料。唯一的例外是,我也讀了很多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我鄙視這個人)。我希望通過安德魯·貝維爾這個角色展示那種自由派的(libertarian)、硬核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新自由主義的腔調: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都是糟糕的、社會福利讓人懶惰、對投資人和股東好的東西對全社會來說也是好的、涓滴經濟學、對亞當·斯密的原教旨主義理解、放任自由的市場邏輯等等。我把這個作為靶子,是因為我認為這是美國社會的痛苦根源。這是這本書中最明顯具有政治性的部分。
03 厭女跨越階級和意識形態
界面文化:艾達這個角色也很有趣,她是一個意大利裔二代移民。我們知道在美國移民史中,意大利人曾是歐洲移民中最受歧視的群體。這個移民故事的深意是什么?
迪亞斯:這本書中出現意大利元素有幾個原因。首先,我有一半的意大利血統,我的母親來自意大利,我至今仍然有意大利護照。我是作為移民來到紐約的,當然我的移民過程是很舒服的,我獲得了獎學金,在紐約攻讀博士學位。當你書寫一個發生在紐約的故事時,你不可能不寫移民。書寫意大利移民的故事是我思考我的過去的方式。我的曾祖父母移民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但他們很有可能登上另外一艘跨洋輪船來到紐約,這完全是一個偶然。

另外,意大利移民在20世紀的前二十年存在感非常強,他們積極參與聯盟、社區和政治組織的建立,但這些組織以一種極端暴力的方式被打壓關停了。其中最可疑的一個案例發生在1927年,許多意大利組織者、活動家被謀殺、被處決、被囚禁,而這段歷史完全從美國歷史中清除了。《信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討論誰能夠講述故事,以及歷史是如何被操縱的。這就是非常明顯的一個例子。美國有如此深厚豐富的移民史,但在大學里沒有人談論。
界面文化:艾達的父親面臨著雙重歧視——他既是意大利人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更有趣的是,他似乎代表了事關商業、金融和資本主義的美國價值觀的反面。
迪亞斯:你說得對,這個在小說中甚至沒有自己名字的角色代表了美國價值觀以及美國夢的對立面。對我來說這個角色有趣的地方是,他和金融大亨安德魯·貝維爾雖然背道而馳,但最終相遇了——美國資本家和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都不相信國家。這是一個古怪的悖論,他們出于不同的原因擁有同一個敵人,他們都認為國家主宰是萬惡的根源。這是這兩個角色關系中非常諷刺性的一點。
界面文化:而且他們都厭女。
迪亞斯:這是我創作艾達父親角色的主要目的,我想說明,厭女是跨越階級和意識形態壁壘的。一個左翼、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在家庭政治當中依然非常反動、保守、厭女。遺憾的是,這種情況并不罕見。
界面文化:在社會科學領域,我們常常說階級、性別和種族構成三種主要的社會沖突,它們都在《信任》中出現了。如果說這是一部講述美國故事的小說,那么美國社會最顯著的沖突是什么呢?
埃爾南·迪亞斯:我認為種族是引發最多痛苦、最隱形、奪走了最多生命的沖突。另外,如今對女性的壓迫在美國進入了一個非常戲劇性的階段。最高法院推翻了“羅伊訴韋德案”,將女性降級為二等公民,她們被剝奪了生殖權利,不再有完整的身體自主權,僅僅想到這一點就讓我火冒三丈。最高法院的這個決定會讓許多女性失去生命,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后果。階級不平等當然也是一個美國社會非常嚴峻的問題,而我認為解決方案其實是有的,就是合理的稅收,但沒有人有動力推動政策改變。
界面文化:在5月11日的對談中,你談到了權力為何需要故事和賦予自身合法性的敘事。正如小說中金融家這個角色所展示的,掌權者能夠抹去對自己不利的敘事,扭曲現實。普通人可以做什么呢?書寫還有意義嗎?
埃爾南·迪亞斯:寫作當然意義重大,否則我就不會寫作、不會成為現在這樣的讀者了。我們所有人都能做的事非常簡單,就是了解情況,批判性地看待任何單一來源的信息。要取得平衡并不容易,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支持一種樂觀主義的多疑——我認為我們應該既保持警覺,又保持希望。我理解多疑可能會導向虛無主義和赤裸裸的陰謀論,這不是我說“多疑”的本意——我的意思是,保持懷疑精神(mistrustful)。但很多人會問,怎樣才算足夠呢?我的回答是大量閱讀,帶著懷疑去閱讀。你讀的越多,你的懷疑精神就越微妙、越清晰,你就能提出更好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