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伍洋宇
界面新聞編輯 | 宋佳楠
Cheyne本應有著一個既定的、范本一樣的優秀人生。
他聰明,學習能力強。小學、初中、高中,都是“別人家的孩子”——同齡人里最拔尖的。他出生于一個醫學世家,從小的耳濡目染和興趣使然,助他順利考入中山大學臨床醫學專業。八年后,他拿到了醫學博士學位。
畢業那年,在家人的建議與安排下,Cheyne進入家鄉城市一所三甲醫院,成為一名住院醫師。
一切都像寫好的劇本那樣,手握高學歷和“鐵飯碗”工作的他,只要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就可以輕松得到被家人乃至整個世俗所認可的人生。
但這種人生軌跡行進不到兩年,他決定親手將其“變軌”。

不少人擠破頭顱想進入的“體制內”,對Cheyne而言只是一個僵化的系統。他想離開,但遭到了家人的反對。經過一番對抗與溝通,Cheyne辭掉了住院醫師的工作去了北京,成了一名藥企研發人員。
藥物臨床研發是他攻讀博士期間就深埋心底的志向所在。那是一種比做博士課題更精密復雜,還需挑戰現實的研究工作。
一年多時間,Cheyne憑借努力得到更多信任,工作內容從偏后期的分析、驗證、匯總,走向更前期的計劃與決策,例如針對一份抗癌藥物在首次人體研究中探索出最合適的劑量。
這是他新的一年最關切的目標:讓手頭的藥物順利度過一期研究,去幫到適應癥的腫瘤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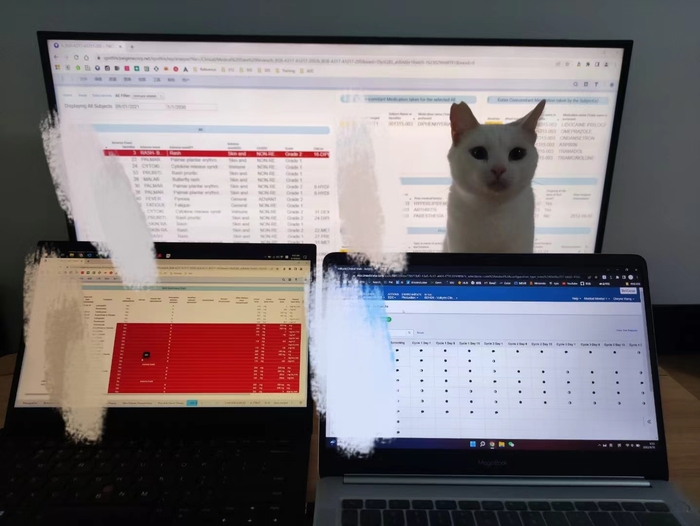
在上一個人生階段,Cheyne最討厭的就是不確定性,他甚至會想好去哪里養老,自己的葬禮上要播放什么樣的音樂——痛仰樂隊的《再見杰克》。
“讓我歡樂一點,讓我歡樂一點,不要讓疑問留停在心間。”歌中這樣唱道。
但現在,他學會了坦然面對變化,“我接受了唯一不變的就是什么都在變。”
他設想的葬禮背景音樂也變成了二手玫瑰的《我要開花》,“我要開花,我要發芽,我要春風帶雨的嘩啦啦。”
以下是Cheyne的自述,經界面新聞編輯整理:
畢業進醫院工作,一方面出于家里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想為臨床研發積累經驗。我不是多么討厭醫院,只因為它不是我自主選擇的。
這種安排會讓我感到不安,潛意識里就覺得不會太長久,尤其是看到醫院很多不專業的管理之后。
我們幾個一線醫務人員曾被派去參加市級衛生系統的一項比賽,每個人都投入了很大精力備賽,幾乎脫產了一個月,也為醫院贏得很多獎項。但回來之后,行政因為我們脫產要扣掉當月的績效。我當時真的覺得,“這家醫院要完蛋了”。
現在看這件事可能沒多嚴重,但我認為折射出了這家醫院對待醫生的態度,它可能只是把你當一塊磚來使。之后我就開始和家里人溝通辭職的事。
他們明確反對,不希望我失去這份穩定的工作,覺得穩定壓倒一切,認為在醫院才能學到真本事。這可能存在認知局限,畢竟我的家人沒有接觸過體制外的工作。
但對我而言,穩定的差,還不如不要。面對當時的處境,我想象不到未來會有什么好的出路和生活,統統不是我想要的。
我盡量不和父母產生激烈的正面沖突,但他們會因此焦慮失眠。我能做到的妥協就是,拿到offer之后再離職。好在家里人看完第一個offer的條件之后,不像一開始那么抵觸了。
入職新公司后,我第一次從北京回家過年,他們都覺得我有了明顯變化。以前會對未來感到迷茫、焦慮,但那次回去會和他們討論自己比較明確的目標,也開始為未來做長期打算,精神狀態積極了很多。
讓長輩轉變態度的確需要時間。第一年時,他們只是稍微松了一點口,我偶爾會皮一下說,“你看我當時的選擇是正確的吧!”到第二、第三年時,他們就越來越覺得我是對的,甚至會說,把現在這份工作干久一點。
我上學時就想做臨床研發。讀博的最后兩年在醫院,正好跟一家公司的研發項目接觸比較多。我覺得臨床研發有一種“秩序的美”。
他們會認真對患者進行隨訪。當時一個患者的資料就可以塞滿一整本活頁夾,有新華字典那么厚,紙張是A4紙大小。里面什么都有,比我們寫病歷詳細多了。這需要耗費很多人力物力,是一個博士生遠不能企及的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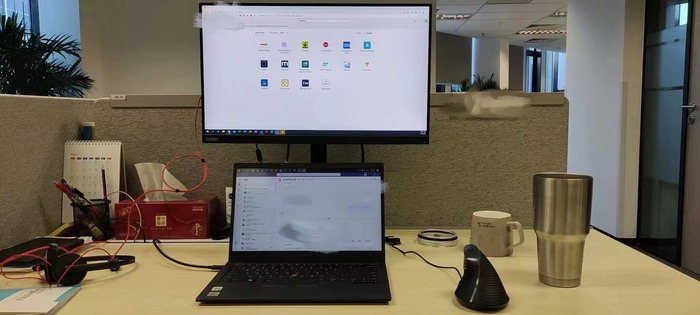
在這家公司,我所在的部門是“臨床開發部”。我們的工作,就是把實驗室的非臨床研究藥物成果往臨床研究階段推進,找到對應的適應癥以及合適的劑量,讓它既能夠有效,又沒有特別嚴重的副作用。最后再通過一系列驗證、說明的文件報告材料,讓它獲得上市批準。
我的崗位叫做“醫學監察員”,面對不同的項目和階段有不同的職責。比如說,對于錄入信息系統當中的患者數據,我們要核查是否符合邏輯。一方面要判斷是否有錯錄、誤解,或者說有沒有按照方案準確執行;另一方面要監察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號,用于決策。
監察是否遵循方案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研究數據和結論的可靠性以及科學價值。
剛開始會比較興奮,可能因為興趣使然,就算是從0開始學也不覺得枯燥,反而覺得時間不夠用。如果有一些之前沒接觸過的工作內容需要我幫忙,我也會盡可能去幫。在我看來,學習如何做一件事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做這件事。這可能挺“卷”的,但我的同事們也都很厲害。
今年我的工作最重要的變化是,從之前偏二期、三期的研究,到現在可以更多介入一期的研究了,角色更偏計劃和決策。
一期研究相當于首次人體研究,意味著藥物已經完成了實驗室階段,要第一次在人體當中去探索合適的劑量,這也是不確定性最大的一個階段。
我正在做的一期研究,適應癥有很多種,包括肺癌、膀胱癌、卵巢癌、食管癌、胃癌等等。一般來說,如果不是藥物本身有一些局限,我們希望適應癥越多越好,因為這樣能夠幫到更多的病人。
正常情況下,一期研究可能會持續三年左右,我們現在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當然,并不是說每款藥都一定要上市,畢竟臨床研發極易失敗,眾多一期項目里,能有一個進入二期就不錯了。從二期到三期、三期到上市也同理。
相比我在博士階段了解到的臨床藥物研發,我現在對它的認識肯定是更深了。之前只覺得有“秩序的美”,現在面對大量的不確定性在未知里探索,才發現有這么多有趣的事情。
我上一個人生階段最討厭的就是不確定性。在新的階段,我覺得唯一不變的就是什么都在變,人要擁抱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