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北風(fēng)呼嘯,寒潮來臨,文化界在12月接連失去了社會學(xué)家李強、當(dāng)代藝術(shù)家余友涵、政治思想史家約翰·波考克、意大利哲學(xué)家安東尼奧·奈格里、法學(xué)家江平、漢學(xué)家伊懋可……
我們試圖以這篇十分有限的盤點,記錄下今年文化界的逝者,以寄哀思。其中最年長的逝者是翻譯家楊苡,享年103歲,她的人生百年經(jīng)歷了軍閥混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新中國成立……從1919年到2023年,她趟過了最濃郁跌宕的一段近代中國史。其中最年輕的逝者是導(dǎo)演、作家萬瑪才旦,“才旦”在藏語里有壽命永固之意,而他的生命卻停留在了53歲。萬瑪才旦的作品還在影響著更多觀眾,他的電影《雪豹》今年獲得了第3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jié)最佳影片獎。
每逢年底,逝者人數(shù)似乎就會陡增。這并不僅僅是令人傷感的直覺判斷,更有科學(xué)上的證明。紐約消費教育組織美國科學(xué)與健康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Science and Health)微生物學(xué)家Alex Berezow博士表示,冬天去世的人數(shù)確實更多。美國疾病預(yù)防控制中心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清楚地表明,在美國,十二月、一月和二月是一年中死亡人數(shù)最多的月份。
愿你健康,并和我們一起追思懷念今年的逝者。也許有些名字沒有進(jìn)入媒體盤點,沒有在公眾心目中得到反復(fù)的紀(jì)念與哀悼,但對你我來說卻至關(guān)重要,也請在年底這個時刻,默默地追思與致敬,因為沒有一個生命曾經(jīng)白活,或多或少,世界已經(jīng)因他們而改變。
在2023年年末,界面文化(公眾號ID:BooksAndFun)和大家一起回望這一年遠(yuǎn)去的文化界人士。

王智量
俄語翻譯家
1928年6月-2023年1月2日

“我有一個好處,就是永遠(yuǎn)堅持我的信念。這樣我才活了下來。”1957年,在中國社科院文學(xué)研究所工作的王智量卷入了當(dāng)時的政治運動,被派到河北農(nóng)村改造,臨行前,他與所長何其芳偶遇,后者對他說:“《奧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王智量大哭一場,將本來不敢?guī)У摹秺W涅金》塞進(jìn)了行李。改造時,哪怕背上背負(fù)著一百多斤的石頭,王智量也會默念著《奧涅金》,在心里把它們譯成中文。晚上,他就把斟酌寫好的詩句寫在糊墻的報紙、香煙盒、草紙等能找到的廢紙上。回到上海后,王智量一邊做重體力勞動,一邊翻譯,在黃浦江邊,他邊扛木頭邊口中念念有詞,一度引發(fā)警察跟蹤。這部書在1962年翻譯完成后,又經(jīng)歷了數(shù)十次修改,才最終定稿。自由體和后來修改完成的古典體譯本都得以出版。84歲時,王智量還完成了該書的第三版翻譯。
1978年,在華東師范大學(xué)校長劉佛年的幫助之下,50歲的王智量破格成為了華師大教師。他終于得以站上大學(xué)講臺,講授俄國文學(xué)。這以后,他“每天只睡幾個小時,4點半起床,一分鐘都不浪費”,目的是“把那20年補回來”。2006年9月,中國翻譯協(xié)會設(shè)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2019年,王智量獲得了這一獎項。
顧嘉輝
加拿大籍華裔作曲家
1931年1月1日-2023年1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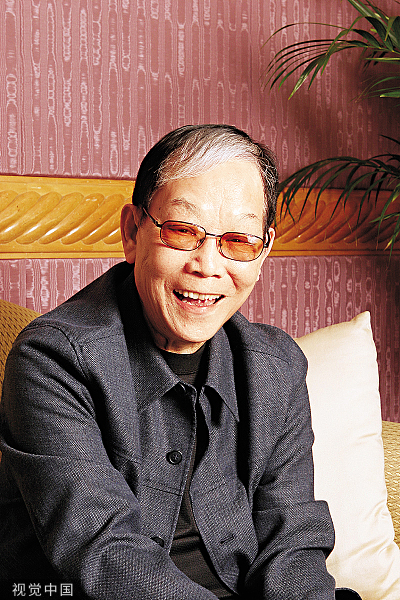
顧嘉輝的父親顧淡明曾在汪偽政府就職,后因被指認(rèn)為漢奸而帶著姨太太逃往中國香港地區(qū)。顧嘉輝也跟著姐姐奔赴香港地區(qū)尋找家人。赴港之后,二人主要靠姐姐顧媚出外唱歌賺取基本的生活費用。顧嘉輝在姐姐影響下開始對音樂產(chǎn)生興趣,成為了一名琴師。1961年,美國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xué)院的校長在香港地區(qū)某夜總會聽到了顧嘉輝的演奏,主動為他申請了一筆獎學(xué)金,并邀請他前往美國深造。在邵逸夫等人的資助下,顧嘉輝遠(yuǎn)赴伯克利音樂學(xué)院深造了兩年,也成為了這所學(xué)校第一位中國學(xué)生。深造期間,他首次參加邵氏電影《不了情》的作曲比賽,首作《夢》獲得了第二名的成績,之后又參與了多部邵氏電影的作曲。
在上個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多數(shù)粵語歌都是作為電影插曲而存在。1974年,顧嘉輝為電視劇《啼笑因緣》《鬼馬雙星》譜寫制作主題曲,這些作品成為了“香港粵語流行歌曲”的發(fā)端。顧嘉輝等人創(chuàng)作的兼具嚴(yán)肅性和藝術(shù)性的粵語歌使得粵語歌逐漸成為樂壇的主流,原本只愿意演唱英文歌的歌手也開始演唱粵語歌,粵語歌不僅風(fēng)靡香港樂壇,也走紅到了中國臺灣地區(qū)和中國內(nèi)地。
馮天瑜
歷史學(xué)家、武漢大學(xué)人文社科資深教授
1942年2月8日-2023年1月12日

左手吊瓶,右手握筆,馮天瑜在湖北省人民醫(yī)院的病房中寫完了《中華文明五千年》一書,該書在2022年年初出版。武漢大學(xué)國學(xué)院院長郭齊勇回憶說,“馮先生是一位奇人,豁達(dá)開朗,積極樂觀。醫(yī)生多次宣判他生命的期限,可他就是不予理睬,似乎無暇消沉悲戚,抓緊分分秒秒,專心專意思考理論、歷史的問題,一門心思寫書。”
馮天瑜曾說自己“30多歲才初入學(xué)術(shù)門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極少探討文化和文明的問題。1979年,37歲的他來到武漢師范學(xué)院(湖北大學(xué)前身)任教,原本學(xué)生物的他轉(zhuǎn)向歷史,開始了文化史的研究。他不僅關(guān)注整體文化史,還聚焦于中國文化史歷程中的兩個重要時段,一是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先秦),一是中國文化的近代轉(zhuǎn)型期(明清)。馮天瑜還定義了“中華元典”及螺旋式上升的“文化重演律”。他分析哪些典籍屬于元典,又是如何生產(chǎn)的,告訴讀者中國元典與古希臘元典、希伯來元典和印度元典的同中之異及異中之同,由此透視中國文化的特色,揭示轉(zhuǎn)換著的元典精神如何在中國近代化運動中發(fā)揮作用。
馮天瑜一家生活簡樸,但他父親非常喜歡購買書籍和古董,為的是它們的藝術(shù)魅力和史料價值。1979年初,馮家開始向武漢師院剛復(fù)建的歷史系捐贈古幣。到2018年,馮家兩代學(xué)人將長達(dá)半個世紀(jì)間收藏的珍品都捐獻(xiàn)了出來。因為數(shù)量非常多,武漢大學(xué)專門設(shè)立了“馮氏捐藏館”,有人問這些家藏到底值多少錢,馮天瑜說他沒研究過。
郭宏安
法語文學(xué)專家、翻譯家
1943年2月2日-2023年1月16日

“斯丹達(dá)爾認(rèn)為一個人不能有過多的錢財,也不能沒有錢,過少要仰人鼻息,過多有其他的煩惱,錢剛好能看書、談戀愛和看歌劇就夠了。我和斯丹達(dá)爾的想法一樣,幸福生活對于我來說就是能看書和寫作足矣。”郭宏安曾這樣談及代表譯作《紅與黑》作者想要傳達(dá)的主題。
高中時,他接觸到《紅與黑》《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臺》,這三本書直接影響了他對職業(yè)的選擇,使他走上了研究、評論和翻譯法國文學(xué)的道路。1961年,郭宏安考入北京大學(xué)西方語言文學(xué)系,選擇法國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大二時,他借助字典一點點啃完《紅與黑》的原著。1993年,郭宏安重譯后出版《紅與黑》,翻譯僅用了5個月。“也許在別人看來譯得太快了,可是人們并不知道,我心里已經(jīng)把《紅與黑》翻了30年。”
20世紀(jì)80年代起,他持續(xù)關(guān)注加繆和波德萊爾的作品,開展研究和翻譯工作。從《加繆中短篇小說集》到《加繆文集》,從《波德萊爾美學(xué)論文選》到《波德萊爾作品集》,對兩位作家的系列研究是他認(rèn)為自己在法國文學(xué)翻譯領(lǐng)域內(nèi)兩項較大、較完整的成果。1992年,波德萊爾的作品《惡之花》經(jīng)郭宏安翻譯后出版,該譯本開創(chuàng)了文學(xué)名著插圖本的先河。2012年,他因《加繆文集》獲得“傅雷翻譯出版獎”。
楊苡
翻譯家
1919年9月12日-2023年1月27日

老有記者采訪,拿“貴族”身世說事兒,楊苡覺得有點兒煩。楊苡出生于書香世家,祖輩有四位在晚清時考入翰林,父親楊毓璋是中國銀行的天津分行行長,哥哥楊憲益同為著名翻譯家,姐姐楊敏如是古典文學(xué)研究者。她也是巴金的筆友和朋友,兩人有著長達(dá)六十余年的友誼和橫跨半個世紀(jì)的書信往來(兩人的書簡收錄于《雪泥集》)。少女時期,她與巴金通信時說想做《家》里的覺慧,巴金不贊成,認(rèn)為應(yīng)該先把書念好,要有耐心。
楊苡在重慶借讀時偶然讀到《呼嘯山莊》原著,覺得“里面的愛情可以超越階級、社會和生死,比《簡·愛》要好”,萌發(fā)了翻譯此書的念頭,巴金也鼓勵楊苡,認(rèn)為楊的譯筆絕對不會差。《呼嘯山莊》曾經(jīng)被梁實秋翻譯為《咆哮山莊》,楊苡并不滿意這版翻譯,一日夜里風(fēng)雨交加,她從雨聲中得到靈感,最后將書名Wuthering Heights定為《呼嘯山莊》,成為了公認(rèn)的佳譯。
萬瑪才旦
作家、導(dǎo)演、編劇
1969年12月3日-2023年5月8日

藏人并不像人們想象中那樣生活在神話里。他們一直都那樣真實地生活,許多文學(xué)作品像是《尊者米拉日巴傳》等對此早已有深入描寫,只不過讀者們——尤其是漢語世界的讀者——不了解罷了。萬瑪才旦曾經(jīng)這樣闡釋自己創(chuàng)作的的關(guān)鍵詞“藏地”。
萬瑪才旦生前的作品包括《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氣球》,他還著有小說集《烏金的牙齒》與《故事只講了一半》。他最初想要當(dāng)一個作家,剛開始拍攝電影時,萬瑪才旦并未意識到一些小說可以變成電影。在作者的影視意識覺醒之后,電影與文學(xué)才開始結(jié)合。萬瑪才旦提到,自己與扎西達(dá)娃和馬原的藏地寫作不同,他的藏地更為日常與世俗:“你通過我的文字或影像,你會覺得作為人,本質(zhì)上和你們也沒有多大區(qū)別。我可能更了解他們作為人的最細(xì)微的情感方式。”
孫機
文物專家、考古學(xué)家、中國國家博物館終身研究員
1929年9月28日-2023年6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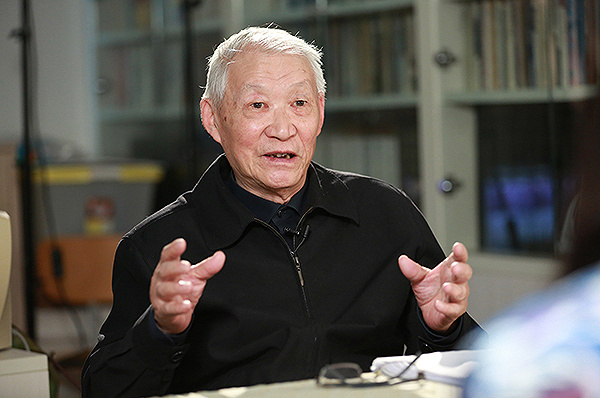
孫機曾經(jīng)這樣調(diào)侃鑒寶現(xiàn)狀:第一句“真的”,第二句“兩百萬”,現(xiàn)在很多文物研究者鑒定文物時往往只有這兩句話,一般民眾也并不在意文物的真究竟真在哪里。他認(rèn)為,做文物研究,一定要在一個廣闊的時空之下,從文物背后的思想狀況出發(fā)。某次一位記者去拜訪孫機,孫機說起喜歡吃饅頭和米粥,接著講起了饅頭的歷史——15世紀(jì)的歐洲還不會做發(fā)面的面食,然而漢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饅頭,名為“起面餅”。
孫機的考古研究事業(yè)始于結(jié)識沈從文。新中國成立之初,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工作,孫機跟隨他學(xué)習(xí)中國古代服飾史,幫助整理中國古代銅鏡的資料,自此打開了考古這扇大門。之后他考入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yè),師從中國考古學(xué)泰斗宿白。宿白告訴孫機,考古研究要多讀書,還要注意史料中的“觸角”,這些觸角會互相聯(lián)系起來,成為學(xué)術(shù)研究的入口。孫機后來著有《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中國古輿服論叢》《仰觀集》等作品,所有作品中他最喜歡的是《仰觀集》——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一件青銅和一縷絲線也可折射出人的審美和創(chuàng)造。
李強
社會學(xué)家,清華大學(xué)文科資深教授
1950年-2023年12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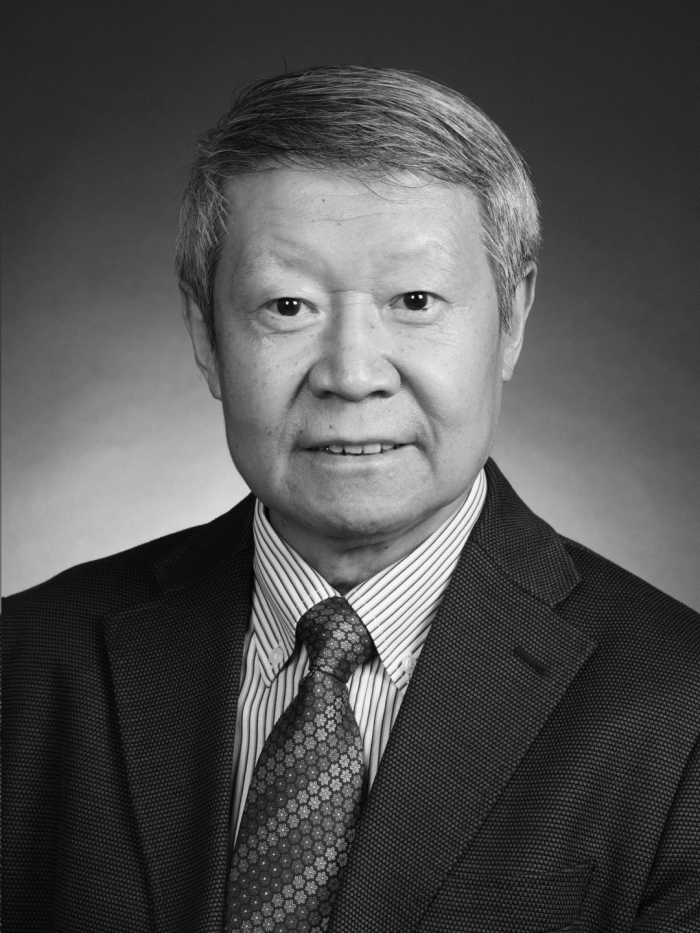
李強曾說,“我的社會學(xué)基礎(chǔ)大體上是自己讀書讀出來的。”1978年他考進(jìn)中國人民大學(xué)時,學(xué)校還沒有社會學(xué)專業(yè),也沒有社會學(xué)的概念。一天,他在外文圖書展上發(fā)現(xiàn)有歸類為Sociology(社會學(xué))的書,感到很有趣,此后走向社會學(xué)研究道路。
1987年中國人民大學(xué)正式建立社會學(xué)系,李強是系副主任,之后他又進(jìn)入清華大學(xué),擔(dān)任過清華人文社會科學(xué)學(xué)院院長。他也是社會分層與流動、城鎮(zhèn)化與城市研究、社會治理等研究領(lǐng)域的領(lǐng)軍人。根據(jù)清華大學(xué)的訃告,21世紀(jì)初,在結(jié)合數(shù)據(jù)分析和客觀全面經(jīng)驗觀察的基礎(chǔ)上,李強提出了中國社會“倒丁字型”結(jié)構(gòu),之后根據(jù)社會結(jié)構(gòu)變化實際又提出“土字型”社會結(jié)構(gòu),為中國社會分層研究打下理論基礎(chǔ)。
余友涵
當(dāng)代藝術(shù)家
1943年-2023年12月13日

小學(xué)美術(shù)老師告訴他:“音樂家一曲表演下來,全場鼓掌,還會有姑娘獻(xiàn)花。畫家不會有這樣的光輝時刻。”余友涵曾在《自問自答錄》中寫道:“我記住了,我不喜歡這種時刻,我喜歡默默無聞。”喜歡默默無聞的余友涵后來在1993年參加了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也是中國藝術(shù)家首次登上威尼斯雙年展舞臺。余友涵回憶,在當(dāng)時的圣馬可廣場,“只有兩個人穿著西裝,一個是意大利總統(tǒng),還有一個就是我。”
余友涵之所以得到世界關(guān)注,一大原因在于他是20世紀(jì)90年代的政治波普藝術(shù)領(lǐng)域最具代表性的藝術(shù)家之一。他在80年代接觸抽象與極限藝術(shù),在1989年以其抽象“圓”系列參加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大展。到90年代,余友涵在挪用政治宣傳圖像的中國波普風(fēng)格作品中大膽嘗試,綴以花朵且滿溢色彩的畫面,為“藝術(shù)為政治服務(wù)”與“藝術(shù)為取悅大眾”信條帶來全新演繹。如果考慮到所有作品,事實上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多元而豐富,不局限于政治波普風(fēng)格。
江平
中國政法大學(xué)原校長、終身教授
1930年12月-2023年12月19日

改革開放時,江平已經(jīng)快要五十歲了。在政治運動中長期不被允許從事法律、法學(xué)工作的他,直到彼時才重新燃起了對這項工作的熱愛。他曾說,“對私法情有獨鐘,理由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私法在中國社會中始終未有植根。因為中國社會缺少私法植根的土壤和條件,中國缺少一個‘市民社會’。”
從著作《我所能做的是吶喊》到《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江平的人生經(jīng)歷與法治觀念不僅影響著法律學(xué)人,更是超出法學(xué)的范圍影響著整個社會對于法治的理解和認(rèn)同。江平一直關(guān)注中國法治建設(shè)進(jìn)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為會議主題,提出進(jìn)一步深化改革部署、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后,他倍感振奮,不顧年老體衰,為建設(shè)法治社會奔走呼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