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終身教授江平今日中午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逝世,享年94歲,九天之后即是他的95歲生日。
從《我所能做的是吶喊》到《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江平的人生經歷與法治觀念不僅影響著法律學人,更是超出法學的范圍影響著整個社會對于法治的理解和認同。

文集《依然謹慎的樂觀》出版于2016年,收錄了江平關于推進司法改革、建構法治政府、法治社會與法治經濟等重大問題的文章和采訪。江平一直關注中國法治建設進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為會議主題,提出進一步深化改革部署、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后,他倍感振奮,不顧年老體衰,為建設法治社會奔走呼號。下面這篇問答摘自本書,以表哀思。
記者:您是法學界的老前輩,是中國法治建設的推動者、見證者,您認為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點關注哪些問題?
江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三個概念當然不完全一樣。法治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內容就是如何實現市場管理的法治化。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很大的一個層面就是市場經濟如何法治化。如果講到法治政府,那當然很明顯了,就是講公權力怎么來實現法治化,政府的權力不能過大。如果涉及法治國家,或者是依法治國的概念,那么我理解這包含立法、司法、行政在內,這是我們將來一個大的法治國家的概念。這三個層次不太一樣。法治實際上就是怎么樣來貫徹治理國家的現代化的模式,就是把我們過去的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等提升到治理國家的現代化。我覺得今后法治中國建設應當偏重在公權力方面,更多還是公權力運作方面如何能夠實現現代化。這會涉及一些社會治理的問題,但是好像更多還是偏重在公權力的運作,可能這個是主要的。
記者:雖然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法律數量比較多了,但不可否認的是,法律內部矛盾、沖突等不統一現象以及法律操作性不強等立法質量不高的問題還比較普遍。比如說,《土地管理法》規定,收回閑置土地應當由縣級政府做決定,然而有關規章又規定土地行政部門也可以做決定。實踐中,有些地方是市政府做決定,有的是國土部門做決定。一旦發生糾紛,上級行政部門的行政復議維持地方國土部門的決定,但訴訟到法院,一般認為國土部門無權做此決定。再比如,目前正在推動不動產統一登記立法,《不動產統一登記條例》也即將出臺,但這樣一部條例的出臺會牽涉很多法律法規的修改,相應的立法任務非常繁重。可以說目前的立法體制似乎不能適應法治現代化的基本需求,對此您怎么看待?
江平: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從立法階段來看,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以修改為主的階段,所以最近都在關注各個已經通過的法律如何進一步完善。但是在立法完善的過程中,扯皮現象太嚴重。
拿《土地管理法》來說,《物權法》通過以后,《土地管理法》就要修改,現在《物權法》已經通過7年了(指采訪時),但《土地管理法》的修改還是沒有動靜。剛才講的不動產登記,《物權法》就明確規定了相應制度,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實行。我覺得這反映出全國人大權威性不夠的問題。立法本來是全國人大的事,修改法律的時候雖然要征求各個部門的意見,部門有不同意見要考慮,但是最后做決定是在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如果說該往這個方向修改,那就定了,全國都得服從,不能夠再按部門的意志,一個部門一個意見,不同部門之間扯皮。即使扯皮,到最后總得有一個拍板的人。立法必須要有權威性,應該由立法機關做決策。總的來說,立法機關不能處于弱勢,沒有權威性,總是處于扯皮狀態就比較麻煩。
第二個原因,我們現在立法缺乏一個總體的思考。比如,拿我們熟悉的民事立法來說,民法典要不要搞?現在到底往下怎么搞?都不知道。聽說現在在修改《繼承法》,同樣存在沒人拍板的問題。這完全是人大立法,跟其他部門沒有任何關系,頂多由最高法院來配合。可是這個法究竟怎么搞,《人格權法》怎么搞?《民法總則》制定不制定?《民法通則》要不要變成《民法總則》?這些東西都沒人管。現在的立法多少有一點“走一步看一步”。另外就是急的法先立,很被動,缺少一個統籌安排,我覺得這是個大事情。這兩個問題恐怕是現在立法領域存在的很重要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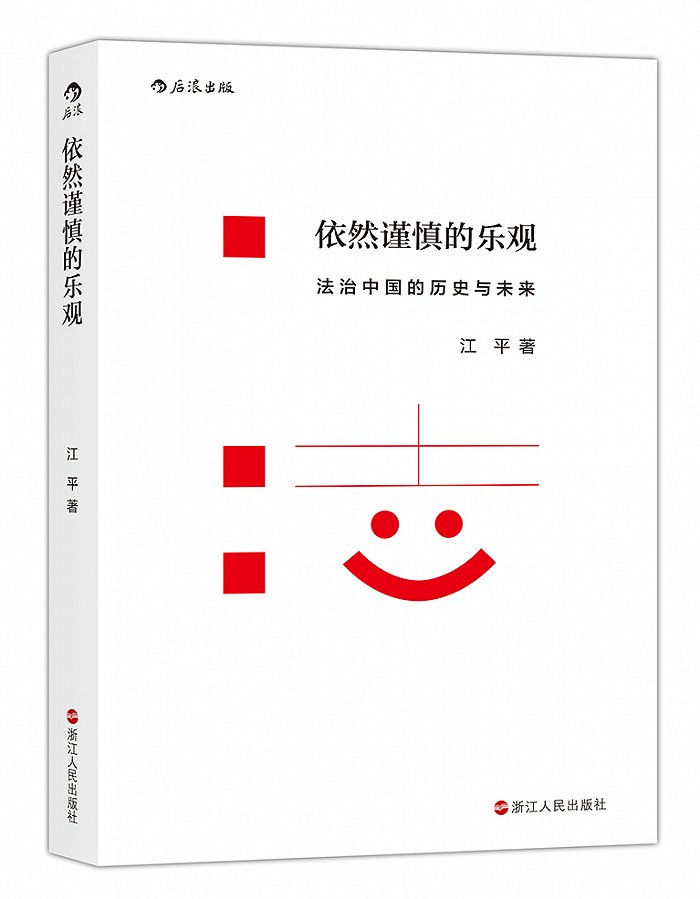
江平 著
后浪出版公司·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04
記者:在行政方面,法治的重點是什么?
江平:行政方面我覺得就是一句話: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這是最核心的目標。因為現在看起來,公權力還是太大了。公權力侵犯私權利的現象還是相當普遍的。如何把公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面,這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而且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面,不僅是法治政府的迫切需要,也是廉潔政府的前提。只有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面,權力受到制約,才能夠解決腐敗的問題。腐敗的根源就在于權力被濫用了。現在提出來各級政府要制定權力清單,明確你享有哪些權力,就明確了哪些是你不應該享有的。這實際上也就是李克強總理說的:法無禁止即自由,法無授權皆禁止。對于私權利,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自由的;對于公權力來說,法沒有授權的都是禁止的。因此政府的權力必須要有授權,有法律授權才能合法,法律沒有授權就是違法,就是越權了。但是這個問題落實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公權力一旦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掌權人都希望權力越大越好,誰希望管得那么嚴啊,這是人的本能。
當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領導在做《行政許可法》的報告時說,市場主體自己能解決的盡量自己解決,市場主體不能解決的由社會自治團體去解決,只有市場和社會不能解決的政府才來干預。但是現在看來,政府審批的事項仍然是一大堆,每個部門都希望有權力,都希望蓋自己的章才能通過。所以,應該說習慣勢力太大,或者說中國幾千年來就是這樣一個對公權力缺乏約束、限制的社會。現在要限制公權力是非常困難的,而要真正限制、約束公權力,還要從立法來著手。立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除了極個別完全由上級政府授權給下級政府的情況,一般來說是法律授權,只有法律授權政府,政府才有這個權力。如果法律不健全,就談不上政府權力的合法性。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面首先應從立法著手。

記者:黨的十八大以后,反腐敗工作明顯提速,而且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贏得了民心。但是,目前也出現了一種現象,即干部隊伍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觀望、不作為現象。一些官員認為,反腐敗會影響經濟發展。對此,您是怎么看待的?
江平:有人說腐敗是市場的潤滑劑,這種觀點我是不認可的。但是實際上往往也有這樣的情況,就是越是市場改革的能人,最后被揭露出的腐敗現象越多;越是老好人,他倒沒什么罪,成績突出的往往容易被抓起來。怎么能夠在反腐敗中區分個人責任和領導決策責任,把不同的責任分開?我覺得最重要的仍然是在法制上進一步制定明確的規則。怎么能夠追究你的責任呢?證據確鑿了,構成犯罪了,取得證據的手段不違法,查處就沒有問題了。
就怕兩種情況,一種是刑訊逼供,這個從重慶“打黑”案看得很清楚,利用刑訊逼供來做反腐的事情不是個例。另一種就是現在經常發生的,當證據不足的時候先把人抓起來。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危險的。在證據不足的時候把人抓起來,然后借助他的電腦里面的資料,或者借助其他人的舉報,或者用其他的一些東西來定他的罪名,我認為這種情況也是違法的。雖然最后可能查出一些問題,但是當時抓人的時候是缺乏證據的。所以我覺得反腐敗必須手段正確。
(本文節選自《依然謹慎的樂觀》,較原文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