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這句話最近在網上廣為流行,并延伸出了“人生是曠野,曠工、曠課”的句式。就像界面文化聊天室欄目曾提到的,社交網絡上常見舉著《Chiikawa》玩偶在飛機上或自然風光中拍照并引用“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表現虛擬人物輕松擁有而我們無法實現的生活。
這句話的出處尚有爭議,然而不少年輕人紛紛表示從中獲得了療愈——曠野指向自然的啟示和多樣的選擇,軌道則是直行向前、非如此不可的路徑。可是,曠野究竟怎樣療愈人心的,軌道距離人生的真相又有多遠?

曠野摧毀了生活的雞零狗碎
身處曠野,我們會更懂得享受寧靜嗎?在《12只鳥兒,治愈你》一書里,經歷喪母之痛的英國自由撰稿人查理·科貝特講述,他想要以自然自我療愈,可是靜坐于自然之中、聆聽萬物生長,聽起來容易,實現起來卻困難重重,因為人們總是想要逃離無聲的時刻。獨處時他才發現自己的思緒令人氣餒、有些恐怖,而且一點也不平靜。當他丟掉手機,與周圍的土地建立聯系,才逐漸復蘇,以一種內在的心態體會自然——秋天的特點是內在的平靜,萬物從盛夏和假日帶來的巨大壓力中恢復日常的模樣;自然伴隨著一種幸福的嘆息慢慢衰落至冬季,然而在暴風雪來臨之前,每個人包括大自然本身都能喘口氣。
對于曠野的感受來自于對“喘口氣”的心領神會。當科貝特習慣了出門,到花園中或者散步,從獲得基本的新鮮空氣與進行鍛煉,到最后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樂趣。個人不再是一個獨處的個體,而是多樣的宇宙中的物種之一,“你不再是你自己情景悲劇中的主角,而是大自然偉大史詩中的一小部分。”夏天聽到金翅雀的歌聲會令人忘記憤怒和緊張,秋季雁群的遷徙景象壯觀而讓人心跳加快。他逐漸學會辨識鳥兒的鳴唱,就像認識左鄰右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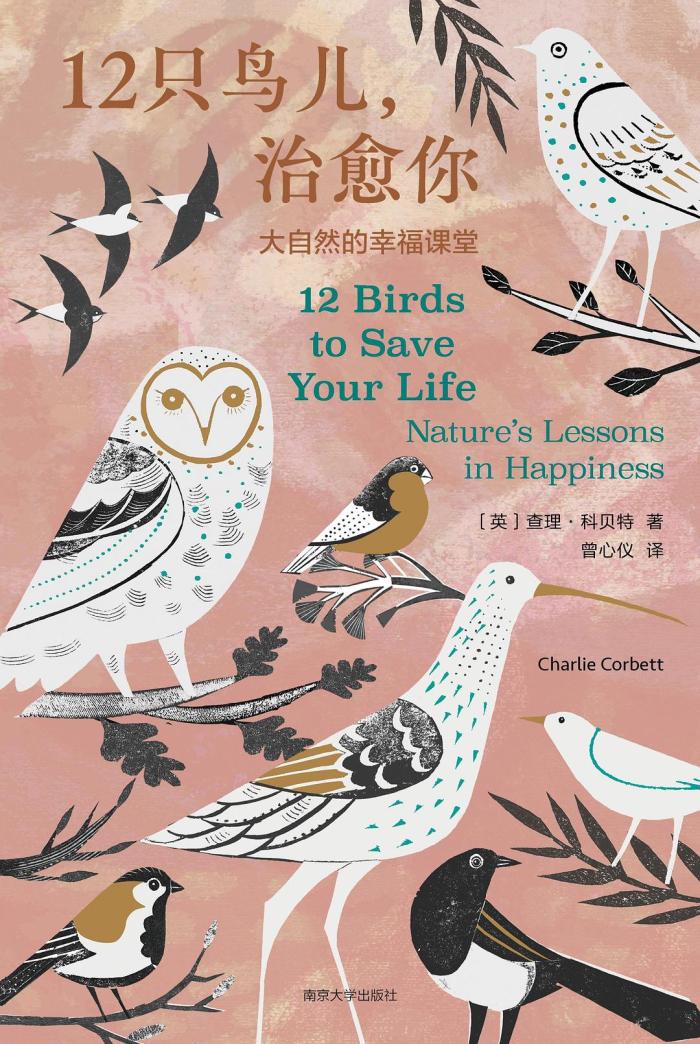
英]查理·科貝特 著 曾心儀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3-10
英國作家海倫·麥克唐納在觀察雨燕時有著類似的體會。雨燕會結群飛升至八千英尺的高空,在上升過程中收集空氣溫度、風速及風向的消息,“它們所做的就是飛到如此高的天上,準確地把握自己的位置,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動。”在這一點上,人們可以從雨燕的生活中獲得提示。普通的生活是瑣碎的,希望與憂慮、成本與收益、計劃和干擾此消彼長,人們需要自己親手建造的防御工事像是書籍、小狗、手工藝來度過漫長的一生,但也不能只活在這些東西當中,因為那樣就無法確定自己該往何處去。雨燕并不總是在飛越,大部分時間它們生活在邊界層以下的空氣中,進食、交配、洗澡與飲水,可是如果想要了解那些更重要的力量,就必須飛越去邊界層,與同伴交換信息。
這兩則故事都證明了,見識過曠野的人會明白,自然不僅是微風拂面、使人感受愉悅的,而有著自身的欲求、情感與生機。這似乎在提醒我們,那些讓我們保持忙碌的建筑工事、留戀不已的情感關系和一帆風順的生活理想,都是如此地相對與有限。人們應當從荒野的荒蕪和猛烈中煥發出熱情,如梭羅所言:
“沉郁哀怨的疾風暴雨何以讓我覺得悅耳動聽?我想,是它摧毀了我們一帆風順的生活所致的雞零狗碎。”
摧毀雞零狗碎——而不是撫慰日常與平庸——正是曠野的意義。這與玩偶愉快地曠工、曠課不太一致,也與同樣流行的“人生體驗論”大不相同。“人生體驗論”如此寬慰年輕人:“寶貝你只是來體驗生命的,什么都帶不走,就是來經歷有趣的事和難忘的人。”這樣的話語一方面確實緩解了生活的緊張情緒,另一方面卻用“有趣”和“體驗”將曠野替換為充滿粉色泡泡的游樂園,將自我自戀地想象為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的少年。

又寂寞,又焦慮
人們從曠野中讀出了情感的療愈與生活的啟示,但是也總有理由逃離寂靜,以忙碌和充實填充自己。梭羅說,成年之后,人好像被派上了特殊而小氣的用場,窮其一生貫徹某種特定的部署,因為不遑四顧,以領會生活和生命的諸種事項。忙碌、用途和確定性似乎構成了一間看不見的牢獄,令人們安坐于室內。
當然也有人對此提出抗議,像是羅伯特·瓦爾澤的小說《唐納兄妹》中在社會上屢屢碰壁、徘徊于初級職位的年輕主角,就曾感慨道,“春天里的一棟銀行大樓是多么愚蠢!”大樓是在春天的映照下顯得愚蠢的,那么人們為何不從柜臺后面走出來,從抄寫文書的工作中自我解放?這位主角大概是踐行了人生是曠野、曠課、曠工的人,他的每一份工作都干不了幾天,甚至無法在一個地方長久地待下去,因為無法忍受環境和規矩的束縛。
人們為什么會日復一日地待在銀行大樓里呢?難道春天和曠野比大樓更令人感到恐懼嗎?比起輕率地說出曠工、曠課,也許人們更加害怕自我解放,或將之視為一種自我流放?所以才會讓自己的玩偶實現理想,自己仍舊待在格子間內,希望現在的努力是為了有一天能夠真正為自己而活。

可是這一目標并沒有那么容易實現。古羅馬斯多葛主義哲學家塞涅卡在《論生命之短暫》中早有論述,“為自己而活”如一種虛假甜蜜的幻想,督促著人們心甘情愿地勞碌。即使那些住在鄉間別墅、躺在沙發上享受安寧的人,也不知如何陪伴自己,他們經常為宴會、招待和享受陷于小心翼翼之中,這樣的生活只能算“無所事事”而不能算悠閑,仍是充滿焦慮而非安寧:
“無論富裕還是貧苦,人總會有不安的理由。生活就這樣,被一個又一個渴望推著向前走。我們永遠在渴望悠閑,卻又從未真正享受過悠閑。”
滾滾向前的軌道
軌道,總是與進步、滾滾向前、方向明確、單一進程等概念相關。今年熱播電視劇《漫長的季節》里范偉飾演的火車司機大聲地向觀眾喊話,“向前看,別回頭!”意思是過去的創痛已成定局,不如好好地把握現在,擁抱未來。長年行駛于同一條軌道之上,火車司機的職業經驗塑造了“向前看、別回頭”的智慧。
軌道向前,而人們生活的時間并非總是如此。博爾赫斯在訪談集中引用英國哲學家布拉德雷的觀點說,時間并非總是由現在流向未來,而是相反地,從未來流向我們,我們總是溯流而上,而未來正是轉變或溶解為過去的時刻。這個觀點令博爾赫斯受到啟發,亦緩解了他未來要經歷手術的恐懼,因為既然未來與過去的關系顛倒了,因果關系的鏈條也沒有人們自以為地那么明晰。
如果說博爾赫斯的這一譬喻過于神秘主義,我們也可以參考神經科學家奧利弗·薩克斯《意識的河流》中的觀點。薩克斯引用博爾赫斯對于時間的河流比喻,認為與其說是河流,不如說是一連串的珠子。生活的瞬間就像電影快照,是由生命的軌跡和主軸串聯起來的,不同時刻彼此串聯、互相融入的感覺讓時間變得連續。
他以患者的故事為證據,證明是意識讓生活有從過去流動到未來的感覺。很多患者在偏頭痛發作時暫時失去了視覺的連續感和動感,眼前看到的是閃爍的定格畫面,他將之稱為“電影視覺”,因為患者總是將看到的影像比作慢速播放的電影。在另外一些帕金森綜合征患者身上,他觀察到意識被切成碎片、解體為快照的情況,不僅如此,意識還可能會暫停,一次長達數小時。書中的一個例子是,某女士進浴室洗澡,浴室里的水漫成災,她也動彈不了,因為她在水深達2厘米時暫停了意識,“被困在那個永恒時刻之中。”如果生命連滾動的河流都不算,而僅是依靠感覺聯系起來的電影快照,那又怎么算得上是非要如此不可的軌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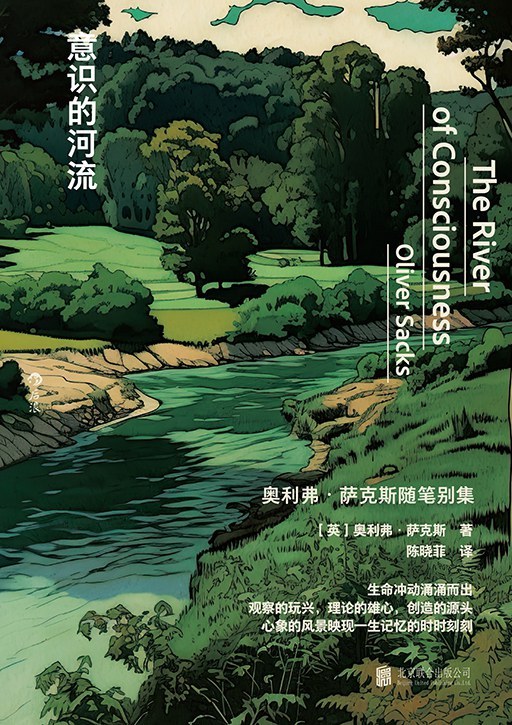
[英國] 奧利弗·薩克斯 著 陳曉菲 譯
后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3-7
即便如此,軌道和曠野就沒有折衷之道嗎?在寫給青年詩人的信中,詩人里爾克勸對方安于自己職業的軌道,安于單調枯燥與寂寞,因為所有的職業都差不多,“是不是一切職業都是這樣,向個人盡是無理的要求,盡是敵意,它同樣也飽受了許多低聲忍氣、不滿于那枯燥的職責的人們的憎惡。”青年現在需要應付的職業,不見得比別的職業被習俗、偏見和謬誤連累得厲害,因此他需要做到的就是以渺小、沒有光彩的事物開始,“好好地忍耐,不要沮喪。”如果實在覺得失落,就去投身于曠野,“還有夜、還有風——那吹過樹林、掠過田野的風,在物中間和動物那里,一切都充滿了可以分擔的事。”我們從各自軌道的寂寞中擴展出遼遠和廣闊,這或許指出了一線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