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朝不保夕者”(the precariat)的故事要從新自由主義的起始講起。20世紀70年代末,一群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發現,他們的學說在被凱恩斯主義支配了幾十年后,終于有了被政界重視的苗頭:他們反感國家干預,將國家等同于由計劃和管制機構組成的中央集權政府,主張建立“勞動力市場的彈性機制”,將風險轉嫁給勞動者,讓企業得以提高效率和國際競爭力。這些學者后來被稱為“新自由主義者”和“自由至上主義者”;他們的學說,即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也自那時起重構了全球資本主義。傳統工人階級在上世紀中葉爭取而來的穩定就業和社會福利被不斷侵蝕,勞動者的工時、薪資、工作地點甚至工作內容都可以被輕易改變。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注意到,在上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植入全球市場經濟的弊端就已經顯現無疑——收入、財富和權力向擁有財產的少數人集聚,形成“食利者資本主義”,而在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加劇、勞動力市場進一步去管制化的時候,普通大眾之中開始形成了“朝不保夕者”。斯坦丁將形容詞“不穩定的”(precarious)和名詞“無產階級”(proletariat)結合,形成了“朝不保夕者”的概念。
朝不保夕者不等同于“窮忙族”或工作不穩定的人,他們是缺乏七種勞動安全的群體:勞動力市場安全、雇傭安全、崗位安全、工作安全、技能再生產的安全、收入安全、代表性安全。
2008年金融危機后,大多數發達國家政府推行緊縮政策,加劇了朝不保夕者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狀況。2011年,斯坦丁出版了《朝不保夕的人》(The Precariat)一書。從出版至今,此書已成為了考察新自由主義時期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必讀書。今年,《朝不保夕的人》中譯本面世。
在這12年間,全球朝不保夕者的境遇日益嚴峻。2021年,斯坦丁在第四版序言中寫道,“據粗略估計,2011年,在很多國家,大約1/4成年人的生存狀況岌岌可危。2020年,新冠疫情前夕,這個比例可能已經接近1/2,朝不保夕者特別集中在年輕人當中。”斯坦丁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訪時表示,新冠疫情讓全球的朝不保夕者遭受了又一次沉重打擊。


無論是在書中還是在接受界面文化的采訪中,斯坦丁都流露出了對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強烈憤慨,對全球朝不保夕者(特別是其中占多數的年輕人)的深切同情和對政治現狀的憂慮。他說,
我們面臨的許多危機相互關聯,最糟糕的一點也許是,太多擁有權力或影響力的人并不打算認真對待、采取行動。我認為,領導者告訴社會和經濟沖擊的受害者更加努力工作或變得更堅強會適得其反,因為受害者能夠看到和聽說億萬富翁們過著多么驚人的奢侈生活。
近年來,斯坦丁把思考和工作的重心放在以“朝不保夕者”的概念為基礎,提出變革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種種方案,比如推廣全民基本收入。作為“基本收入地球網絡”聯合創始人、現任名譽聯合主席,他告訴界面文化,在所有進行了基本收入實驗的國家或地區,結果都相當一致——擁有基本收入的人心理和身體健康都得到了改善,學習能力增強,工作也更勤奮,社會態度變得更好。
誠然,朝不保夕者作為一個仍在形成中的階級仍然面臨種種問題,特別是不斷的內斗令許多朝不保夕者成為了制造仇恨和痛苦的政治的狂熱支持者——“在朝不保夕群體的內部,一個群體可能會將自己的弱勢和受到的侮辱歸咎于另一個群體。”但我們依然要對變革的出現心懷希望,斯坦丁說,“設想一個‘沒有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是至關重要的。”
01 新冠疫情和相關應對措施使全球朝不保夕群體擴大
界面文化:是什么啟發了你寫作《朝不保夕的人》?
蓋伊·斯坦丁:在1990年代,顯而易見的是我們正處于“全球性變革”(Global Transformation)之中,新自由主義經濟革命與全球市場經濟的痛苦建設同步發生,帶來了更大的不平等和新的長期經濟不確定性。但與芝加哥等地的新自由主義所聲稱他們期望的情況相反,發生的卻是史上最不自由的市場經濟,即我所謂的“食利者資本主義”(rentier capitalism)。
這意味著新的全球階級結構正在形成,越來越多的收入、財富和權力流向了那些擁有財產的人,不論是實物財產、金融資產還是知識產權。
我堅信,新自由主義經濟和食利者資本主義意味著社會和經濟不安全性的擴散,新的大眾階層,即“朝不保夕者”,具備三個維度的特征:不安全的勞動和工作、不穩定和不確定的收入,以及在國家中喪失權利。
但我認為,朝不保夕者不僅僅由“受害者”構成。他們是新的危險階級,因為他們不會陷入錯誤的自我意識,認為“工作”是通向幸福的道路。受過教育的那部分人不會認同資本主義,也不會認同20世紀定義社會民主主義的舊式國家控制和國家家長式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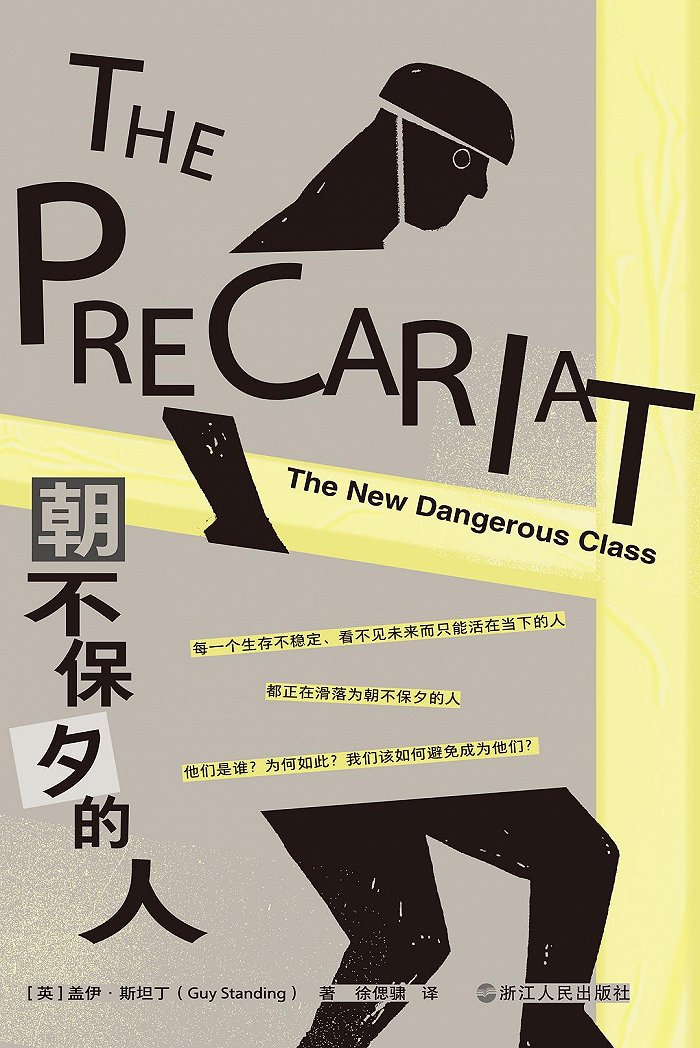
[英]蓋伊·斯坦丁 著 徐偲骕 譯
潮汐Tides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4
界面文化:作為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回應,《朝不保夕的人》首次出版于2011年,而在中國讀者首次讀到此書完整譯本的2023年,我們已經經歷了具有極大經濟破壞性的新冠疫情。在過去12年的時間里,全球朝不保夕者的境遇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大流行是否加劇了朝不保夕者的痛苦?
蓋伊·斯坦丁:新冠疫情是本世紀的第六次大流行,它典型地展現了全球轉型危機的主要特征。我們正處于不確定時代(Age of Uncertainty)。不確定性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不安全。在不確定性下,你無法預測不利沖擊的概率,也無法預測誰會受到影響,以及受到多大程度的影響,或者應對和從這些沖擊中復蘇的概率。
我認為很明顯,在全球范圍內,由于新冠疫情和許多政府的應對措施,朝不保夕者群體擴大了,后果之一是各種形式的債務進一步擴大。“生活成本危機”進一步惡化,價格上漲不僅與正在發生的戰爭有關,還與全球金融資本故意操縱價格以增加利潤有關。
更糟糕的是,我們還面臨著不斷加劇的環境危機和全球變暖。無產階級更依賴公地,但世界各地的公地正因私有化和耗竭而被剝奪。我在兩本書中詳細闡述了這個問題——《公地的剝奪》(Plunder of the Commons)和《藍色公地》(The Blue Comm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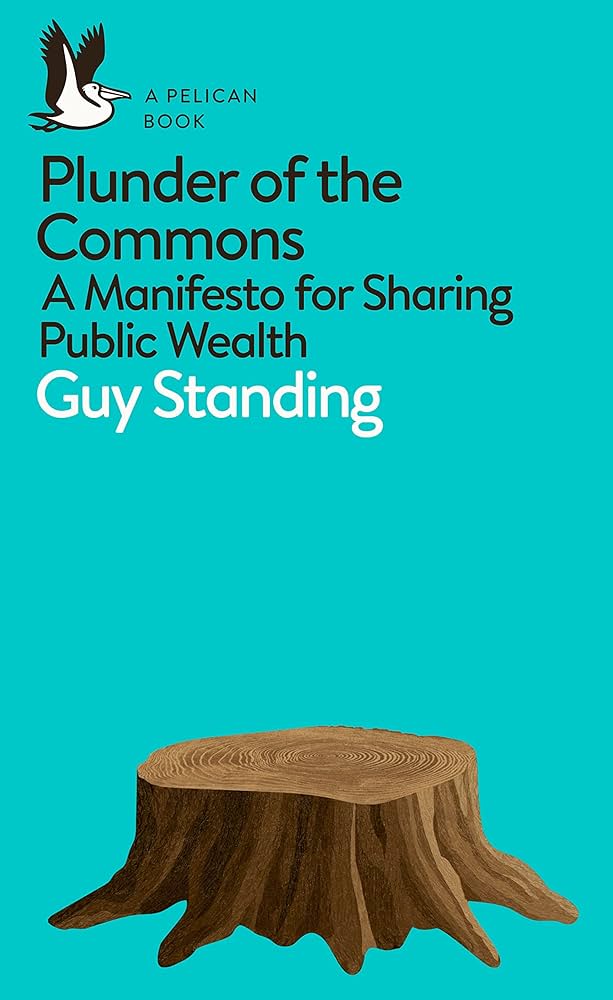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提到,2008年經濟危機中出現了“男性的大衰退”(mancession)。而一些觀察者,包括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發現新冠疫情造成了“女性的大衰退”(she-cession)——很多服務業的女性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間失去了工作,而且和男性相比,她們更難返回工作崗位。你能否談談“男性的大衰退”和“女性的大衰退”之間是否存在轉折關系,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全球勞動力版圖的變化?
蓋伊·斯坦丁:我認為疫情以及后疫情時期的勞動力市場發展不應該以性別為解釋框架。很明顯,個人服務業受到了重創,而這正是女性主要集中的領域。我在較早的統計學工作中展示過——早在克勞迪婭·戈爾丁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呈現出U型曲線。早期工業時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非常高,而后出現下降(部分是因為統計原因),然后又一直在上升。
我1989年和1999年在《發展與變革》(Development and Change)雜志發表了兩篇關于“靈活勞動中的全球女性化”的文章。文章顯示,從更長期的角度來看,女性的就業率相對較快地上升,失業率相對于男性下降,部分原因是男性的情況在惡化。我認為僅僅比較全職工作的工資或者就業率是不正確的。
正如我在新書中所論述的,傳統的勞動力市場趨勢評估中最大的問題之一,特別是在評估女性工作和勞動力方面,是女性做了大量未計入國內生產總值(GDP)或經濟增長的勞動。她們還越來越多地從事“遠程勞動”和“云勞動”,這兩者都被嚴重低估。

界面文化:近年來,關于勞動者、工作和階層的話題常在公共輿論中被討論。超長的工作時間、狗屁工作(借用大衛·格雷伯的術語)和女性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劣勢都是爭論的話題,你在《朝不保夕的人》中也討論了這些話題。這是否意味著,全球社會經濟系統正在面臨總體性危機,或早或晚,所有人都將面對其沖擊?
蓋伊·斯坦丁:我們面臨的許多危機相互關聯,最糟糕的一點也許是,太多擁有權力或影響力的人并不打算認真對待、采取行動。我認為,領導者告訴社會和經濟沖擊的受害者更加努力工作或變得更堅強會適得其反,因為受害者能夠看到和聽說億萬富翁們過著多么驚人的奢侈生活。
02 真正的教育,是一種公共利益
界面文化:為什么青年很容易滑入朝不保夕者的行列?
蓋伊·斯坦丁:全球各國的朝不保夕者群體中,年輕人占絕大多數,而且年輕人的失業率要高得多。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中,人們常常因事業或經濟不安全而受到責備,被稱為“不具競爭力”、“懶惰”或更糟。這種看法是非常錯誤且不公平的。
如今的現實是,舊有的社會保護模式已經不可挽回地瓦解。朝不保夕群體中的人,特別是當他們經歷失業時,會陷入越來越深的無法維持的債務中。所有這一切都與不斷增長的健康問題有關,特別是心理健康問題,導致“絕望之死”。

界面文化:當體面的工作機會越來越稀少,年輕人花更多時間追求研究生及以上學歷,進一步加劇了“學歷膨脹”這一長期問題。你能否再展開談談你在書中提出的一個觀點:為現有的工作機會接受“過度教育”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該把學位從一種投資品變為一種“休閑品”。我會問這個問題,因為同樣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觀點認為,隨著傳統意義上的中產工作正在大規模被自動化,除了接受更多教育,為更精細復雜的工作做好技能準備之外,我們沒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選擇。
蓋伊·斯坦丁:首先,讓我們非常明確地說,教育,我是說真正的教育,是一種公共利益,說某人“受過度教育”實際上是一個矛盾之詞。如果一個人擁有一件事物并不會剝奪另一個人擁有它的機會,那件事物就被視為公共利益。現代新自由主義的悲劇在于,教育已經被濫用為一種私人利益,學位、文憑和其他證書僅僅是根據它們是否提高了一個人的“人力資本”來評判。
教育不應該只關乎工作或賺更多的錢。它關乎尋求真理、美、理解自身,理解我們的社會和文化,關乎我們與自然和人類的關系。
朝不保夕者是歷史上第一個平均學歷水平超過現有工作所需水平的大眾階級。危險在于,這可能會導致一些政策制定者和評論員提出削減教育經費。一個更文明的方法是為教育本身而重振教育。
界面文化:因意識到大學畢業生過剩且他們并不必然符合雇主對人才的要求,中國正在嘗試改革其教育體系,將更多注意力放在職業教育上。在這一方面,德國其實一直是我們學習的目標。因此,我在讀到你提出德國學徒制度正在消亡時感到有些驚訝。能請你再談談德國的案例嗎?在你看來,職業教育是提高年輕人職業競爭力的出路么?
蓋伊·斯坦丁:教育家們有點像軍事將領,他們總是擅長應對上一場戰斗。試圖將教育轉向“職業”學校和培訓,是在應對基于制造業的舊經濟。德國發展學徒制度,是在德國還是嶄露頭角的制造業大國之時,那時有眾多的小型和中型企業。在那個年代,學徒制度的理念是有道理的。年輕人——遺憾的是,主要是年輕男性——可以進入工作現場進行為期數年的培訓,預期將在接下來的二十年或更長時間內從事某一職業。
但這種模式在現代以服務為導向的經濟中不起作用,特別是在技術變革迅速、極具顛覆性和不可預測性的情況下。朝不保夕者很少能夠預測他們下個月或明年將從事什么職業,更不用說在接下來的十年或二十年內了。
界面文化:今年有一個現象吸引了很多注意力:年輕人放棄壓力很大、很精英的白領工作去做體力活。這不僅讓我們想到疫情期間美國出現的“大辭職”(Great Resignation),我們要如何理解如今年輕人的倦怠呢?
蓋伊·斯坦丁:這種現象是相當健康的,這是朝不保夕者對社會走向的一種靜默抗議。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反應,這反映了普遍拒絕“錯誤意識”的態度,即勞動和“工作”是幸福的根源。
毫無疑問,一個良好社會應該以時間的解放來標志進步。當然,工作和勞動是建立經濟基礎所必須的,但“內卷”現象必須被理解。那些不斷催促人們更加努力工作的政策制定者沒有意識到的是,太多的人感覺自己像西西弗斯一樣,不斷地推著巨石上山,只為期待它再次滾下來,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重復這個過程。我們必須采取一種解放時間的漸進策略,這正是我的新書《時間政治:在不確定時代獲取控制權》(The Politics of Time: Gaining Control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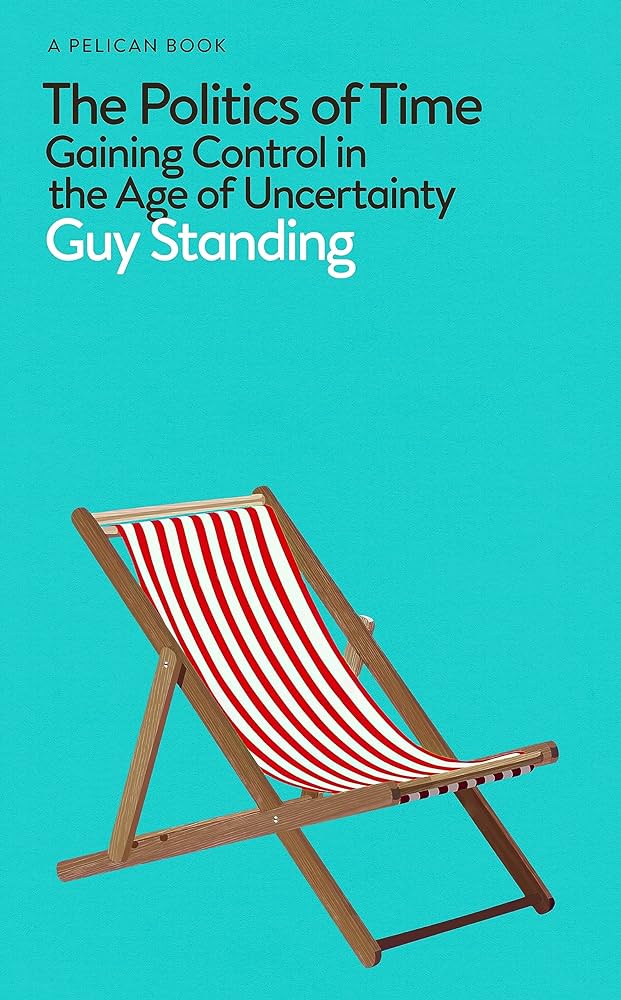
03 設想一個“沒有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至關重要
界面文化:我們如此徹底地生活在一個新自由主義的世界里,似乎很難想象一個沒有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是怎樣的。對我們當中那些希望改變現狀的人來說,我們到底想實現什么呢?是希望時光逆流,回到新自由主義不曾如此徹底決定全球經濟圖景的時代么?
蓋伊·斯坦丁:設想一個“沒有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需要重新構想未來,意識到我們正在朝著一種變革的生活方式前進,其中我們可以從事不是勞動的工作,實現“共有”(commoning),即在一種友好和社會團結的氛圍中進行共同生產和繁衍活動。我已經嘗試在我的新書的最后一章中描述這可能會是什么樣子。
界面文化:這兩年我們看到了英國和美國的多個行業都出現了工會和大規模勞工抗議復蘇的情況。這是一個樂觀的跡象嗎?
蓋伊·斯坦丁:這個“復蘇”是真實的,還是垂死之獸的最后掙扎?每一次歷史性的轉型都涉及到新的集體發聲方式和新的代理機構的出現,而不是重復過去。一百年前,工會曾是強大的進步力量,盡管它們從未具有顛覆性。它們想要的是為它們的“成員”爭取更多的經濟蛋糕份額。這沒有錯,但它們從未真正為無產階級或社會邊緣群體而戰,而且他們在環境保護方面表現得非常糟糕。面對工作和環境之間的選擇,它們總是選擇工作。

不要誤解我的觀點。我們需要有集體機構來代表我們的利益,國家需要尊重這一點,而不是壓制集體聲音。然而在21世紀,我們需要機構來代表公地,使我們中的更多人能夠花更多時間從事護理工作、社區工作、參與健康的政治活動、修復自然。工會需要進行轉型,我們需要一場聯合的革命。“聯合”這個詞可能會嚇到希望看到全景監控國家進一步加強的政府官員,但我們需要的是和平的漸進式變革。明智的領導者培育公地。
界面文化: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很重要?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有可能見到全民基本收入的實施嗎?
蓋伊·斯坦丁:如果你沒有提出這些問題,我會感到非常失望。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或真正的進步主義者,相信人類長期將邁向正義和解放,那么你肯定要努力建設一個人人都擁有基本經濟安全的社會。這是一項普遍的正義問題,是推動自由和將基本安全視為人權的問題。
我在書中以及我們的國際網絡“基本收入地球網絡”(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中提出了這一觀點,我們剛剛在首爾舉辦了第22屆國際大會。
我確信,為所有常住公民提供基本收入在任何國家都是可行的,這將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加強社會團結。我們一直在許多國家進行試點和實驗,包括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最近還包括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部分地區。
我可以向你保證,結果在非常不同的社會中都是一致的:擁有基本收入的人會體驗到心理健康的改善、長期身體健康的改善、更好的學習能力和更好的社會態度。與政治偏見相反,擁有基本收入的人工作更多,而不是更少,但他們更多是從事他們希望從事的工作,包括照顧他們所愛的人。這是常識!
界面文化:要解決朝不保夕者的問題,全球協作的行動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緣政治張力加強、紛爭不斷的時代。要改革現有經濟制度,我們要采取的第一步是什么?
蓋伊·斯坦丁:朝不保夕者仍然是一個正在形成的階級(class-in-the-making),因為它在內部存在分歧,分為我稱為“返祖派”(Atavists)的一派——他們傾向于聽從民粹主義甚至新法西斯主義的聲音,聽從像唐納德·特朗普這樣的人,他是一個令人不悅的惡棍——以及“懷舊派”(Nostalgics)和“進步派”(Progressives)。“懷舊派”是那些沒有真正家園感的移民,包括那些沒有戶口的人。“進步派”大多年輕且受過教育,他們是新進步政治的先鋒,但他們仍然在尋求一種難以捉摸的“天堂的政治”。明智的政治領袖會傾聽他們,并鼓勵他們定義新的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