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乘飛機時,你或許也曾在百無聊賴間翻閱過機上雜志。如今幾乎所有航空公司都會在自家的飛機上提供機上雜志,以此作為企業宣傳、品牌形象輸出的一部分。老道的乘客能從機上雜志的設計中看出每家航空公司的審美取向、地方文化特色,長期旅居歐洲,有著豐富旅行經驗的作家文澤爾對此很有話說:阿聯酋航空的機上雜志Open Skies無論是撞色系風格的手繪封面,還是整版整版用超廣角鏡頭拍攝的宏偉建筑、風景名勝照片,都有種濃濃的中東風情;美國聯合航空的機上雜志Hemispheres特別嚴肅;不列顛航空的機上雜志則分級供給,頭等艙能看First Life,商務艙則變成了High Life或Business……
據文澤爾考證,最早的機上雜志由美國泛美航空于1936年4月發行,最初它不過是每期寥寥數頁,刊登當地新聞和廣告的簡陋雜志。但二戰后隨著航空公司越來越重視品牌建設,機上雜志也制作得越來越用心。直至今日,全球約有150多種不同的機上雜志,有趣的是,其中許多其實是由同一家外包公司制作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邏輯也體現在了這些機上雜志中:
“盡管風格上相差十萬八千里,卻都是來自同一家公司——這就是現代出版傳媒集團往往主攬多家刊物的妙處所在。共享資源,節約成本,提高效率。”
在文澤爾看來,機上雜志是一種特別具有“場所性”的雜志:乘客進入飛機機艙后,就會根據自己對周遭環境的觀察確認“場所性”——這家航空公司乃至航空公司所屬的國家具有怎樣的特色?“機上雜志所需要做的,無非是將這些期許以文字和照片的形式,放進幾個小時后那短暫未來的視野里。”文澤爾注意到,隨著互聯網服務被引入機艙,機上雜志就如地面上的雜志一樣面臨數字化世界的沖擊。紙質機上雜志會消亡嗎?這同樣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文澤爾 著
后浪 | 四川文藝出版社 2023-7
《云端看雜志:談機上刊物,或言場所的場所性》
撰文 | 文澤爾

場所的場所性
短暫去巴黎時乘坐的柏林航空的雜志AirBerlin Magazine上偶然提到了機上雜志的起源,是由二十世紀的著名文化象征——美國泛美航空(PanAm)所創造。創刊大約是在1936年4月:印刷簡陋,每期僅寥寥數頁,內容也不過是當地新聞和大幅廣告而已。這本名字想不起來的雜志,不僅在泛美航空當時的上百條航線上供顧客取閱,還提供給美國聯合航空的飛機共用。當時的想法,應該是打造一本在飛機上可讀的通用刊物,并沒有多少突出企業文化甚至所在國文化的考量。二戰期間,因為物資緊缺的緣故,機上雜志曾一度取消。到了1947年,野心勃勃的美聯航為了突出自有品牌,推出了自己的Mainliner Traveler,主打旅游和商務新聞(請注意,這正是高端大氣的Hemispheres雜志的老祖宗)。
如今全球約有150多種不同的機上雜志,可實際上,其中大部分都不是由航空公司內部親自打造的:航空公司的宣傳和廣告部門,會將這項業務外包給專門的公司來完成。這些公司根據航空公司本身的定位、企業形象、航線覆蓋地來組織合適的編輯人員,聯系作者,制作雜志,再將印好的雜志用集裝箱運輸到航空公司總部,完成發行工作。目前負責這類雜志的全球最大公司為InkPublishing,這家公司包攬了近四十家航空公司的機上雜志制作業務,從印度廉價航空——香料航空(Spice- Jet)的SpiceRoute到布魯塞爾航空的Bspirit!,均是由Ink Publishing實際編輯出版的。
“盡管風格上相差十萬八千里,卻都是來自同一家公司——這就是現代出版傳媒集團往往主攬多家刊物的妙處所在。共享資源,節約成本,提高效率。”
偶然在飛機上遇到的熱情鄰座如此評價道,不過名字是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了——職業是新聞人,目的地是開羅,性別男,著裝正式得令人記不起臉。反正——無關緊要。他見我不言語,又笑說這段話是Ink Publishing的高層人物JeffreyO’Rourke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的。
“全是廢話,似乎是對的,其實沒用處,不是道理,而是感慨。”新聞人鄰座憤憤地評價。至于為何憤憤,原因我當然也不清楚。
“所以,怎么樣?” “機上雜志嘛,只要強調場所的場所性(PlacenessofPlace) 就可以了。” 好吧,其實新聞人鄰座不過出自我的杜撰,但“場所的場所性”——拿這個詞來概括機上雜志,簡直是再妥帖不過。場所自然是在飛機上,因為需要有人“在場”的緣故,便同時暗含了時間(飛行時)及對象(機上乘客)這兩個關鍵要素。而機上雜志作為一種特殊的預付費雜志,訂閱冊數一般是根據航線的座位利用頻次來確定的,發行量幾乎可被完全消化,退刊率趨近于零。在整個雜志出版業內,機上雜志的這一“完全封閉性”曾多次引發過激烈辯論,甚至其是否應該歸于傳統雜志之列,至今都未有定論。當然,形式上的認定倒沒那么困難:機上雜志往往被視作一類偏重于短閱讀的綜合雜志,內容側重點則在旅游、奢侈品及流行消費,還有娛樂休閑上。

記得曾在《明鏡周刊》還是哪里讀過一則專述,用測試數據證明飛機上的航行噪聲和顛簸感會削弱乘客的閱讀理解力(這大概屬于那類不需要看任何科研報告也能夠達成共識的所謂“經驗之談”),因此機上雜志的文章風格,以平實簡單為宜。Ink Publishing所雇編輯們的想法則更加細化,他們按航空公司、航線、票價和艙價來精確展現不同的風格。廉價航空的機上雜志設計往往更為簡陋些,所登廣告則更加平民化,內容也以普通旅游客喜愛的熱門景點、餐廳、流行產品為主。例子說回布魯塞爾航空,比如他們飛往巴塞羅那和飛往法蘭克福的航班上,機上刊物的內容就是有明顯區別的:旅游線路上以Bthere!和Bspirit!為主打,著重介紹目的地風土人情、重要景點,并順帶推薦一下與自己公司間有密切合作伙伴關系的旅游公司。商務線路上則按人頭分發諸如《法蘭克福郵報》或《每日財經》這類最新報紙。機上雜志倒也有(甚至還準備了一些如ELLE、Auto這樣的流行或專門雜志),但除非乘客主動向空服人員提出要求,否則不予提供,連看也不讓你看到。
“我們飛往一個地方,我們對那里會有怎樣的期許?”如果忽略機載電影,轉而翻看機上雜志,這將是我最希望能夠從中取得答案的問題。完美呈現“場所性”是機上雜志存在的理想狀態,想想看:如果我剛好能夠從雜志上得到想要的信息—— 事先想去的目的地景點的最新游覽指南、市內便宜又好吃的特色餐廳點菜建議、當地人正在熱議的新聞、幾句簡單但實用的外語……確實,目前許多大型航空公司已經在國際線路上提供了有一定限制的互聯網服務。比如素來以提供多種舒適服務體驗聞名的阿聯酋航空,除了可以任意點播電影、收聽音樂,以及用出身亞琛工業大學的阿拉伯工程師們特別設計的機載搖桿在座椅屏幕上玩游戲,還可以利用飛機自帶的網絡服務給朋友打電話或者瀏覽網頁。
盡管機上互聯網服務理應是大勢所趨,乘客需要取得何種信息,直接在網絡上搜尋答案即可——相比博大精深的互聯網,現有機上雜志在信息量和信息時效、精確度上都存在先天劣勢。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機上互聯網也同樣將網絡信息的冗雜、細碎、難辨真偽帶到了平流層以上的高度。我們已經無法擺脫互聯網,但仍需要自己給自己做決斷。互聯網的存在,恰恰是在抹殺“場所性”,以全無篩選和濃縮的態勢,將地球上任一個聯上網絡的角落變得全無特色。

泛美航空創造機上雜志之初,無非是希望能夠給乘客們一種打發機上無聊時間的消遣方式。今日的航空服務業已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若論消遣,雜志顯然遠及不上機載屏幕上播放的最新電影——只要常坐飛機,這項觀察結果可說是有目共睹。
所以干脆剔除掉機上雜志的消遣性,讓它能夠更徹底地呈現“場所性”為佳。如此細想起來,“場所”并不是孤立在機身以內、乘客們閱讀時所安坐的乘客座椅上的——聯結起飛地與目的地間那條或許數千乃至數萬英里長的、看不見的“航線”,以及這條“航線”兩端的風土人情差異,再加上客機本身,才是我們當下正在討論著的“場所”。這意味著理想的機上雜志編輯部,需要考慮比如巴基斯坦人去塞浦路斯度假時,想要獲知怎樣的具體信息;又或者中國人前往新德里時,不希望吃到哪種口味的咖喱——乘客中的小部分人可能已經了解到這方面信息,并且比編輯部在刊物上所提供的還要詳盡、深刻得多。但機上刊物永遠是為大多數乘客服務的,從某種角度上講,機上刊物可說是大部分乘客對目的地期待的結晶。
這樣的說法稍嫌矯情,所以“結晶”改成“集合”,可算是給機上刊物“場所性”等思考的一種理想結語。
機上刊物未來形態暢想
作為一座私人圖書館的擁有者和經營者,總有人會想起來問我同樣一個問題:
“紙質書終究消亡,你覺得呢?” 如此大而化之的問題實在無法回答。比如如何定義“紙質書”,如何定義“消亡”,“終究”指向哪個時間點,等等,太多的不確定,太少的期許。不過,拿這個問題限定下范圍,放在本文中倒可以成立了:
“紙質機上雜志終究消亡,你覺得呢?” 上周生病在家,偶然收到一封漢莎航空(Lufthansa)寄來的推廣郵件,標題是很醒目的一句話“Lufthansa Magazin機上雜志提供免費App 下載!”全文德語,翻譯過來大致如下:
“Lufthansa Magazin登錄App Store。過去,讀者們只能在飛行過程中享受這本流行、時尚、信息量豐富的雜志;不過——從現在開始,感興趣的朋友們也可以使用自己的iPad,在App Store免費下載最新的雜志了!我們的電子版雜志提供視頻、音頻、360度全景展示等多媒體特性,歡迎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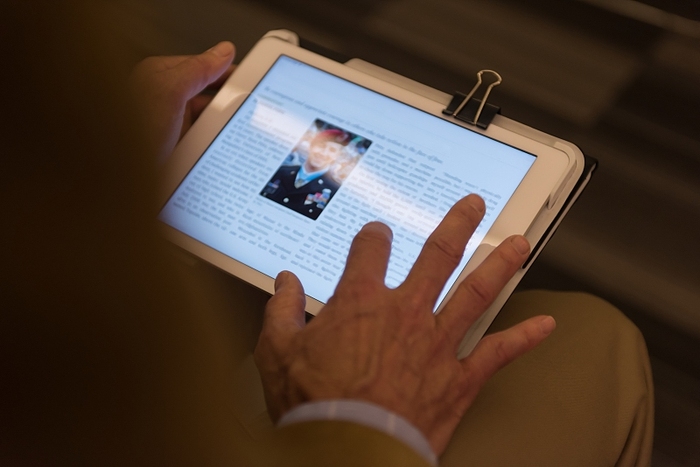
這封郵件意外為我此刻所撰的文章提供了一堆堪稱悖論級別的議題:且不論Lufthansa Magazin的具體定位如何,一份原本具有完美封閉屬性的雜志,突然以免費形式進入活躍用戶數達到五億之巨的AppStore,可說是完全拋棄了本身的封閉性。仔細思考,這既不能算是原來機上雜志的電子化,也不能算是原封閉雜志的開放化。若說漢莎希望用統一的電子版本來取代紙質刊物,大而化之的角度似乎說得過去,可實際上,飛機上并不是每位乘客都會拿出iPad(根據最近實乘飛機時的觀察,無論全球哪條航線,光是會取出iPad的比例,能有10%已經很不錯了)來瀏覽預先下載好的雜志(這個比例應該小于1%)。就目前情況而言,兩個用戶群間并沒有太多交集,且iPad相比紙質雜志還是太重,喪失了隨意翻閱的舒適感。就算Lufthansa能為每位乘客配備相應的電子閱讀器(相對漢莎航空的三百多架飛機來說,顯然會是筆不小的改造開支),看電影的用戶也絕對會比瀏覽雜志的人要多。想想看,既然選擇開放iPad雜志架,那為何不干脆開放《時代周刊》《名利場》《花花公子》這樣的大刊給機上乘客們免費或付費閱讀?不客氣地講,機上雜志的唯一核心特點就是封閉性(大部分時候與前文提到的“場所性”等價),未來若拋棄封閉性,讀者群轉變為一般雜志讀者,內容轉變為一般綜合類雜志內容,也就同時失去了仍需存在的理由和競爭力。
關于這個 問題,去掉題設中的一個限定條件后,或許能夠看得更直觀些:如果不是電子版雜志,而是將印刷版的Lufthansa Magazin以5歐元的售價放在書店和書報亭里銷售,將會如何?
結論一目了然:在所涉領域里缺乏與專業雜志一較長短的實力,要么從市場上消失,要么淪為“粉絲向雜志”——“粉絲” 自然指漢莎航空的堅定擁護者們。可是,一旦演變成此種情況,和在飛機上供乘客免費瀏覽相比,又有什么實質區別呢?機票或許降價5歐元(實際上,發行本身增加了成本,這點是不可能實現的),喜歡看Lufthansa Magazin的常客們則在候機時花同樣的價錢買來最新一期?徒增煩瑣罷了。
沒錯,且不論場所性,飛機上總是會有“不如輕松讀本雜志”的需求,紙質機上雜志在至少十年時間內,應該是不可能退出歷史舞臺的。進一步想,一旦乘客確定出發點與目的地,選好合適的航空公司和航班。在進入相應的飛機機艙后,便瞬間達成與“場所”間的某種神秘契約——什么是合適這里的?包括空服人員的制服、年齡、態度和相貌,包括飛機餐的菜色和所提供酒水的品牌、數量,包括座椅間距離的大小、所使用椅墊的圖案及用料、舷窗的形狀、過道地毯的顏色及踩上去時的質感、機用耳機的音質、毯子的大小和舒適度……所有這些要素的獨有特色聚集一處,便成為這一航空公司,乃至航空公司所屬國家的特色概括。而機上雜志所需要做的,無非是將這些期許以文字和照片的形式,放進幾個小時后那短暫未來的視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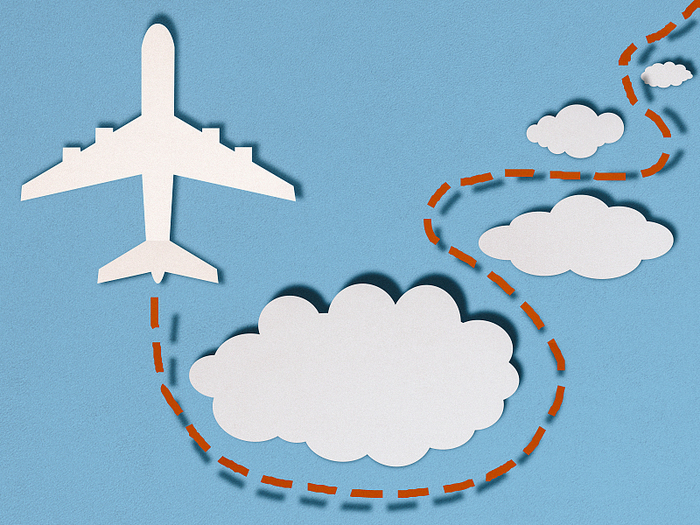
忘了是在哪次例會上,佐藤君告訴我,2016年時,荷蘭皇家航空的機上刊物Holland Herald就要迎來它創刊五十周年的紀念日了。到時他肯定是會去收一本“半世紀紀念刊”作為留念的。Holland Herald我也讀,2008年底的時候去鹿特丹,還記得當時雜志里收有一篇介紹都市傳說的專題文章,題目是Believeit,ornot! 內容及四色版畫風格的插圖均相當漂亮,即使面對Life或者Reader’s Digest這般的世界級刊物時也不遑多讓。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未來的機上雜志能夠進行這樣一類嘗試,即完全摒棄“場所的場所性”,成為那種只在小范圍內提供閱讀的人文類雜志,又會如何?以跨國航空公司所擁有的資源及財力,聘請頂級設計師和專業編輯來制作更高水平的機上刊物,理論上自然沒有任何問題。如果世界上有種雜志是真正的“閱后即焚”,比如只能在特定的航班上讀到,內容極端精彩,且完全不允許乘客帶走——如此一來,率先提供此種服務的航線,將會出現乘客爆滿、一票難求的情況也說不定。
比如全日空航空上赫然出現佐藤君主編的Inflight Magazine Magazine(日文名字或許是『機內志の志』)。
全日空大概是不會愿意的吧。
本文節選自《孤獨的旅行家》第七章《云端看雜志:談機上刊物,或言場所的場所性》,較原文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