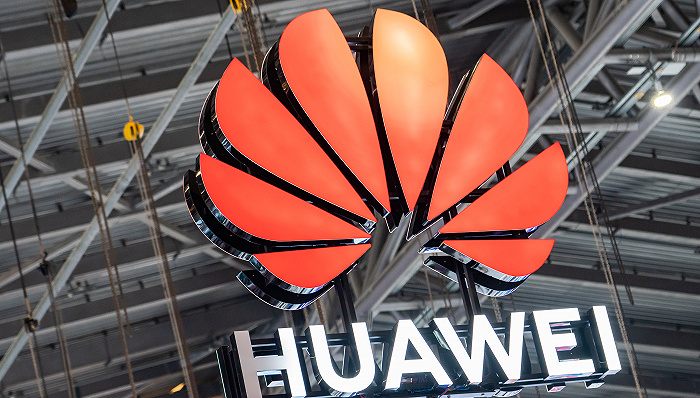界面新聞記者 | 陸柯言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方遠
9月25日,孟晚舟回國兩周年當天,華為舉辦了秋季全場景新品發布會。
在這場發布會上,Mate60系列手機仍像它發售時那樣神秘。華為沒有為手機留出講解時間,而是介紹了平板、手表、智慧屏、耳機、智能眼鏡等新品。
但無論是舉辦日期、開場與結束時特意設計的合唱環節,還是現場此起彼伏的“遙遙領先”口號,都讓人意識到這場發布會的與眾不同。
每次手機廠商舉辦發布會時,來自全國各省的經銷商都會在現場拉起橫幅,為即將開始的發售打氣。但最終的銷售成績到底如何,所有經銷商心里都沒底。
而在這場發布會前,不止一位來到現場的經銷商告訴界面新聞:近幾年沒有哪一代產品像這次這樣,辦不辦發布會都充滿信心、供不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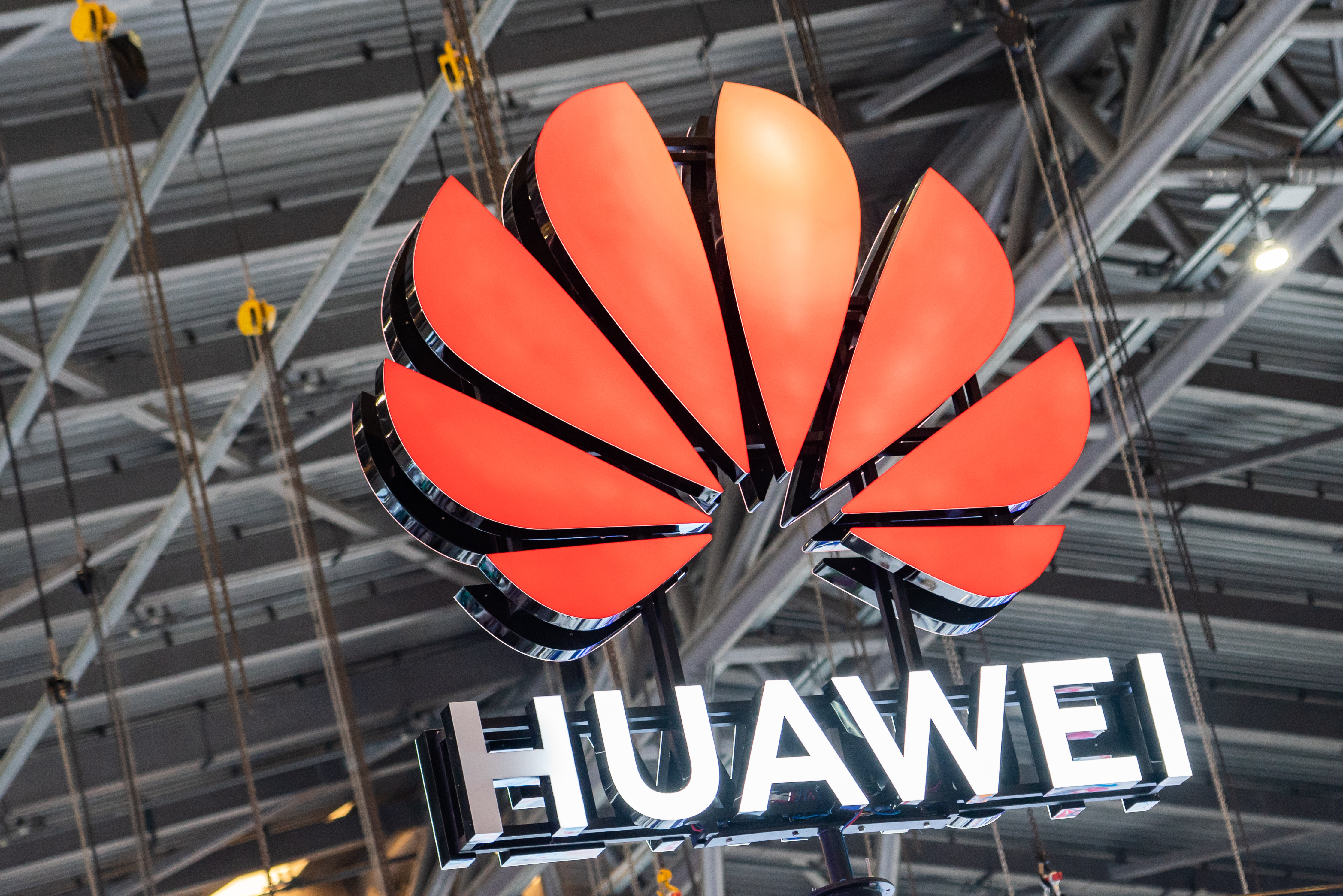
Mate60仍有挑戰——比如供應是否能夠滿足需求。但無論如何,華為需要借其來告訴外界,自己已經做好回歸的準備。
在此之前,華為已經蟄伏四年。
緊急補胎
2019年5月,華為首次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此后所有受《美國出口管理條例》管轄的物品,向華為出口、再出口或進行境內轉讓都必須獲得許可。
負面影響接踵而至。谷歌宣布停止與華為合作,華為手機也無法再使用與安卓系統深度集成的谷歌移動服務(GMS),這直接砍斷了華為在海外市場的可能性。第二輪制裁也很快降臨,臺積電無法再為華為代工芯片,麒麟芯片成為絕版。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華為只能盡力節省臺積電在限期前趕工的芯片庫存。
海外被限后,華為手機將戰略重心轉回國內。 根據第三方市場調研機構Canalys發布的數據,華為(含榮耀)在2020年第二季度智能手機出貨量在中國市場占據半壁江山,并首度登頂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第一。但由于供應鏈難以支撐,華為很快從頂峰跌落,滑入“Others(其他)”。
華為人對此早有預感。時任華為終端BG軟件部總裁王成錄說:“市場份額第一并不意味著真正的第一,因為方向盤不在自己手中,一被制裁就下滑了。”他向任正非建議,華為用戶規模增長后,根基不握在手中會十分危險。因此,華為要做自己的操作系統,更要有自己的生態。
谷歌的斷供加速了這個進程。2019年10月,華為開展了一場公司史上最規格最高、參與人數最多、最具挑戰性的緊急“補漏”項目——“松湖會戰”。超過2000名華為工程師匯聚在東莞,攻堅HMS(華為移動云服務)與鴻蒙操作系統,以替代安卓的統治。時任華為終端云服務總裁的張平安回憶,這是一場但凡參與過的人提起都會落淚的戰役。
鴻蒙問世時并不被看好。華為在2020年拿出鴻蒙1.0版本時,外界形容它是“PPT”。即使一年后發布了更完善的2.0版本,鴻蒙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為是安卓翻版。但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里,這卻是必須邁出的一步:華為需要盡可能地優化鴻蒙體驗來留住用戶。
而在硬件層面,有限的芯片庫存正在一點點耗盡。華為及榮耀兩大品牌幾乎陷入出貨停滯,渠道商和供應鏈均無米可炊。有專賣華為的渠道商表示,一旦斷血超過三個月,現金流就有可能斷掉,這也威脅著一家經銷公司的生命。無奈之下,剝離資產成為當時唯一的選擇。
2020年11月,華為宣布將榮耀品牌相關業務資產出售給深圳市智信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并不再持有榮耀公司的任何股份。獨立后的榮耀重新修復了供應鏈與渠道,而華為也通過出售榮耀的利潤獲得了短暫的喘息空間。任正非在送別宴上告訴榮耀員工,一旦“離婚”就不要藕斷絲連,不要心疼華為,甚至可以喊“打倒華為”。
瘦身與補漏是華為被制裁期間的關鍵詞。也正是在被制裁之初,華為成立了一家注冊資本達7億元人民幣的子公司哈勃投資,重點投資芯片制造、汽車電子及5G產業鏈等核心業務。
過去兩年間,華為研發費用也達到歷史高位,并且對根技術保持幾乎無上限的投入。例如華為芯片設計部門海思,華為副董事長徐直軍稱:“只要我們養得起,我們就能養著他們繼續向前。他們可以不斷做開發,為未來做些準備。“
夾縫中生存
在供應鏈受限的情況下,華為用了兩種妥協手段來解決芯片問題:一是通過不斷優化軟硬件來延長手機的使用壽命,比如延伸芯片的可用性,用面積、堆疊方式換性能,用不那么先進的工藝保障未來產品的競爭力。
另一種妥協的手段是,在高通4G芯片解禁后,重啟4G手機生產。2021年春節前夕,供應商接到了華為采購4G手機相關零件的訂單。Mate50系列、P50、P60系列手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推出的。
余承東曾對央視回憶,在做Mate50之前,很多人告訴他不可能成功。壓力最大的時候,他半夜一個人到外面走,走到天亮時再回來。最后的市場熱情證明,Mate50這一仗華為還是打贏了,但團隊幾乎沒有任何時間慶功:“都到絕地求生的地步了,哪還有時間狂喜?”
在艱難時刻,Mate50的確幫助華為守住了部分市場,但由于高通供應仍然有限,渠道端的缺貨情況始終沒有緩解。
長期與華為合作的渠道商告訴界面新聞,艱難時期的華為只能夠選擇保住各地區的堡壘客戶(出貨量大、華為產品占比高的經銷商)上,每個城市商圈基本只留住一家門店即可。而在縣城或者鄉鎮,則有大約三四成的門店因為分不到貨而關門或者轉型。
一面是供應鏈與渠道的枯竭,一面是養活整個終端事業群的壓力,華為開始使盡渾身解數造血。華為推出了智選手機策略,包括Hi Nova、優暢享、NZONE、麥芒、鼎橋等品牌,智選同樣賣各種合作伙伴的消費電子產品,甚至包含背包和雨傘。當時內部還在規劃進軍游戲行業,但后來這個項目不了了之。
最危急的時刻,華為想到了賣車。余承東在對外宣布這個決定時表示,美國四輪制裁后,華為手機這種高頻、剛需、海量的產品業務遇到巨大的困難。智能電動汽車銷量雖然沒有手機那么大,但是單價高,能夠彌補手機的銷量和利潤缺失。
汽車市場并不如華為預想中的那樣簡單,華為與賽力斯合作推出的問界品牌也出現了一段時間銷量低潮。但對渠道商而言,保住與華為的合作尤其重要,這決定了華為5G手機回歸時能否成為優先級更高的經銷商。“這幾年很難熬,只有華為5G手機回歸,我們才會有翻盤的機會。”
2020年的業績發布會上,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被問到次年計劃時,他的答案是“爭取明年還能發財報”。這句話成為了華為每年公布財報時的一個經典梗。盡管有些夸張,但卻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這家焦點公司過去四年的困境:核心業務增長遇阻,新興業務需要追趕時間,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
但當被問及是否會放棄手機業務時,徐直軍給出了明顯否定的答案:“我們不會放棄,而是努力讓它在適當的時候重回正軌。否則我們辛辛苦苦打造了一個品牌,說沒了就沒了,這么努力生存,還有什么價值呢?”
企業業務“供血”
終端業務淡退的幾年間,To B(面向企業)業務成為了華為新的增長引擎。
華為云的成長尤其快速。這個2017年才成立的部門,已經在短短幾年之間躋身中國前二、世界前五。2021年,華為云在金融、制造業、互聯網等領域均保持20%以上增速,在一片公有云巨頭失速的背景下,成為唯一高速增長的頭部廠商。
數字能源同樣是華為近年的明星業務。2021年,華為成立數字能源技術有限公司,成為與華為云、車BU、三大BG并列的一級部門,營收增速高達30%。
但這仍然不夠。華為企業BG副總裁陳幫華告訴界面新聞,盡管2021年,華為在云、數字能源等領域都實現了營收30%的增長,但國內的增長并不符合預期。因此,華為希望將To B業務進一步聚焦子行業,通過軍團的模式更貼近客戶,來帶動收入增長。
從2021年至今,華為接連組建了二十余批軍團,囊括煤炭、港口、數字能源、金融等各個細分行業。各大軍團與華為三大業務運營商BG、企業BG、消費BG屬于同一級別,軍團組織由任正非親自制定并督導。
每屆軍團成立時,華為都為其舉辦至高規格的出征儀式。任正非在首批軍團成立時的講話,也揭示了軍團在華為當下背景下的使命:“我認為和平是打出來的,我們要用艱苦奮斗、英勇犧牲,打出一個未來30年的和平環境……讓任何人都不敢再欺負我們,我們在為自己,也在為國家。”
華為內部人士對界面新聞分析,煤炭、港口、光伏這幾個行業的解決方案是可以高度復制的,這是華為最擅長的事。先大量投人、投錢到一個行業中,然后快速復制,有利于在短時間內打下行業山頭,從而實現高速增長。
如今,軍團已是華為當前最重要的作戰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為華為貢獻了新的增長。2022年,華為云收入453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25%;數字能源業務收入甚至更高,達到508億元。同期,整個企業BG收入為1331.5億元,增速超過30%,成為毫無疑問的增長引擎。
而相比起華為過去處處都要爭第一的風格,軍團的目標也更為實際。正如任正非所說,市場部門要逐漸從銷售收入導向,轉向加大利潤的考核權重。各產品線、各地區部不要盲目地爭奪什么第一,要創造價值、合理利潤,關注生存。
全面回歸
幾乎所有接受采訪的華為員工都認為,公司從來沒有對“從實體清單中出來”抱有任何幻想。如何在制裁常態化下維持正常運營,才是核心問題。
但人們仍然感受到了華為放出來的積極信號。在今年年初的新年問候中,華為輪值董事長胡厚崑寫道:“當方向盤突然回到手中,短暫的茫然之后一定有大膽前行的欣喜。”
此后不斷有好消息傳來。4月,華為宣布實現自主可控的MetaERP研發,并完成對舊ERP系統的替換。這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企業級IT應用,也是華為企業經營最核心的系統。在此之前,國內公司還沒有研發出能夠滿足如此大規模跨國企業使用的ERP系統。
這只是華為這三年來在基礎軟件領域的突破性成果之一。在基礎軟件開發工具方面,華為三年間完成13000+顆器件的替代開發、4000+電路板的反復換板開發,階段性克服美國政府斷供帶來的生存問題。其中,華為聯合國內EDA企業共同打造了14nm以上工藝所需的芯片設計工具EDA,基本實現了14nm以上EDA工具國產化,2023年將完成對其全面驗證。
不同于此前的高調官宣,備受關注的手機業務回歸反而采取了一種最低調的姿態。Mate60在沒有任何提前預告的情況下發售,甚至沒有寫明芯片配置信息,但卻收獲了史上最高的關注度。大量拆機與測速視頻似乎已經說明,Mate60實際體驗已經超出消費者預期。
從數碼博主的拆機視頻來看,華為Mate 30系列的國產零部件比例僅為30% ,Mate50系列超過60%,到了Mate 60系列,國產化率已經超過90%。至少有46家供應商、一萬多種零部件來自中國,也是目前國產化率最高的手機。
華為內部人士向界面新聞確認,華為手機從今年秋天開始啟動全面回歸戰略。國內渠道與供應鏈已經為此做好十足準備,此前因營收下滑流失的員工也正在回流。而在海外,華為終端發布會的節奏也更為密集。上述人士稱,海外回歸也只是時間問題。
撇去當下面臨的贊譽與爭議,過去四年的華為仍是一個頗具研究價值的商業樣本——當一家規模堪稱巨大的制造企業供應體系被突然切斷,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實現快速自我造血。
擺在華為與整個國產供應鏈面前的挑戰仍然艱巨,現在也遠遠未到最終的慶功時刻。但可以確認的是,華為在封鎖中活了下來,并且又站回了熟悉的起跑線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