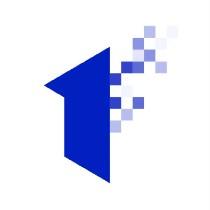文|一財商學院 吳羚瑋
做內容,是拼多多在競爭格局下做出的防御動作。其內容化陣地,目前僅有多多視頻與多多直播。
作為電商平臺旗下的內容產品,多多視頻依靠“撒紅包模式”成為用戶增長最快的玩家之一。2020年2月上線后,多多視頻DAU(日活躍用戶)已于去年底至2023年初突破1.5億,目前穩定在1-1.2億——不及抖音(超6億)、快手(近4億),但超過小紅書(近億)。用戶時長峰值超過40分鐘,目前穩定在30分鐘上下(視頻號用戶時長35分鐘)。
但直播業務一直是拼多多長期未見起色的業務:自2019年上線直播業務后,目前還沒有孵化出一個叫得上名的頭部主播,也沒有一個標桿型的直播商家案例。直播曾在2020年9月出現在拼多多首頁底欄tab中,此后又因表現未達預期,在2022年被“多多視頻”取代位置。
今年年初開始,沉寂許久的多多直播先后推出多項激勵政策,大規模招募直播商家、服務商、主播——恰恰說明此前直播功課的欠缺。
拼多多在直播業務上成績平平,既出于超級大腦的戰略考慮,也有商業模式的必然性。長期來看,它的內容化之路走得也不會容易。

戰略重要性上,直播弱于品牌化與買菜
一家公司的第一戰略,決定了資源流向。近年來,拼多多的主要精力放在品牌化和多多買菜業務上——希望通過增加SKU,實現營收增長,近期則放在了跨境業務上。在資源有限、且人員能效已經被高度榨取的情況下,拼多多在買菜這一主要戰場投入的精力,自然高于直播這個次要戰場。
2020年,淘寶直播已經構建起了達人主播+商家自播的完整生態,快手也有辛巴、散打哥等家族團隊,抖音攜重金打出羅永浩標桿,分別在主播側和供應鏈端進行卡位。盡管拼多多也曾在同年邀請馬布里、周濤等明星主播造勢,但馬布里的一小時直播中,只賣出不到160件商品,場觀只有兩萬多人。
由于直播業務表現未達預期,原本拼多多計劃增設的直播事業部未能落地,此后拼多多內容化業務一度沉寂。而疫情特殊時期催生的線上買菜需求,使得拼多多在2020年中調集1000多人籌備多多買菜,占當時總員工近 1/6。
拼多多創始人黃崢在2020年10月10日拼多多的五周年內部講話中,指出多多買菜是拼多多“炸開金字塔尖”的“試金石”項目。相比之下,他對直播的評價是一項“工具屬性”的業務,是“提供給商家運營私域流量的工具”,對應地,此前拼多多的直播入口藏在首頁商品列表、商品詳情頁、店鋪頁和聊天頁等地方。只有私域做得好的商家,直播間才有被看見的機會。但在拼多多這樣一個以低價單品換爆發的平臺來說,商家很難擁有“私域”。
商業模式與商家類型,決定拼多多難做內容
從商業模式上看,拼多多主打“低價+單品爆款”,結合中心化流量分配機制,制造爆發性銷量的神話。
曾經李佳琦、薇婭們被稱為“人形聚劃算”,就因為他們和聚劃算、拼多多一樣,走的都是“薄利多銷”的模式。直播電商的“省”與拼多多的“省”同源,都來自于需求的聚集。
此外,拼多多在低價供給與匹配的效率上,還要高于直播電商。因為后者受限于幾大因素:
受限于時間:貨架電商可激發并承載全天購物需求,直播電商僅有直播那幾個小時。
受限于流量池:拼多多的低價商品可以拿到全網流量,直播電商是在各個主播/品牌的流量池中聚集需求。
受限于顆粒度:拼多多聚集需求的顆粒度到SKU,直播電商聚集需求的顆粒度到品類——因為主播的私域流量很可能跟SKU并不匹配,大部分達人直播間會盡量劃分品類矩陣賬號解決匹配效率問題。
因此,當拼多多已建立起一套更高效的供需匹配模式,也有了低價心智,便沒有太大必要再次克隆一個已有的商業場景與模式。
從拼多多的商家類型來看,主流商家是白牌工廠。第一,價格是這類商家的最大優勢,不太需要內容的額外加持。商家投入內容的能力與意愿有限。第二,通過服務商代運營或進行達人直播,將極大拉高這些商家的經營成本,反而削弱價格優勢。對品牌型商家來說,拼多多的角色定位往往是清庫存渠道,不會在其中投入內容預算。
從服務商和主播入駐意愿度看,拼多多的低客單價,加上商家的低出價意愿,意味著主播的抽傭低,也很難吸引到有影響力的達人入駐。
短視頻靠補貼“上位”,但未必持久
拼多多的內容化布局,原本寄希望于直播業務,但后續便將籌碼押注到了短視頻業務。
從入口設置來看,2020年,拼多多首次推出多多視頻時,它還藏在“個人中心”里的二級板塊“功能”中,但到了2022年初,多多視頻替換“直播”,正式上線拼多多首頁底部一級入口。目前,拼多多首頁關于內容的入口僅有底欄Tab的“多多視頻”,平臺內沒有直接找到直播入口——從“多多視頻”進入后,用戶需要向左滑動才能看到直播推薦。
從資源分配上看,拼多多主要通過現金獎勵的模式獲取用戶:第一,根據用戶瀏覽時長與瀏覽視頻數,分階段發送紅包至微信賬戶,這一部分由拼多多來承擔;第二,商家根據成熟用戶在平臺上總的停留時長與視頻數、評論數與點贊數進行提現獎勵,由商家承擔。據36氪報道,拼多多2022年給予多多視頻的用戶補貼金額逼近10億元。
兩項舉措,讓多多視頻用戶滲透率從2022年2月的8%提升至2022年7月的25%,目前日活穩定在1-1.2億,用戶時長峰值超過40分鐘,目前穩定在30分鐘上下。
相比直播電商更重的模式——涉及供應鏈、品類供給、服務商與主播等服務配套,布局短視頻投入精力較小,帶來的用戶增長更客觀。不想在用戶時長爭奪戰中落下風的拼多多來說,這是一條捷徑。它曾經分別依靠微信與百億補貼塑造的價格心智引流,現在做短視頻,依舊是為了拉開流量口子,而非通過種草實現轉化。據觀察,多多視頻少有帶商品鏈接的短視頻,且大量是擦邊視頻——這說明它并不指望消費者在看完短視頻后就產生下單沖動。
高額補貼帶來的增長難以持續。據36氪報道,受補貼力度影響,多多視頻的DAU和用戶時長等數據呈現起伏。補貼力度最大的2022年二季度,補貼額3-4億元,多多視頻DAU從一季度的1億增至1.2億。到三季度,由于補貼下降,DAU回落至9000萬左右。拼多多在四季度加大了補貼額,才讓DAU在去年雙11期間達到峰值,突破1.5億。
多多直播補課:供給、服務商和主播
品類供給上,此前拼多多的直播運營中,品類范圍僅限于生鮮食品、服飾等高速線上化滲透的類目,且對單一直播間的品類內容有相對固定的要求。
2023年3月,拼多多利用產業帶方面的優勢,發布“百產計劃”,旨在招募產業帶商家入駐開啟店播,實現平臺品類快速擴張。新商家只要入駐參與“百產計劃”,就可以在完成相應任務項的前提下,獲得最高相當于59200元的廣告紅包,以及千萬級免費流量扶持等優惠。
當前其他各平臺普遍向商家以5%以內標準抽傭,多多直播目前不向商家進行服務費抽傭。
在2022年之前,拼多多官方并未提供直播運營服務,也沒有安排配套服務商,商家僅能自行摸索經營。雖然大部分商家品牌開通了相關功能,但長期以來都是在直播間循環播放錄播視頻或宣傳視頻,并沒有真正將直播運營起來。但多多直播也對商家提出了從錄播轉向真人直播的要求,錄播功能將于2023年第三季度下架。
配套服務體系上,主要分為主播與服務商:
(1)主播
2023年1月,多多直播啟動“新超星計劃”,招募其他平臺成熟主播入駐。計劃中,凡是在多多已有店鋪,或者在站外有直播店鋪的運營者,只要參與計劃,就可以得到1萬至2萬元不等的流量獎勵。
此外,多多直播還推出“伯樂計劃”、“百萬主播挑戰賽”。其中伯樂計劃規定,無論服務商還是商家,每邀請成功一個主播開播,就可以獲得300元的廣告推廣紅包獎勵。而百萬主播挑戰賽,則是平臺為鼓勵主播更積極參與直播而設立的比賽獎勵活動。該活動規定,在真人直播中近30天內總成交額達到一定水平的主播,有機會獲得平臺給出的每月最高達30萬元廣告紅包獎勵。
(2)服務商
2023年618后,多多直播在長三角、珠三角、環京、成渝等重點產業帶大規模引入服務商,并對商家主播提供一對一服務,以全面提升商家的運營能力。
對服務商入駐大幅放寬了門檻條件,規定任何類型服務商,只要具備合規的營業執照即可入駐,不設任何押金,并且不設區域和品類限制。市面上常見的直播場地運營商、云倉服務商、MCN機構、廣告服務商等主體,皆可成為多多直播服務商。
組織架構上,多多視頻由秋白(花名)負責,他曾任職于抖音,在2021年前后加入拼多多。最初拼多多的短視頻與直播業務均分散在各個行業類目,每個行業類目配備一定人員進行運營,由類目負責人統管。
自2022年以來,為了應對抖音等短視頻平臺的沖擊,拼多多開始將分散的直播和短視頻業務合并管理,內部將這一業務統稱為“Video View”,代號“VV”。
據一名拼多多內部人士透露,拼多多負責直播和短視頻的團隊,包括產品、運營、設計,共50-60人。目前團隊主要考核指標有兩個:一是日活,保證“多多視頻”這一tab的流量;二是成交規模。
(3)拼多多內容戰場時間線
· 2018年:拼多多就開始鼓勵商家、工廠進行直播賣貨;
· 2019年:11月底“多多直播”開始內測微信小程序;隨后,拼多多App以“百億品牌補貼”為入口,低調開啟直播首秀;· 2020年:1月首次增加直播頁面;2月首次增加多多視頻;9月,首頁上線統一直播入口;(2020年下半年,拼多多曾計劃增設直播事業部,由聯合創始人陸娟君領導,但由于直播業務表現未達預期,該計劃未能落地。此后拼多多內容化業務一度沉寂)
· 2021年:5月多多視頻變為一級入口,對部分用戶進行內測;
· 2022年:2月多多視頻正式在一級入口上線。
電商平臺一旦誕生,便注定為流量而戰
兩個誕生于不同時代的電商平臺淘系電商和拼多多,最初選擇了不同方式,但最終它們的流量輸血方式殊途同歸。
拼多多早期依靠微信生態引流,中期依靠百億補貼的低價心智+站外采買流量,目前其唯一的內容入口“多多視頻”成為新增的引流方式。
淘系電商的內容嘗試曠日持久且無處不在。早期靠無所不包的“萬能”,靠神人、神店、神物;此后,為了實現站內種草-成交的閉環,先后嘗試過洋淘、直播、逛逛、點淘等種草項目,但效果有限。
長期以來靠自帶流量的網紅們+站外采買模式往站內引流;直到去年以前,淘系電商的內容化還屬于種草邏輯,但當淘寶直播、首頁猜你喜歡短視頻的指標先后開始發生變化,強調時長與互動等“內容”指標而非轉化指標時,淘系電商也開始信奉“流量型視頻”。